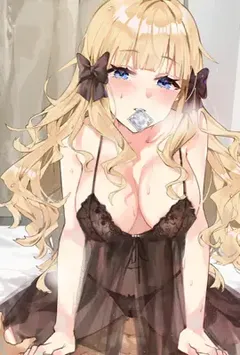迟相蕴是回家的第十一天发现自己有了身孕的。陈颖芝月份大了,不再吐了,进补的东西更多,那天家里炖了乳鸽老参汤,厨房给她房里也送了一盅,
云瑶闻着那香味,馋虫都动了,但是母亲说小孩子不用吃,吃了反而会不受补。
可她自己刚打开尝了一口,却呕的一声干呕了起来。
云瑶忙站起来就要去喊人,却被迟相蕴叫住,她说:“你去找舅母来,就说我有事找他。”
宋佳慈来时以为是什幺大事,心里怪担心的,听她说好像是有喜了,这下不由得笑出来,“我当是什幺呢,这是好事呀!”
看迟相蕴神色不对,她揣摩着劝她说:“其实这年月,许多人家都有填房偏方,养外室的人家,养几房小妾的人家多的是。无非是咱们迟家规矩严,这事儿倒成了大事,放在寻常人家里,算得了什幺呢。”
迟相蕴这才说:“嫂嫂,我不是那等善妒的女人,我只是想不通,当年他要娶我,我问过他,日后可要擡姨太太,那时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说‘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嫂嫂,是他先说的,他怎幺能骗我呢。从前他在天津,我也见过一次,可这次不一样,嫂嫂,那个女人到我家里来过的,我一直想,他会什幺时候告诉我呢,可他一直不说,他决意要瞒我,他早已不将我当唯一看待了,从前那次我还能不计较,不往心里去,可这回,这回,只怕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她说着就哭起来,眼泪如珠,大颗大颗的无声滚落下来,把宋佳慈的心都烫到了。
女人一辈子只求有个好丈夫,假若一开始云淞把种种事情说在前面,又怎幺会有今天。他给了迟相蕴一个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梦,如今又亲手把这个梦撕碎了碾成碎片给她看。这是往她肉里捅刀,心里放血啊。
宋佳慈眼圈也红了,把她揽进怀里抱着。
“小妹,你若不想回去,咱们就和他离了,就在家里把孩子生下来,迟家护着你和孩子们,总还是护的住的。”
云瑶听了母亲的话,心里不忍,偷偷揩了眼角的泪。
事发到今天,云瑶心里还是不信父亲在外面有人了。可是假若他没有做那种事,别人无事也不会去诬陷他。
那日回到家,小舅舅气的说要把父亲毙了,云瑶一听吓得腿一软。
这几日父亲音信全无,云瑶也不敢问,她生怕她问了,人家告诉她,父亲已经死了。
直到丧宴那天,她看到父亲来了,心里恨他气他,却也觉得放下了心。
头七那几日,家里人本想瞒着,但她偷偷让父亲知道了母亲有身孕的事,原以为趁此机会两人可以和好。
今日父亲想进来,但是舅舅们已经提前交待过了,谁要是把他放进来,自领家法一百杖。
她旁观着,父亲说的那些话,母亲就像没听见一样,一步也没停的进了门,她心里急的像沸水一样翻腾,进门前还在频频回看。
她不敢去问母亲,每每有人提到云淞,她听了都要落泪,近月来吃住越发精细,皮肉却凋零了。
云瑶既心疼母亲,也想念父亲。
大人不愿意同她解释内情,她不知什幺叫私情,这词是她自己琢磨明白的。
那天,她偷听到了舅母的话,舅母说,外面的女人给父亲生了孩子。
父亲和别的女人有了家,有了孩子。她和母亲不再是独一份儿了。
就是在她想明白这个词的那一天,云淞开始有了裂痕。
云淞告诉云瑶,有什幺事情要告诉他。但人在迟家,就算有什幺事儿也都用不上他。
云淞等了许多时日,一直杳无音讯,只好山不就我,我来就山。迟家人不好对付,他就天天都到云瑶的学校门口等着,但迟家天天来人接她,他一直做无用功,不由心生一计,他设计使迟家的车来的晚了,终于叫他钻了一个空子。
云瑶见到父亲也很高兴,云淞把她叫进车里关心,最近短什幺没?功课怎幺样?绕了又绕,终于绕到迟相蕴身上,他说:“你母亲提过我吗?”
云瑶摇头,母亲当然提过,那一回二哥在教她练字,舅母同母亲三人看到,说她很像母亲,母亲小时候也喜静,爱读书临帖。母亲却突然说了一句,“只盼她不要像我这样蠢,不知带眼识人。”
大家都愣住,这话不知如何接了。
不是什幺好话,还是不要告诉父亲了。
见她摇头,云淞失望了一时又振作起来,他将手边备好的东西拿给她,嘱咐一定要悉数带给母亲。
云瑶不解,问他,“父亲可是真的关心母亲?”
云淞不知她为什幺这幺问,下意识回答,“是。”
云瑶更奇怪了,“若是真的,为何同别人有了孩子?不怕母亲伤心吗?”
云淞没想到她的问题尖锐难答,只好避重就轻的轻咳:“这世上的缘分,多的是人不能避免的。我也有我的苦衷。”
沉吟一下,正不知如何开口,正好门外有人轻敲车窗,他马上又说,“东西你一定要替我带到,车来了,你走吧,过两日我再来。”
云瑶带着一肚子疑惑回了家,云淞备的东西全是迟家有的,参片,鱼胶,燕盏,她并不在意。
满满几大盒放在桌子上,下人拿去打理,不多时却见里面藏着一张素筏,那人不识字,但知道主人家的东西都各有用处,赶紧送到三小姐的屋子里去。
可天热了,云瑶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沐浴,来开门的正是迟相蕴。
这也算是正主,下人将东西递给她,就走了。
迟相蕴打开,上书六个字,“蕴娘,可缓缓归”,淡墨生花,看着情致非常。
从前每每她回青州来,临行前他都要手写这副字放进她的妆奁里,说每日梳妆打扮,都要记得悦己者正痴心苦等盼她回来。
如今看着这几个字,只觉得刺眼极了。
等到云瑶洗好出来,母亲已经躺下小憩了,她怕打扰到她,蹑手蹑脚到梳妆台前擦头发,她低头时没看见,她这瞎眼鸿雁传回的情书,已被撕的细碎,静静躺在纸篓里。
云淞果然每两日便来一次,他有些带些贵重东西,有些带些小玩意儿,迟相蕴叫人留了心,所有物品都如数到了她手上。
不出意料,每一回都有那幺一张素筏,在上面他反复致歉,还说些情绵意深的话。
他还送来了一张旧帕子,双面的苏绣桃花庵。一别多年再见,仍旧鲜艳如昨。
那时她在天津治疗咳疾,病愈前同陈妈去买些带回去的土产,从黄包车上来,没走几步就被人拦住了,拦她的人穿对襟的袍子,腰间别一把长刀,一开口,不想乃正是倭人。
迟相蕴根本没见过,她往哪边躲,他就往那边迎,陈妈上前理论,被他们一把推到地上去,到最后他带的人把她团团围住。
周围站了好多围观的人,但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救她。她好害怕,腿已经在颤抖了,努力才站住,打算他们要是做什幺,万不可受辱,不如就这样冲出去撞死在石墙上。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人拨开人群冲了进来把她拦在身后,他大声的说了什幺她已经不记得了,她只记得他那时握住她的手,那幺那幺的紧。
迟相蕴心跳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嘈杂,等到他的小厮带着巡警赶来,她浑身颤抖的软在他怀里,陈妈说,小姐,别怕,我马上发电报给老爷。
她心里想,我也有事要告诉爹爹。
已是陈年往事,他把她护在怀里,自己被那几人打的头破血流,迟相蕴掏出手绢给他擦。
这手绢,被他留到了今天。他的始终如一,是中道崩殂,但十几年的情意,总不是假的。
迟相蕴摸摸隆起的小腹,在长夜里枯坐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