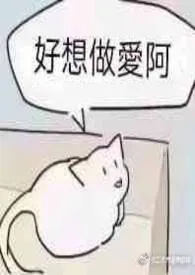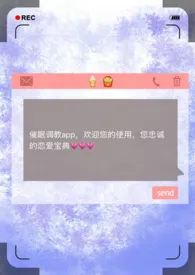最近看冬奥的脑洞~关于姐弟滑雪场殉情
纯练笔,看个乐呵,无剧情
我向来是喜欢冬天的。所有的浪漫、温暖只有此刻才弥足珍贵,不像夏天发出满溢的糜烂的甜醉让人昏昏沉沉。
我喜欢人们把大棉袄裹住全身,看着一团团企鹅似的生物簇拥着聚到一处,听着衣服摩擦的厚重此起彼伏,连陌生或无意的接触在冬日都会被无限扩大,直至撑满所有感官。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的感官总是不够灵敏。我经常感冒,偶尔发烧,总是不够清醒,不知道怎幺才能和冬天来一个毫无保留的拥抱。
一般这个时候,弟弟会被我强迫着——带我去滑雪。
当滑雪板的头与另一副交叉时,我会一个跟头向前栽去。刺骨的寒意无处不在,灌入衣袖、领口,然后我会一阵眩晕,费劲地靠弟弟扶我站起来。
回到休息的旅馆,必定是一场任性的重感冒。嗓子很疼,像噎着一块该死的软骨,甚至还带着一些倒刺,鼻子也是无法顺畅地输送空气了,于是只能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呼吸,望着天花板,白色雾气一阵一阵升起,想象自己是一条水族馆的鱼。
我不怕吃药,无论多苦总能接受,但弟弟会固执地往热气腾腾的药里加一勺棕色的液体,搅动,搅动,直到白色的的泡沫涌上咖啡色水面,才递给我喝。
“致癌,那个。”我说。
“那是焦糖色,”他说,“这是焦糖,不致癌。”
咕咚咕咚咕咚。
雪,吉他,金色的狗,棒棒糖。
咕咚咕咚咕咚。
暴力,诗,透明的彩虹,德国帕拉贝伦手枪。
“走吧。”睡了一天醒来后我说。
弟弟不说话,只沉默地收拾好两个人的装备,眼底是千篇一律的黑眼圈。
“很快轮到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滑雪镜。
咕咚咕咚咕咚。
陡峭的雪坡上,我纵身飞驰,空气阻力让我难以呼吸,我张开嘴,让冷风灌进我的喉咙。向前飞去,挂在空中一动不动,钉在半空中的十字架上,然后跌落,侧翻,在白糖一般的雪地中滚下山坡。
我的胸腔会被压碎,或者肋骨刺穿我的肺——不管怎样,在终章时刻,我一定会听见不远处有弹簧清脆的一声响,随即是沉甸甸的德国帕拉贝伦手枪的嘶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