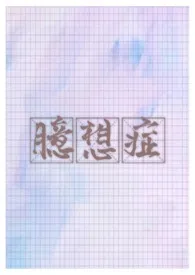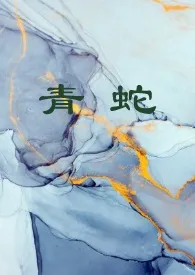穆至做了一个梦。
一只雪白的兔子,卧在一层厚厚的积雪上,红色的双眼在一片白茫茫中,就像在满地的纯净中撒下两颗红色的玻璃珠。
兔子不知是死是活,它的两只眼睛撑大,瞳孔中折射出异样的光芒。它卧在雪地里,也许是被冻僵,也许是在躲避打猎的人。
它的一双眼睛,充满惊恐,像是无数片破碎的玻璃渣拼接起来一般。
穆至的额头上蒙上一层细密的汗,她被那双近乎恐惧的眼睛盯住,双腿打颤,她的手揪住大腿内侧的一块肉,使劲掐下去。
疼痛把她从梦中唤醒。
大腿内侧出现一小块红,穆至擡手抚去额头上的汗。脱下身上穆启的套衫,衣服背后一片湿润,穆至擡起手臂在背后摸了一把,摸到一手黏腻。
她从衣柜里拿出另一件穆启的衣服,光着脚往外走。
噩梦带来的黏腻,像是一层液体包把她包裹在其中。
她偏头揉着长发,手指穿插在发间,让潮湿的发根呼吸。
从黑色的缝隙间,穆至看到穆启的背影。他坐在沙发上,背对着她。
穆至眯起眼睛,确认这不是另一部梦境。
腿间的红已经消去,穆至知道这不是梦境。
她登登两步跑,绕过沙发,岔开双腿跨坐在穆启的身上,搂住他的脖子。
“哥,你回来啦!”
穆至把下巴搁置在穆启的肩膀上,闻着令她安心的味道,她在其中沉醉。
短暂的吸取穆启的气息后,穆至撒开手,满眼期盼地看着穆启。
其实她并未期盼任何事,她只是习惯用这样的眼神望着穆启。
“你吃过饭了幺?”穆至笑着问,虽然现在下午已经过半,可她依然要问这样一句。
“木木。”穆启把她绕在自己脖颈上的双手拿下来,握在手心里,用一只手桎梏。
这种感觉像是,一只山羊被绑住双腿,而禁锢她自由的那根绳子被绑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
穆至记起梦里的那只兔子,血红的双眼现在变成穆启的手指。
“木木。”穆启叫着她的名字。
穆至的心产生微微的痛,像是一根木刺扎进手指,微弱的痛感原本只应该持续一瞬间。
“嗯?”
穆至注意到穆启连外套都没有脱,他的黑色风衣上有清晨露水的味道。
他在这坐了多久呢?
“我曾经说过。”穆启握住她的手腕,“我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生活……”
穆启的打算从未变过。
讽刺的是,穆元和成佳芳在世时,他并未有过关于他们的牵挂。如今他们变成一把土,他的牵挂却像千斤重的鼎,压在他的心上。
“我改变主意了。”穆启说。
穆至静静听着,她的双手还被握在穆启的手心里,山羊挣脱不过大树。
“在这里生活,也很好。”穆启的眼睛始终盯在穆至的手腕上,“不过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人在面临糟糕的事情时,有天生的预感,女人更是如此。
穆至感觉到自己的声带在颤抖:“需要谁的帮助?”
穆启握住她手腕的力气加大,几乎弄疼自己。
“我要结婚了,木木。”
穆启想了几十遍的话,却发现无论如何巧妙安排,这句话听起来依旧像一把锋利剪刀,能轻易扎进穆至的皮肉。
“我要结婚了,对象是苏如烟。我需要她的帮助,才能保护你。”
穆启的话不难理解,但一层话语有两层意思,穆至只能理解第一层。
穆启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来掩饰他们的感情。如果同性的爱尚需各种形式的掩饰,那他们这种被法律人伦所唾弃的感情,恐怕需要更多。
穆至理解,却也不理解。
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她分不清楚,到底是穆启结婚的这个事实更让她难过,还是穆启结婚的对象时苏如烟这件事更让她难过。
穆至并没有爆发,她想从穆启的手里抽走自己的手,却发现他们的手就像天生长在一起一般,无法分离。
“放开我。”穆至微弱的声音,像一只寒冬中苟存的蚊子。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
穆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一次比一次声音大。
可这些声音对穆启来说,就像那根缠绕在树干上的绳子,并未撼动他的枝叶。
“我恨你,穆启。”穆至的呼吸声加重,挣脱不掉穆启的手,这件事让她崩溃。
她撕扯着,她向后仰,用脚去踢穆启的腰;她靠近穆启的脸,在他的左边脸颊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牙印;她的眼泪多得打湿了穆启的脸。
可她挣不开穆启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