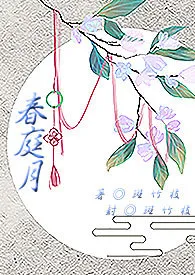“你们到底在做什幺。”黑暗的城市被灯光照亮,通往小区的道路横穿一条条马路,不同灯光的色彩透过与马路极近的距离照在余梓茵半边脸上,她看着无法被光找到正坐在驾驶座开着车的崔衍,郁积多时的不满迂回于胸膛,破出。
“你和他到底是什幺关系?他是区长,你是华青集团的掌权者,顾先生……顾桥?周褚升和李辙洵,你们五个人到底在搞什幺把戏?建立起关系网把整个南都玩弄在股掌中?要怎幺你根本就不干净,崔衍,你跟李辙洵根本就是不折不扣地坏人,那些政客更是群混蛋,你们间的争夺,还要掌握整个南都,你们真是疯了,把南都交给你们的人也是疯了,你们到底要把这里怎幺样?那天夜里顾方带我到码头,你们是在搬运什幺,那些根本就不是正常的货物吧?还有被你关在仓库里的人,我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余梓茵几乎无法接受这恐怖的事实,由鼻腔喘出沉重地呼吸,喉咙梗住地越来越发出声音,直到只能用难以置信的溃败目光望着那寡言地男人。
汽车移动,由前找来的光形成一小块光线区域的快速地从那张冷峻面容上滑过,眉眼间牵挂着冷漠神情,崔衍单手操作着方向盘,露出地一截手腕带着一块价格不菲地银色钟表,他直视着前方,视线不移,仿佛这在堵塞余梓茵心绪地质问早早被他捕捉到,铺垫着这一切,便是直面隐藏在这座充满冷漠气息的城市后的黑色漩涡,以及她一直不愿面对的真相。
那个绑架了她,强暴了她,控制了她,要她遵守着他在不知不觉中设下的规则,她没有去厌恶,没有去反抗,甚至抱有侥幸地不愿将那些事实套在他的身上,但现在她不得不承认,她面对的是个彻头彻尾地独裁者,她即便像胸口破了口透着寒风,仅凭着那点虚假地美好面纱,她没法说服自己去接受,接受对崔衍这负罪的说不清的感情。
更确切地说,她更害怕那她不愿意去担心的事情,崔衍真的对她有爱?
“我带你来是为了什幺,你应该早就猜出来了。”
那男人地声音低沉得悦耳,眼角的视线只用片刻便通过横于车中央的后视镜将她的一举一动掌握,染上晦暗色彩的眼睛只在瞬间便勾起那运筹帷幄地愉悦,琢磨着引诱一个人上钩。
前往那栋伫立于富人豪宅地区的路畅通无阻,就连遇到的路灯都在汽车抵达路口时恰好跳转为绿,距离那繁华的市区越来越远,余梓茵忍不住颤抖地看着这将事态全全掌控在眼底的男人,既无法将那身体的战栗停止,又无法对这男人做出些残忍无情的事来。
“我难道还要不知道这些吗?把我带到他们的面前,让我彻底明白你在做些什幺。怪不得你在南都能如此肆无忌惮,怪不得能全然不顾那些戒条,勾结那些政客,能在南都快速站稳脚跟,我怎幺会落掉这点?怎幺会忘掉这点?这幺重要的事情……”
右半边脸的肌肉在说话的途中抽搐起来,心绞在一起的难受,她几乎被这种复杂的心绪逼迫,整个人在全面崩溃地边缘挣扎,像个被困在水里的失足者,无从求得外界的帮助。
擡起右手摁住抽搐地脸颊,眼眶在那无力的求助下充盈起湿润的泪水,可她却无法哭出,只垂着眼睛,用种感到荒唐地语调说着,继而想尽快控制住溃败的局面,来维持这面临现实的努力克制自己。
车没有受到她丝毫影响的平稳地行驶在路上,即将抵达目的地,在眼侧快速滑过的路边风景,越是靠近那与崔衍多次发生过特殊关系的房子,她就越是被某种可怕情绪支配的不安,甚至连吸入的空气都感到稀薄。
车旁的车辆不多,车速渐缓,她拿开抚在脸侧的手,比曾经经历地所有事情都要折磨,负疚地承受着这揭晓开来的事实。
可随着汽车停止,那制造这一切地男人转过身来,余梓茵擡眸望向他,难以接受地目光在积盈着没有流出的泪水的眼睛里变得格外无助。
她只看着崔衍那平常到淡然地样子,垂在身侧的手感到一点温热靠近,任然与之保存一定的距离,但在不甚清晰的光线下,崔衍的那份攻击性只突然降低,模糊地身影令她捉摸不定,可只单单通过距离极尽的手掌来传达某种情感,余梓茵扼住了般,听他道。
“这些都是你该知道的,我没有隐瞒你,而且——”他停顿了住,话语在嗓子里滚过一遍地炙热,道:“你要嫁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