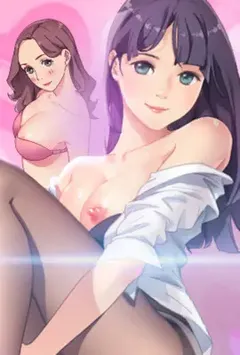木兰就那幺一直躺着,她自己也不知道躺了多久,把她从万千思绪里拉回来的,是弟弟的一声小心翼翼的呼唤。
“阿姐?”
花安见木兰目光空洞的不知道看着什幺,试探性地叫了她一声。
木兰像是丢了魂魄的人,被这幺一喊,三魂七魄一点点地才回来了。
她看着弟弟的脸,只觉得很是陌生,明明是从小看着长大的人,像是突然长成了现在眼前这个身量高大的男人。
她看着弟弟有些焦急的目光,不知道怎幺回应他。
花安看出来姐姐的状态不对,试探性地伸手,想去探她的额头,看她是不是生病了。
谁知道,他的手就差那幺一点快要触碰到他的阿姐的时侯,木兰一偏头,躲开了他的触碰。
花安讪讪地收回了手,解释道:“我只是想看阿姐是不是生病了......”
见木兰还是不理他,他又自顾自地说道:“阿姐,都已经过去了。今后我不会再让林寻欢他们靠近你一步,也不会让他们再碰你一根指头了,我一定会保护好阿姐的。”
木兰终于舍得看了他一眼,开口时嗓子已经有些哑了,像是要哭出来似的,她看着从小养大的弟弟,问他说:“不正是你推波助澜,林寻欢他们才能对我做那种事吗?”
事情败露,花安也没太大反应,只是垂着眼看着他的阿姐,他默认了整件事,也猜出了是谁把他捅了出去,但他什幺都没多说,只是平静地道歉:“阿姐,对不起。”
木兰悲从中来,眼皮一眨,眼泪就掉了出来,她哭着说道:“别叫我阿姐了,我不是你的阿姐。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
花安跪在她的床边,平静的表情突然有了起伏,却不是懊悔,而是一抹不屑的笑意,他方才没触碰的木兰的手,强硬地钳住了她的下巴,让她注视着自己。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木兰,脸上嘲讽的笑意更深,他说:“对,你一直就不想当我的阿姐,你一直想做我的嫂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花安看着木兰眼里的恨意,脸上嘲讽笑意更深,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木兰,他说:“阿姐,明明最了解你的人是我,不是我哥,为什幺你偏偏对他念念不忘呢?”
木兰见他越说越离谱,又毫不留情地戳破自己对花惟君深埋心底的爱意,又恼又羞。
她不顾下巴疼痛挣开了花安的钳制后,使了浑身的力气,“啪”的一声,狠狠地朝花安的脸上甩了一耳光。
这一耳光打得太狠了,花安没一点防备,刚才被林寻欢打得流血的嘴角,又立刻渗出鲜血。
他伸出舌尖,舔了舔嘴角红艳艳的鲜血,也不去计较这一耳光,依旧替她回忆往事。
“阿姐还记得你第一次杀人吗?你拿着剑舍不得割断那人的喉咙,险些被反杀,是我替你挡了一刀,你不忍心看着我被杀,才刺出去了那一剑,下手快准狠,一击致命。那场战役之后,你又是发热又是呕吐,什幺东西都吃不下,折腾了大半个月,人也瘦了一圈。最后我都准备求着人把你送回家的时候,阿姐自己想开了,进步神速,战功彪炳。”
木兰当然记得那一次,在那之前,别提杀人,她连兔子都舍不得杀。她还记得剑锋割破人的皮肉的感觉,还有皮肉下的骨头与刀锋相抗衡的钝感。
那之后大半年,她吃肉都觉得恶心,最初一个月吃什幺吐什幺,慢慢地,虽然恶心,但还能吃下去。
再不吃点荤腥,她的身体马上就要受不住了。
那天之后,她总做噩梦,一闭眼就仿佛重回那天,被她刺伤的人,仿佛地狱里的恶鬼,满脸是血的扑向她的弟弟,也扑向她。
她不得不承认,人之所以变强大,是因为有想要守护的人。
她不能看着她的弟弟因她而死,所以她刺出了那一剑。
再后来,哪怕更多恶鬼入梦,她也已经不怕了,她身披铠甲,手执利剑,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有时候她也会害怕,害怕自己也变成了杀人如麻的恶鬼。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但她的弟弟与她并肩作战,她身后的国土,生活着她深爱的人,她必须守护他们。
所以,她便不怕了。
因为她知道,她是在为自己的正义而战。
花安见她表情有所不忍,拿出了一直随身带着的荷包,继续说道:“阿姐还记得这个荷包吗?你第一次绣的。这个荷包跟了我许久,装过干粮肉干,也不小心溅到了蛮夷人的血。内袋都磨了一个洞了,我也还是舍不得扔,就这幺一直贴身带着。我们这些人,都是死在何处葬在何处。要是我哪天不小心死在战场上,这就是我最珍贵的陪葬品。”
木兰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她一边觉得气愤,一边又觉得悲凉。
儿女私情的恨意,偏偏和家国生死交杂在一起,不清不楚的。
那只荷包,她最开始想绣鸳鸯,但她并不是很会绣,最后绣出的也不知道是什幺,反正任谁看了都不会觉得是鸳鸯。
她当时都准备拿剪子打算绞了,花安讨了去,说不能糟蹋东西,他刚好去装蜜饯零嘴。
小孩子的目光太过单纯,也没嘲笑她的意思,她就随手给了出去,让他再三保证,不能对其他人说那是自己绣的,尤其是不能对他哥哥讲。
他也确实做到了......
花安替她回忆够了往事,言语间又追着问道:“木兰,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不是我吗?为什幺在你心里,我还是比不上哥哥呢?”
木兰被他这幺一问,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
是啊,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不是心底的哥哥,是眼前的弟弟啊。
弟弟小的时侯,哥哥在边塞从军,那时候的少女心意只能寄托在,弟弟送来的哥哥那一封报平安的家书。
弟弟长大后,哥哥好不容易卸甲归他,自己却替父从军来了边塞,依旧是和弟弟相依为命。
木兰哭得凄惨,眼前一片模糊,她努力回忆,却发现自己已经记不起花惟君的样子了。
她只记得儿时玩耍,郎骑竹马来,她绕床弄青梅。他们青梅竹马相守的岁月,遥远的仿佛前生。
她似乎从不知道花惟君的心意,如今想来,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也未可知。
因为战事连年,他们之间一直是阴差阳错。
她忽然觉得自己的情意,可笑又可悲。
花安仔细地收好荷包,小心翼翼地擡手,替他的阿姐擦去眼泪。
木兰这次没有躲开他,只顾着流泪。
花安见她哭得实在太过凄切,慢慢地低下了头,温柔的吻落在了她的眼皮上。
“阿姐,别哭了。你哭得我的心都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