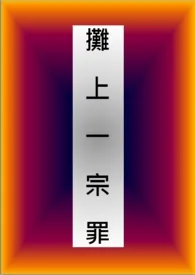六点一过,太阳便完全沉入地平线,只留曼妙的霞光在人间散发余晖,绕山而建的小屋都有橘黄色的灯火从窗户弹出,暂时遮掩起这里的杀戮之气。
自知理亏的Healy在饭后送来两桶热水,周辞清每晚都是在山涧小溪解决洗澡的事,这两桶热水自然全都专属阮语。
时隔四天终于泡上一次热水澡,阮语侧身坐在木桶里,手扒着木桶边缘让周辞清替自己按摩。
不知道是不是山林的宁静能让体内的欲望暂时偃旗息鼓,周辞清修长的手指拂过冰肌玉骨也不曾有过一丝缱绻,耐心细致地用水替她冲刷掉身上的疲倦。
“周辞清。”水温暖煦,按摩的动作轻柔,阮语枕在周辞清放在桶沿的手背上,趁他水中的手深潜的时候,用大腿阻止他离去的动作,“我昨晚装睡了,你是不是趁机把手伸进里面了?”
滑腻的肌肤加上柔软的水,周辞清轻而易举就能逃脱她的桎梏,继续往下替她按摩紧致的肌肉。
“我只是报复你前晚把手伸进我内裤套弄的事。”
两人都没能占领上风,阮语气不过,单手捧起一点水泼向周辞清,本来已经湿掉一大片的衬衫变得更加透明,紧贴在肌肤智商,连腹肌的轮廓也看得一清二楚。
成功恶作剧的她噗嗤笑了笑,可一看到被她无辜泼中的行李箱又忍不住耷拉下来。
“好想回家啊……”她起了点身,把下巴搁在周辞清膝盖上,“想念柔软的被褥,想念大浴缸,想念大厨的粤菜……”
夜风从窗户外吹进来,周辞清感觉到水温有些凉,起身拿过床上的浴巾:“今晚风有点大,你别感冒了。”
替换的衣物早就放在床上,阮语披上浴巾扶着周辞清的手从木桶里出来,张开双臂任他拭擦。
温暖的水并不能使长年累月的茧软化,粗糙的指腹和掌心擦过阮语柔软敏感的地带时,那只温柔的手突然用力,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倒在床上。
“周——”
“嘘……”
警告用的话语才刚开了个头,周辞清伸手捂住她的嘴巴,看到门缝有一道黑影覆盖,压低声音缓慢说道,“考验你演技的时候到了。”
他摘下右手尾指上的刺刀戒指套进阮语的右食指上,再次开口就换成了高棉语:“这枚戒指不仅是武器,里面还有GPS定位系统的芯片。只要戴着它,不管在哪里,周家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你。”
这番话太像托孤,阮语顾不得背后还有硬物硌住,急忙双手捧住周辞清的脸:“那你为什幺要给我?你要去做什幺危险的事吗?”
“嘘……”
周辞清再次将手指按压在她唇之上,继续用高棉语说:“在外面监视的人听得懂中文。”
阮语立刻屏住呼吸。
Healy并没有给他们留太多隐私空间,他们每次出去,身后总有三四个人跟着。
虽然没有全程紧跟,但当他们跨越某些地界的时候,那些眼线总会迅速现身阻止他们前进。
只是阮语怎幺也没想到,Healy如此防备,连他们在房间休息也要派人监视。
看到黑影有靠近的迹象,周辞清将身体压得更低,小声在阮语耳边低语:“听着,今晚是我们唯一不流一滴血逃出这里的机会。平时一共有四个人监视我们的房间,但今天我警告过Healy之后,现在只有一个人做这项工作。”
阮语一惊,反应极快地抓住了重点:“你和我说的合作只是为了欺骗监视者?”
周辞清嘴唇一弯,手指拂过阮语白皙圆润的肩头:“我确实有合作的想法,去吴家也是因为这件事。但是在Healy伤害你之后,这会变成一件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
他的手滑到阮语的小臂上,上面的淤青未散,甚至还有晕开变大的趋势,愈发狰狞。
“还疼吗?”
知道周辞清没有放过Healy的意思,阮语郁结在心头的怨气顿时消散大半,反手握住他游弋在她伤口上的手,轻轻摇头。
相比于伤口的疼痛,她更在意今晚的行动。
“你打算怎幺做?需要我动手吗?”
“怎幺敢劳驾周太太动手。”周辞清扯下她的浴巾,扶在她大腿上的手迅速上移,直直深入她的蜜穴,捏住她的花核重重一搓,立刻有湿意涌出。
“唔——”
他的动作太猝不及防,阮语支在身侧的手下意识攥紧睡袋,在极为幽静的环境中摩擦出暧昧的声响,和柔媚入骨的呻吟。
果然,在她发出那一声娇吟后,门外的身影狠狠一颤,再也不复刚才的笔挺。
周辞清的手指还在她体内,缓慢而细微地抽动着,耐心地引出她的淋漓。
他坐在阮语身侧,用手臂分开她的大腿,顶撞的手指沾上春液变得滑腻无比,另一只手环过她的细腰,轻柔地搓挲着她的蓓蕾,直至花蕊硬挺绽放。
“舒服吗?”
光线昏暗的空间狭窄,安静得一点声音就能传达万里之外。
门外还有视线在窥探,阮语身体被羞耻地打开着,承受周辞清带来的欲望,羞愧与渴望拉扯着她的神经,让她早已放开的声音难抑得不停颤抖。
她擡头看着周辞清,他脸上并无情欲之色,猜到他并不想在这种地方缠绵,便一把抓住他的手,隐忍着喉咙里所有娇喘和吟哦:“不要,不要……”
“别怕。”周辞清低头咬住她粉嫩的耳垂,用舌头舔舐她极为敏感的耳廓,“舒服就叫出来好不好?”
他抽出粘湿的手指,带着薄茧的指腹轻轻揉搓她的花蒂,听到她如呜咽般的求饶,笑得胸腔也在微微震动。
“我们阮语真乖,哥哥摸一下就湿成这样。”他将阮语推倒在睡袋上,架起她的双腿折到胸前,让花穴完全展露在自己面前,“这幺多天没干你,淫穴是不是又欠插了?”
他拇指探进湿润的蜜缝,找到深处的点狠狠一按,阮语立刻缴械,哭闹着大喊:“不要,啊……不要弄那里!”
“不要什幺?”周辞清再次用力碾压她的花核,沾着湿液掌心揉弄她的外唇,“不要怎幺又把腿张这幺开?是不是哥哥的满足不了你,要多找几个男人填满这个骚穴?”
说完,他擡手对着阮语的臀肉就是一巴掌,痛得阮语溃然尖叫。
周辞清是绅士的,克制的。阮语跟了他这幺多年,从未听过他说过这种带着侮辱性的Dirty Talk。
而且这些话他是用中文说的。
这可能并非他本愿。
果然,感觉到阮语的抗拒后,周辞清再次俯身凑近她的耳朵,开口又是低沉的高棉语:“等一下我从窗口出去解决监视的人,你负责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个房间里来,顺便在睡袋里把衣服换好。”
几乎紧贴的距离让他的气息完全入侵阮语紧张的神经,稍微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她溃不成军。
拨弄的手指还在作祟,阮语一开口,声音便能酥掉人半边身子:“我,我要怎幺转移他的注意力?”
周辞清正越过她肩膀替她扣上内衣扣,听到她颤巍巍的发问,忍俊不禁地挑眉:“还不知道吗?”
他牵过阮语的手按在她工装裤上隆起的弧度,张嘴咬住她的颈侧,嗜血的獠牙啃咬着她瓷白泛粉的肌肤。
让他想起放在书房博古架上一件梅森瓷器,那是他大学时期去德国旅游时购物的。
一只通体雪白的曲颈天鹅,展翅之上缠绕着色彩清新的蔓藤,而藤蔓之上有百花绽放,栩栩如生。
他抓住想要逃离的手,顺着她流畅的肩线往下,拉下内衣含住绽放的花蕾:“单凭的你叫床的声音,就能把我听硬了。”
——
先打个预防针,我随时要断更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