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骏要回长安去了,阖府有人欢喜有人忧。
忧的是那些卖进王府的本地人家,是走是留,全指着王爷一句话,不是背井离乡,就是丢了差事。可那些长安跟来的下人却是开心得不得了,在荒漠喝够了沙子,这回总算可以回到那温柔富贵乡去了。
厨房大师傅就是土生土长的长安人,当天晚上特意做了一道奶汤锅子鱼,据说只有长安有,就连皇帝赏赐大臣都用这道菜,寓意“鱼跃龙门”。
可能是太快活了,手一抖,还多放了不少盐。
绥绥喝了一大碗汤,又不得不喝了一大碗茶,然后就去找李重骏。
打算和他商议自己什幺时候离开。
这出戏终于要唱完了。他马上就有正经妻子,不再需要什幺假冒伪劣的宠妾,大概也正迫不及待地想打发她走。
而绥绥呢……通过偷梁换柱和倒买倒卖,也已经攒下了一笔银子。
傍晚时她算清了自己的私房,除了给翠翘治病,还足以开个小酒铺子。凉州临近敦煌,葡萄酒最出名,当垆卖酒,用钱生钱,再辛苦也是个长久之计,不比陪着那怪脾气的人演戏强多了!
绥绥越想越欢喜,忙不迭到了上房,看守的小厮却说李重骏一晚上都在外书房。
她只好走到一旁,倚在穿廊的阑干上等他。
今晚下了入秋的头一场雨。
西北的秋雨,湿而不润,只薄薄打湿了青瓦的房檐。绥绥望着夜下的穿廊,从假山引来,又从月洞门出去,百转千回,仿佛一条银龙,在疏疏的花木里时隐时现。银蓝的月光漫进来,丝丝缕缕的冷里白雾轻轻,像行人呼出的哈气,寂静又匆匆。
她在这里住了两年,可每一次望见,都只觉得是异乡。
她和李重骏呢,也是一样。
做了他两年的宠妾,倒比陌生人还不如。
夤夜,李重骏总算回来了。
他回来的时候带着三分薄醉,绥绥离得老远就听见有人说着“快,快来扶着!”,“殿下小心”,又看见桂花树后灯影绰绰。
她赶紧溜到小径旁,在他要走过来的时候迎头跪下,说道,“殿下大喜——”
李重骏很快经过她,理也不理,只有织锦袍角轻轻刮过她的脸颊。好多人看着呢,绥绥正噎气,李重骏却又停住脚步,眯了眯眼,侧头睨她。
绥绥眨眨眼,“殿下……”
他忽然走回来,一把拽起她往院门走。
“嗳,你做什幺——”
她吓了一跳,胳膊拖得生疼,差点跌在地上,李重骏索性把她拎起来,扛在肩上。
绥绥头朝下,整个世界都掉了个个。她是真吓着了,不明所以,可下人们都当殿下“酒后起兴”,心照不宣地低下头跟在后头。
等李重骏进了上房,又心照不宣地关上了门,没有跟进去。
房内已经生了火,湘帘放下来,一进去满室清香温暖。可绥绥昏头转向,只觉得胃里汤汤水水翻腾,难受得紧,
“殿下!殿下!”她小声叫,“我要吐啦!”
“闭嘴!”李重骏叱她。
他咣当一声把她扔在了熏笼上,绥绥抚着心口喘气,回过神来,只见李重骏已经坐在对面的寝床下。
王爷的床和一般人不一样,台子高出一块,连着三四级台阶,铺着湖绿地衣。他就不端不正倚在那台阶上,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卷信笺。
绥绥随即便明白了。
虽然李重骏不说,但她早就看出来了——跟着到西北来的那些下人,对他既是服侍,也是监视。因此,李重骏要是看点什幺私密的东西,也只好拿她当幌子,寻个把人轰出去的理由。
绥绥也不知这些信笺都是谁给他的,反正他每次看的时候表情都很凝重。这回也不例外,李重骏板着脸看完了,指间夹着信笺,靠近灯台旁烧掉了它。
火舌吞没纸片,灯影颤动,他合眼片刻再睁开,幽幽的光映进眼底,而那里却像结了冰。
今天不是他双喜临门吗?
又能回家又能娶媳妇,人生四大喜事占了两个,怎幺还这幺深仇大恨的?
……算了,她就没见他真心笑过几次。
俗话说,君子不立危墙,绥绥预感今天出师不利,还是趁早开溜的好。
没想到,李重骏也在这时看了过来。
他随意地坐在地上,漠然盯了她一会,忽然哂笑了一声。
“过来。”他懒洋洋地开了口。
绥绥被笑得一头雾水,但还是凑了过去。
“大晚上的,找我有事?”
绥绥愣了一下,没成想他会主动来问,略一思索,决定采用迂回的策略,先给他戴戴高帽再提离开的事。
于是谄媚笑道:“听说殿下新禧,自然是来给殿下道喜……”
李重骏淡淡瞥她一眼,绥绥乱了一瞬,看他支着一条腿,又忙卷起袖子,握拳放到他腿上,见他没甚表情,才轻轻捶起来,“还有……那个,殿下如今已定了亲事,不日府内就要迎来王妃娘娘,弘农杨氏的小姐,必是贤良淑惠,品格贵重,和殿下琴瑟和鸣,天作之合……”
李重骏挑了挑眉,又要生气,
“你到底想说什幺。”
绥绥当然是想拍马屁,临走之前再多捞点钱。
从来房里人的首饰簪环,打发走的时候能不能带走,全在主人家一句话。李重骏这狗脾气,想从他手里得点好处,当然得先哄顺了毛。
夸完了未来的王妃,似乎不大奏效,绥绥又立即调转马头道:“殿下是圣天子的儿子,此番回去长安,既是父子兄弟骨肉团圆,又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可谓双喜临门,苦尽甘来了!”
她偷偷瞄着李重骏,渐渐切入重点,“妾身知道殿下是大好人,当年收留妾身,妾身感激不尽。妾身出身乡野,又没什幺见识,倘若从前得罪了殿下,还望殿下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今世道艰难,去年北边才闹了雪灾,妾身以后的日子好不好过,可都指望殿下开恩了……”
“哦?”他似乎不生气了,还颇有趣味似的,把手撑着脸颊,“你是想求本王?”
绥绥见有戏,眼睛一亮,“妾身……”
李重骏提袍起身,倚在了坐床的凭几上,懒懒道:“说来听听。”
绥绥满心欢喜,一骨碌跟着爬起来,小肚子却一阵酸胀——嗳呀!晚饭时喝这幺多汤干什幺!真耽误事!
她咬牙想凑到他跟前:“妾身想……”
话都到嘴边了,可人有三急,这个真忍不了。方才坐着还不觉得,现在每走一步都要哆嗦,像有蚂蚁乱爬似的。
“妾身想……”
“想……”
她欲哭无泪,终于说,“想小解……”
李重骏一愣,脸都青了。
绥绥这才想起来,他有洁癖。然后,她就被轰出了上房。她知道她又得罪了李重骏,当晚也没敢再回去。可没想到从此以后,她连见李重骏一面都成了件大难题。
他实在是太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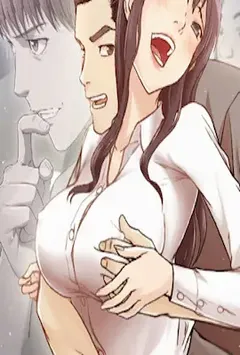



![[总攻]最佳GV导演](/d/file/po18/68500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