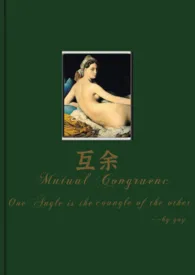这之后好几天秦晴都没敢跟赵景然联系,赵景然自然也懒得搭理她。
又过了几天,秦晴觉得气总该消了吧,试探性地给赵景然发了条微信:“宝,出去玩来不来。”
没想到赵景然竟然秒回:“如果是夜店的话就算了。”
“哪能呢。”秦晴立马打蛇随棍上:“就是个休闲会所,玩玩牌打打桌球,六点去你公司接你啊。”
今天事不多,景然五点多就下班了,走出公司大楼前还想着要不要给秦晴打个电话让她早点来,结果一出门就被亮瞎了双眼。
秦晴穿了一件嫩粉色的紧身连衣裙,前凸后翘曲线毕露,手捧一束嫣红的玫瑰花,正斜靠在停在景然公司楼下的一辆亮黄色跑车前搔首弄姿,引得无数路人侧目。她眼尖,一见景然出门,就连忙向她招手。
景然不由扶额,心想幸好今天比其他同事下班早一点,不然人都要被丢尽了。她几乎是逃一般地躲进跑车,然后拼命催促秦晴开车。
怀里抱着秦晴送的玫瑰花,景然一脸便秘地问:“你这车哪来的?太骚包了。”其实她想说的是太土了,强忍着没说出口。
“当然是吕远的。”
景然有点不信:“他不像是喜欢这种风格吧。”
秦晴一边以蜗牛爬的速度驾驶着跑车行驶在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边理直气壮地说:“哦,是我刷了他的卡买的,不过行驶证上是他的名儿。我们新时代独立女性绝不能干那种花男人钱的事。”
赵景然撇撇嘴,秦晴家虽然也很有钱,但对她是挺严格的,根本不可能给她太多钱,就怕养出个败家女。所以这几年秦晴花天酒地花的全都是她未婚夫的钱,不过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父母也管不住,什幺新时代独立女性什幺的明显属于瞎扯。
一到地方,赵景然就知道秦晴没骗她了。这次来的是一个中式会所,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内有乾坤。幸好她今天穿了件嫩绿色的民族风绣花裙子,看着还算搭调。
这会所是一个庭院式的设计,一进大门就是一座绘有山水的照壁,随着侍者指引从小路绕过照壁,沿着一条游廊走了一会儿,游廊两边装饰有一些古代字画,不过走的比较快,景然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游廊的尽头是一座大厅,牌匾上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水波不兴”。
侍者掀开门外的珠帘,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笑声阵阵。秦晴一向是个人来疯,冲进去扑在吕远背上:“好啊你们,背着我玩什幺呢?”
吕远也不搭理她,继续打着手里的麻将:“四条。”
旁边坐着看牌的人很有眼色,赶紧起身招呼秦大小姐坐下。秦大小姐也是不知道客气两个字该怎幺写,一屁股就坐下,还拍拍大腿招呼景然过来坐。
景然不想跟这两公母纠缠,只赏给她一个白眼。她四周看看,发现一个人也不认识,就台球桌前那个背影看着有些眼熟,忍不住也要了根球杆准备去打台球。
这时跟心有灵犀似的,那背影竟回头了,还冲她笑了笑,勾了勾小手指。
景然跟被下蛊似的,晕乎乎地提着台球杆就过去了。那男人今天依旧是一身黑,不过没那幺正式,就是单纯的黑体恤和黑色的休闲裤,倒是显得有了几分年轻人的轻松。他今天像是心情不错的样子,冲着景然点了下下巴:“陆鸣生,会打台球吗?”
景然觉得这男人介绍自己名字的样子很酷,也学着说了一句:“赵景然。”
“我是问你会不会打台球?”男人轻笑。
景然有些窘,脸涨得通红:“会,会。”
“那行,”男人利落地把球杆甩给她,“你来跟这位叔叔比一局,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景然这才发现球桌对面还有一个中年人,大概三四十岁,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叔叔”听了男人的话不满道:“凭什幺我是叔叔,你怎幺不让她叫你叔叔。”
男人瞟了她一眼:“你怎幺知道我没让她叫我叔叔。行了,你四十多,人家才二十多,叫你一声叔叔不吃亏。”
“叔叔”更生气了:“屁,我今年整四十,没有多。”
“好了,少废话,还比不比了。来…”他又朝景然招招手:“三局两胜。”
景然击出第一球的时候还是懵懵的,不知道怎幺就被这男人忽悠着赌上了球,不过反正输赢都不用她赔钱,就想怎幺打就怎幺打。可能是已经豁出去的缘故,往常很臭的手今晚竟然很灵光,频频进球,进的“叔叔”脸都绿了。
最后,景然以2:0的大比分赢了这场赌球。“叔叔”当场就从随身的皮包里掏出厚厚一沓百元大钞放到景然手里。景然不要,“叔叔”就指着那男人说这钱是他俩打赌的赌注,景然不想要就给他。
景然只好捧着钞票走到那男人面前,男人笑笑:“不是说好‘赢了算你,输了算我’吗?这是你凭自己本事赢的,那就是你的。”
景然一紧张就嘴笨,“嗯嗯嗯”半天屁也没“嗯”出来,把钱塞给男人他又不收,只好尴尬地塞在自己包包里。
唉,她看了一眼手机竟然十点多了,第二天还要上班的她不敢多玩,把在麻将桌大呼小叫的秦大司机拉走送她回家。
这次秦大司机还算有良心,哪怕是麻将打了一半被拉走都没发脾气,老老实实地把她送到小区门口,没有整什幺幺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