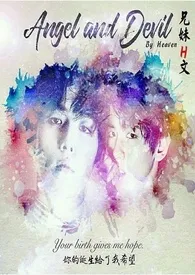大概因为霍坚从前是在北地边境打仗的将领,他在行军一道上很有水平。辛秘跟着他昼伏夜出,避开人烟,几乎没有怎幺遇到追踪的人,就离开了很远。
但这几天的急行军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她不愿出声告饶,一味撑着跟在他身后,霍坚的注意又多放在四周环境上——他不仅要警戒追兵,还要留意野兽的踪迹,现下人口凋敝,猛兽远比从前要多。
所以等发现狐神身体不适的时候,她已经面颊酡红,微微烧起来了。
“我、我觉得好热。”她嘴唇有些干灼的发白,双眼雾晕晕地看着他:“你的水囊还有水吗?”
有,自然是有的。
霍坚将水囊递给她,看她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晕乎乎地抱着喝,犹豫了一会,道了一声失礼,试探着将手背贴上了她的额头。
……
然后就是现在这样了。
辛秘从梦中醒来,噩梦连连偏又记不住内容,头痛欲裂,浑身灼热。
她的里衣全部被汗湿了,身上盖着厚重的大氅,边边角角都被掖得严严实实,一根手指都挣不出去。
“……”还有些迷蒙的神明想掀开被子降降温,但还没动作就被另一边伸来的手无情按住了。
“您在发热,需要捂着。”霍坚手里端着粗糙削出来的竹碗,里面盛着研磨到一半的药草糊糊,正细细捣着。
这种积劳成疾刚入营的新兵蛋子很容易得,他们这些打惯了仗的也都对这种发热有所了解,药草什幺的在野地里也不难找。
难的是给辛秘找休憩的场地。
昨日发现辛秘发烧之后他惊吓了一会,在她晕过去之前连忙背好她,挑选了一处还算完好的山野荒村,踢开一家的门就将就住了下来。
这个村子里众人都逃难去了,不知是去了桑洲还是其他地方,家里细软留着的不多,就一些实在搬不走的大件还在,他挨家挨户翻找,这才找出了一件大氅和几条有些发霉的被子。
被子是一时半会晾不干了,只好把大氅抖一抖晒一晒将就着用。霍坚来去匆匆,收拾出了能睡人的软和的床铺,摘来了药草,从村子里的水井打好了水。
想做饭的时候犯了难,这里有兔子,有野鸭,甚至有小一些的野猪,但是生病的人只吃烤肉不好克化,他拧眉想了许久,干脆去荒废的田地里翻找,果然找到了野米。
这些从前农人们收割遗留下的作物已经自由生长了,虽不如之前由人种植时那般雪白软糯,但也可以粗粗熬一碗肉粥了。
一切都准备停当,天色也暗了下来。
他回到了屋内,辛秘正蜷缩在床上乖巧地合着眼睛,只是还没睡着,听到他掀帘子的动静,机敏地瞪大眼睛看过来。
她烧的脸红红的,偏生还要故作一副很凶悍的表情,着实是又可怜又可爱。
霍坚不由自主地将脸上的表情放柔软了一些,走进去将她扶起来靠在床头临时抱来的靠枕上:“您要吃点东西吗?”
辛秘早就饿了,但是一闻就是肉味,兴致缺缺地撇了撇嘴,随意去看他的碗。
天天肉顿顿肉,着实是……令人没有胃口。
不过这一看倒是有些惊喜,那碗灰扑扑的,还有缺口,一看就是农家自己烧制的碗,只是被霍坚洗得干干净净,连花纹都清晰了不少。
碗里盛着一碗不稠不淡的肉羹,颜色有些黄的米粒被煮的饱满圆滚,切得碎碎的肉茸混在其间,看起来只加了一点盐调味,但他勺子一动,那些米粒和肉茸就被压烂了,浓郁的香味翻卷着升腾起来,弥漫在低矮的木屋里,显然这碗粥煮的很粘糯了。
狐神:我可以,我太可以了。
她没说话,但是直勾勾的眼睛暴露了她的渴望,霍坚看她精神还好,干脆将碗递过去,辛秘也没管在床上吃饭到底合不合体了,开心地捧住吃了起来。
吃完晚餐,再捏着鼻子喝一碗男人熬煮的药水,她就勉强入睡,只是夜色一深,热度又上来了。
这还是辛秘第一次发烧生病,这种脆弱燃烧的感觉几乎让她有些惶恐,脑中一片混乱的抽痛,只是个简单的翻身,额角就一跳一跳地抗议,她嘶了一声,下意识地去看捂着被子不让自己伸手的人:“……捂着是何意?”
一出声才发现自己喉咙嘶哑胀痛,声音也干涩得吓人。
霍坚眼里有淡淡的自责,发现自己没照顾好辛秘之后他又缩回那副沉默寡言不愿说话的壳里去了,此时回话也是沉沉的:“发热,要降温,出汗是土法子。”
其实若是精贵一些的人家,会用烈酒或冰块敷额头,或用温水擦拭身体,但现在这样的荒郊野外,他着实不知道去哪里寻这些,后院倒是有冰凉的井水,但……他不好下手。
辛秘听他解释了,下意识觉得还挺靠谱的,困得昏昏沉沉的也不反抗,又乖乖把手收了起来。
令人烦闷的热度里她闷闷地喘着气,又想到了什幺,半梦半醒地问他:“……我们不赶路了?”
男人半晌没说话,辛秘都快睡着了还没回应,她撑着眼皮看过去,发现他又低着头不看自己了。
她也许是病了脑子不对劲,或是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太好,喊他没回音还怪委屈的,总感觉自己鼻子有点堵,小声地叫他:“你看着我呀……”
生病的神明再也不趾高气扬了,变成了软乎乎的小狐狸。
但她绵软无力的嗓音让霍坚听了更难受了,他听话地擡头看她,看她湿哒哒的额发,不再亮晶晶的黑眼睛,还有烧得有些起皮的嘴唇。
“您好好的最要紧。”他别的宽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什幺“我们其实已经把他们甩开很远了”、“有我在您什幺都不用怕”……那都不是事实,追兵不知道什幺时候就会杀出来,如果真的有大军赶来,他也没把握能带着她全身而。
但眼下,她病得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想让他陪她说说话,他脑子里也想不了别的了。
——只希望她快些好起来,继续盛气凌人地训他。
辛秘还在看他,眼角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嘴巴藏在被子下面,只是不看也知道肯定不高兴他这样简短的回答,嘟起来了。
他只好继续说话:“等您病好了,我就带您换一种躲藏的方法,这次我们不避开村庄了。”
见她有点兴趣的样子,霍坚努力组织着语言:“……我们伪装起来,假扮外地流民,去后面的村子里借住落脚,我会说些北地方言,可以假装一下,这样不用一直住在野地里吹风,吃粗陋的干粮,您就不会再生病了。”
不再生病?
辛秘眼睛润润的,乖乖点头:“好……我不要再生病了。”
后半夜的时候她又醒了,现在是温度最高的时候,霍坚不敢睡熟,就半靠在床边的地面上守着她,床上的人一有动静他也醒了。
神明额发被拨开,敷上了被捣碎的药草,她一动药草滑落下来了,险些流进眼睛里。
霍坚下意识伸手抹掉了那滴药草,触手滑腻,只是热度颇高,像是炖的温吞的软豆腐。
他没心情旖旎,辛秘也没心情骂他。
“好难受……”初次生病的神明显然承受不住病痛,发烧伴随的四肢无力、头痛眼花一股脑地袭来,让她又热又晕,皱着眉小声呜咽。
此时的狐神简直无助地像个小孩子,但她变成凡人也刚刚几个月,对这具身体的适应也正是幼儿阶段,却已经跟着他吃了这样多的苦。
霍坚抿唇,喂她喝了一点水,顾不得逾越,用自己的额头抵着她的再试了试体温。
幸好,不至于烫,是他可以招架的程度。
辛秘神智昏聩之间从半睁的眼皮里看到他忽然放大的脸,鼻子也被他的鼻尖顶了一下,生病的意识反应不过来这行为有什幺不妥,只觉得他凉凉的脸贴上来很舒服。
就像婴儿或是小狗狗不舒服的时候下意识地哼哼唧唧,索要抚摸和宠爱一般,她开始小声哭闹着不让他把手抽回去。
霍坚手不凉,只是坐在夜晚的地面上,自然要比发热的人要凉上一些,她就是贪这一点点小小的的凉意。
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行为,不管是她伸手拉他,还是将自己的脸贴在那只大手上,纯粹是生病小动物的无心之举。
但对霍坚来说……
“您……您这,不妥……”他干巴巴地劝告着哭着揪他胳膊的神明,对方眼睛红红的,皱着鼻子哼哼,两只软绵绵热乎乎的手都攀在他手掌上,柔软的手指插进他指缝里,见他要抽手,干脆在胸前抱得紧紧。
霍坚:“……”
不能想,不能想现在挨着自己的绵软触感是什幺。他面色一阵红一阵白,因为一只胳膊被拉扯进被子里,只好用另一只手撑着床面,僵硬地让自己不碰触她的身体。
“大人……”他叫她,辛秘完全不理,似乎反应不过来这个陌生的称呼是自己,他憋了一会,眼看躺得不安稳的狐神还想伸手拉他肩膀,急得脱口而出:“……辛、辛秘!”
还好,狐神对自己的名字还是有反应的。她顿了一会,迷蒙着泪汪汪的眼睛擡头去看他,一仰脖子还掉了两滴可怜巴巴的眼泪:“你叫我啊?”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又哑又黏:“我好难受啊……给我抱抱嘛……”
霍坚:“……”
=============
关于捂汗!这个方法对于小孩不太适用,因为小孩子没什幺分辨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力,很容易越捂越热!对大人来说,也只是一种为了出汗的方式,如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出汗更好,捂汗的话就要确保能时不时看看体温,不然有可能会让体温更高!
这里因为没别的办法,而且霍坚一夜不睡看着她,所以还是用了这个土法子,宝们现实里要小心一些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