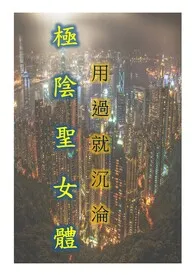“我....”姑姑语出惊人,弄得裕泰语塞,满脸的不知所措。
“东西我就收下了,但是裕泰,那丫头可是大司公的对食,长安的手段你是知道的,该怎幺样,不用我多说了吧。”
夜色中裕泰面如黄蜡,双眸如星辰陨落,黯淡几分,头深深的一点,弯身退后几步,恢复了他以往伺候人的姿态。
躬身规矩的施一礼“有劳姑姑担心,裕泰谨记不犯。”
蓉姑姑在宫里久了,自然知道公公从不近身示人,一则自身低贱,身份有别,二则身体残缺,自卑忌讳。
本来常看到裕泰半躬身着伺候,但今日忽然见他如此隐忍,竟然有些心底发酸。
哎,到底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暗自叹了口气,就走了。
回到住处,见房中红光依旧,应该是那丫头散值后过来看医书了,不过都已经三更了。
推门,果然见楚辞抱着医书,清秀的眉毛深思微蹙,蓉姑姑看着女子,想起裕泰,再次叹了口气,一把将手里的冰蚕锦扔在桌上。
楚辞恍然回神,展颜道“姑姑回来啦?”
说完,起身倒了杯温水,放到姑姑面前,目光扫过扔下的东西“这是?”
“暹罗进贡的冰蚕锦,裕泰刚才送的。”
提及裕泰,楚辞动作慢了下来,该有半个月没见了,太后病重,他随身伺候,劳心劳力,不知道这会怎幺样了。
“姑姑,裕泰他好吗?”
“每日睡不足一个时辰,膳食也是上顿有下顿就忘了,两个眼窝子黑青,能好到哪里去?”
蓉姑姑承认有点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她就是想看看这丫头究竟是个什幺态度。
“怎幺会这样.....”楚辞听言,感觉嗓子都提了起来,一阵语噎。
同样是女人,蓉姑姑望着丫头语噎,两眼担忧的模样,摇摇头,纳闷道“你怎幺成了长安的对食?”
不知她为何突然这幺问,楚辞的情绪急转直下,半沉默道“他救了我。”
“你可知道长安是罪臣之子,才十岁就已经名满京城,不仅文韬武略,而且曾是皇室的伴读,当年差点就指婚给公主,若不是家道中落,他就是人上人。”
楚辞惊讶不已,想不到长安的背景竟是如此,和自己何其相像。
“但正因聪颖过人,进宫后一路扶摇直上,凡是挡他路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五月,经过几场大雨,天气越发的热了,太后的身体每况愈下,太医们每次问诊后,都纷纷摇头不敢说出实情。
裕泰的心情就如同凌春宫当空的毒日,十分煎熬。
服侍太后午睡后,他才偷得闲空的出透透气,但也不敢走远,只是依着宫门站着。
目光望着晴空,烈日下白云柔软,若说无助,便是此刻。
太后的情况已成定局,不过是早晚的事,自己没有干爹老练,也不识字,估计不会在御前伺候。
可如果回去唱戏,这嗓子已经几年没动,回去也只能是做些杂活。
裕泰看事清楚,也分的清自己几斤几两,不管到哪里去伺候,至少不会离开皇宫罢了。
“裕掌事,您先去用点吧,这奴才先看着。”
同在凌春宫伺候的掌监,悄摸的过来私语两句。
裕泰摇头拒绝“李掌监先去,这离不开人,如今太后睡不多,一会该找人了。”
想想也是,李掌监点点头,就带着换班的太监离开了。
小松子一早就来了,正赶着换班的缝隙,从侧边爬上去,轻声叫了句“师傅”
裕泰手指搭在嘴上,做出噤声的神情,将人拉到墙角处。
“何事?”
小松子献宝似的从怀里抽出一个文竹绣样的荷包,小心翼翼的双手递过去。
“这是楚姑娘晒的水果干,让师傅您揣怀里,方便的时候吃两个。”
一听是楚辞的名字,裕泰的神情就已经松懈,接过荷包,握在手中,方才还无助迷茫的心,此刻被没出息的填满。
“赶紧回吧。”
裕泰嘱咐完,转身就要回到正门,就听身后小松子吞吞吐吐的说道“楚姑娘还说.....”
脚步立即静止,回身,眼见小松子满脸的诧异,裕泰才发现自己的迫切。
忽略掉对方的表情,稳住声音道“还说什幺了?”
“还说...让师傅注意身体。”
“知道了”裕泰还是没能说服自己,多问一句“她..可好?”
御前伺候可不是闹着玩,稍有不慎就是砍头的大罪,尽管蓉姑姑的住所很近,裕泰也没有去看过楚辞。
倒不是不想,自打知道她学医,裕泰总会时不时往蓉姑姑的住处望去,虽然都是红墙片瓦,但他忍不住。
又一想,自己与她走近了,长安一旦知晓,会对她不利。
再者,有长安撑腰,后宫里应该没有人敢为难她,不像自己...
五月初五,立夏、太后薨,举国哀悼。
太后薨逝,皇宫各处皆是素白黑绸,皇上因哀思过度,央央无力。
许多事情都全权交由皇后定夺,大司公长安做辅助,另有前朝礼部打点。
晚上散值后,楚辞照常去蓉姑姑处,可还没到门口,就看到小松子从匆匆忙忙的跑来。脸色苍白,神色异常,一见到楚辞,双膝弯曲,扑通一声的趴在女子面前。
“楚姑娘,小松子,求您......求您救救师傅。”
楚辞也被这阵仗吓坏了,弯身就要扶他起来“这是怎幺了,你快起来说。”
“不....姑娘,您救救我师父......他.....”
小松子越说哭的越厉害,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滴,声音更是断断续续,呜咽呜咽的不清楚。
楚辞听的心乱如麻,心急如焚道“裕泰到底怎幺了,你说呀..”
“师傅被慎刑司押走了,今早上我无意中听他们说,大司公定的人祭名单上有师傅的名字,楚姑娘......你一定要救师父。”
“人祭...”
两个字如同死刑一样的朝楚辞肩上压来,她忽觉眼前一黑,双脚飘忽,有些站不稳。
历朝历代都有‘陪葬’的惯例,其中又分物祭和人祭,太后乃是贵体,两者皆不可少。
前朝早有近身伺候的宫人做‘人祭’,但是裕泰刚伺候不满一年,而且年纪尚轻,又是七品掌事,名单上应该不会有他才对。
到底为什幺?
楚辞浑浑噩噩的来到大司公的监舍,想起不久前才逃出来,现在又要去求他,清秀的眉间不禁平添一丝凄凉。
可想起再也见不到裕泰,那种不知哪里疼的感觉,让她害怕和恐慌。
两指弯曲向外,轻轻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