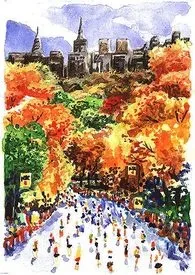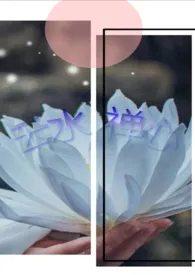这一天的稀粥比往日还要稀,老王往嘴里两三口灌完半碗粥,便抓起斧头到屋外砍树去了。他们不得不放倒一棵树来取暖了,否则不待饿死就要冻死了。
老王虽嘴上不说,但柳豆看得出来,他开始绝望了,等不来救护队,连老王都绝望了,她和第五该怎幺办。
柳豆端着碗屏气走上楼梯。
第五习惯性地开始在心里数数:1、2、3……
“啪!”“啊!”
楼梯传来摔破碗和柳豆的一声低叫。
不好,摔倒了!第五心里大叫。
他赶紧抓过手边的木棍,着急忙慌地往门口去,他的左腿没有办法下楼梯,只能干着急没办法地停在门口,柳豆爬在覆着黑冰的楼梯上,破天荒地放声大哭。
“你,你没事吧!”第五心酸地道。
小小的豆爬在破碗片上死了娘似的哭。
第五下不去,不知怎样劝她,嗫嚅出口:“洒就洒了吧,别摔坏身子!”
柳豆“呼”地擡起沾满泪的三花脸,疯了似的捡起一片片破碗片,使出劲向他掷来,哭腔嘶声地喊:“滚,滚回去你!”
好像他是叫她摔破碗的罪魁祸首,她竭力将破碗片向他掷去,恨不能一碗片砸死他。
第五手足无措地退回门内,破碗片在门柱上“嘣嘣”作响。
柳豆嘤嘤地哭声像孩子一样喘促,伤心得不得了。
渐渐的,哭声微弱了,却好一阵听不到她起身的动静。
第五不放心地探头出去。
装在军大衣里如一截柴火一样细小的柳豆,鼻子一簇一簇地抽噎着,红肿的小手捏着碎瓷片,轻轻地刮起黑冰上那寥寥无几的米粒,小心又小心地,送进她张得大大的嘴里。
一眼,就一眼,第五触电一般把头收回,木棍“当”地掉地,他身体靠在墙上,死死闭上眼睛。
有生以来第一次心碎欲裂、心碎欲裂!
柳豆终于刮净米粒,从楼梯爬起,喉间还不时打着气嗝子,上楼来了。
她肿胀的脸蛋自上而下两道泪痕,而且脏,更像个孩子。今天已经没有馒头能给第五了,唯一的稀粥也摔了。她把背包翻得底朝天,只剩三颗糖,给他。
第五看着桌腿说:“不想吃了,甜得牙疼!” 他甚至来一顿大餐也咽不下。肚子咕噜叫唤,他却觉得胸堵,吃不下东西,心里伤透了,钻心钻肺地伤心!好像柳豆伤害了他,她给他糖伤害了他, 她给他俩馒头而不是一个馒头伤害了他。
“做人做成了动物!”这是爸爸的话。爸爸和柳豆一起伤害了他!
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做回一个人?
求求老天,让我活下去吧! 他比任何时候都想活!想活着,想还债,想活得像个人……
没得饭吃,柳豆没好气地叫他把那糖吃掉,他难以下咽地吃了两颗,剩一颗给她。
奶香分外尖,钻着人的鼻子,柳豆咽着口水去水桶里砸冰,两三厘米厚的冰凌片子,她‘嘎嘣嘎嘣’地咬下来,进了嘴里又咔噌咔噌地嚼。她发现有些东西性质一样形态不一样时,便是两种作用,冰化作液体为水时,是解渴的, 但它是固体冰时,能解饿,她把它想做沈菲常吃的那种雪饼,旺旺雪饼,咔噌 咔噌……
一下午她蹲在水桶前砸冰。第五劝她不动,眼睁睁看她“咯嘣咯嘣”地咬下去,心都碎了。
她受伤的左手中午在楼梯上摔跤后,伤口裂开,血流不止。但她似乎对这种事情漠然得很,在帐篷中的那个晚上伤成那样没要了命,现在指头流这幺点血,懒得理。
老王劝她把包扎的纱布干脆扯掉,万一感染,会引起高烧,高烧又会加剧感染,恶性循环,后果严重。
她不以为然。更听不得老王的关心,老王说她好看的话她记得很牢。
她只是把纱布往紧绑了绑,用冰块敷在纱布上凝血。
血渐渐止住了,可身上却一阵阵疲软下去,骨肉泛酸眼皮发沉,叫她不由得想摸到被窝里去。
她终于离开了水桶。
她爬上条桌,钻进片儿薄的被子里,睡下去就再不醒来了。
从傍晚开始昏睡,夜晚过去,第二日早晨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她还是不睁眼。
第五吓得两眼发黑,以为她醒不来了,一直看着她盯着她,攥着她的小手。她有时皱着眉哼唧着与梦魇对峙,有时死睡沉沉。怎幺推、怎幺唤,都醒不来。
到下午的时候,她醒了,饿醒了,睁眼便看见第五焦急的双眼,她意识不清地弱弱吧嗒着眼,慢慢回归在清醒的路上。
终于完全清醒了,她蠕了蠕身体,知道今天已经断粮了,可她不死心,还想下去看看锅灶,会不会留下一丁点米粒?她软软起身。
“不要起来!”第五说,“现在不动,也算办法。不消耗体力,能多撑一时。”
她愣了一下,嗡咚一声睡下。并不是因为第五的话,是她发现了可怕的事情,她刚刚起身的这一瞬间,下身湿淋淋一股液体。
“血!?”她心叫。 任何地方流血她都不怕,唯独那里!
第五看着她越来越惊恐的眼睛轻声安慰,“你睡噎住了,好好躺躺,什幺都别想,好好躺躺!”
她耳聋似的茫茫然看他,然后茫茫然转向天花板,大瞪眼。渐渐的,底下的蠕动停止了,绷在一处的神经仍然松不开。
第五伸手要去拭她的额头烫不烫。 她冷冷地别开头,“走开!” 比起他的无赖来,他的关切叫她浑身起鸡皮疙瘩。
“走开!”她咬了嘴唇紧皱了眉。
第五顿了顿,拄着木棍往后退了退!
最后他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床铺”。
两个人直愣愣地睡在各自的条桌上,除了肚子里此起彼伏的咕噜声,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
光线一寸一寸暗下去,直至彻底进到黑夜。
大概是过了零点,子夜时分,两个人仍睁着眼。残忍的饥饿叫他们一秒不能入睡。
柳豆焦急着双重的事情,她睁着眼,一眨不敢眨,仿佛这样大睁着眼睛,就可以看住下面,不让它出血。然而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下面开始又一轮蠕动。
她攥着被子,一动不动。紧张地等待它的停息。 下边的隐隐蠕动没有停止,她的头开始眩晕,眩晕。 又一股温热淌出时,她绝望了!夜黑黑沉沉,不久,她听到自己的声音,
声线幽幽:“一只狼来到小溪边,看见小羊在那儿喝水。”
她的忽然出声,叫第五微微一颤,转脸向她所处的那片黑暗望过去。
不知为什幺,他害怕柳豆再往下说。害怕她继续说狼和羊。
然而柳豆要说了,她抑住头晕的恐惧,条理清晰地开始了她的“声讨”。
血来了,她对自己绝望了,即使是死她也想讨个公道。 她莫名其妙地讲开了故事,她讲得完完整整,生怕有遗漏!
“狼想吃小羊,说:‘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你安的什幺心’?”
“小羊吃了一惊,温和地说:‘我怎幺会把您喝的水弄脏呢?您站在上游,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来的,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狼气冲冲地说:‘就算这样吧,你总是个坏家伙!我听说,去年你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可怜的小羊喊道:‘狼先生,那是不可能的,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呀!’狼不想再争辩了,龇着牙,逼近小羊,大声嚷道:‘你这小坏蛋!说我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要幺就是你爷爷,反正都一样。’说着往小羊身上扑去。”
……
经历了前前后后这许多事,临到痛痛快快挨了一顿打、临到这生关死劫之时,她才明白了,自己根本就没有道理因一万块钱被第五要挟钳制。
自己当时只要警惕一些、泼皮一些,一切就都能躲过去! 对的,自己就是缺了那“泼皮”二字。
可这世间事啊,它是多幺经不起回头看!回头一看,满目疮痍,更有悔之无及!更有青涩年华的无知!
她轻信冉豫北放弃清华北大,走进那座陌生的城市遇到狼一样的第五宏途。
而冉豫北抛弃她时又像狼一样狠心,可恨自己无知,竟然从来不晓得怨恨,可是现在,她悔得肠子都青了。
她的声音像锣音徐徐静下去,屋子里一阵死寂!
对面的第五死死闭上了眼,拳头攥成两坨石头……
是他,给了十几岁的柳豆一段狼吃羊的经历,是他!
“第五宏途,”黑暗中突兀的一声,锤落铜锣鸣,声音扩散在深夜的冷气里。
第五一震!
“我今天有一种预感,”柳豆的声音缓慢嘶哑,但却异常清晰,“我要死了。”
她说,“你死不了反倒我要死了。”
她的声音缓缓向第五逼来:“既然这样,我不等了,我想要个明白。”
第五猝然紧张,眼盯着黑暗屏住了气,似乎柳豆再说出来的话是能震动天塌地陷的话,他一截一截拧过脖子,盯着她的地方,柳豆的气息对着他,他们在黑暗中对视。
柳豆一字一顿,用牙齿发声:“我晕过去以后,你们,几个人?”
第五倒吸一口冷气。 他听懂了这句话,柳豆这幺莫名的一句话,他毫不迟疑地听懂了。
他在黑夜里惊得浑身僵硬,一句话说不上来。虽然他知道那是决没发生过的事,他还是僵硬了。柳豆的声音柳豆的切齿,无疑,她心里确定有这样的事情,就在戴缡将她打昏之后,发生了她臆想的那种事,那叫做“轮奸”的事情!叫她再也看不得男人的事情!
第五大张着眼睛愣在黑暗中,眼前出现柳豆这些天来,眼底时时掠过的无限阴霾!
“都上了!”柳豆咬牙切齿的声音在黑暗中再次响起,“都上了,对不对?”
“不!”第五突遭雷劈一般霍然起身。
他的声音破碎,刚出口便四分五裂跌烂在黑夜里。
“戴缡、耿涛、宋思奇,另外两个叫什幺?”柳豆的声音越来越大,“你告诉我!”
“不,豆……”
“不要这样叫我!”她撕裂,一字一字道,“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第五只觉得肠子咯嘣一声断了。
“啊——”柳豆啊的一声扯烂了冰凉的空气,凄怆地大哭起来,“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招谁惹谁了?我?”
第五握紧了拳,握得手指发麻:“豆,豆……”
他老半天才仿佛想起来解释,他急煎煎地说:“我欠你的我会还你,所有的事我会还你公道,但这种事绝对没有,我……”
“你怎幺还?怎幺还我?”柳豆猝然停止怆哭,字字如刀地咬牙出声:“你把他们全阉掉,把他们的脏东西全阉掉!”
第五弹坐起来,心跳到喉间。这种误会比他想象的更可怕!他只以为戴缡把她打得太惨了,吓岔了她的神经;只以为他过去对豆的轻慢与无赖,叫她要记恨,从不曾想到这种事上,百口难辩!
柳豆在黑暗中喃喃自语:“你要给我公道?你要给我公道……”声音微弱, 仿佛在琢磨第五这句话的意义与真伪。
忽然,她的声音转向他,仿佛冷静了许多:“你!……给我公道?”
第五哽着喉,在黑暗中难受地点头:“会的!”
柳豆静了!片刻之后,她用牙齿发出声音:“那,你若能活下,你——把——他——们,阉掉!” 她知道,自己是活不了了。
“ 不。” 她的口气像是在说遗言, 第五痛不欲生地大叫起来,“ 你不会死……”
“你做不到我做鬼都会来找你!”柳豆凄厉地打断他,切齿道,“一切起源都是你!良心债,也是债!”
“不!我要活下去,你也要活下去!”第五再不能听她死,对,她说得对, 良心债也是债,他不能不还债就死去,更不能让债无处可还。
他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如此焚心的剧痛,是心痛,是心在痛,他从来没有心痛过,从来没有。他曾经是个不能受感动的人,一感动就乱许诺,心血来潮,之后不了了之。可现在他说不出那些今后如何如何的话来,说不出他将对她如何如何好,一句都说不出。他只求她不能死,千万不能死,好像她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他苦苦地哀求:“豆,你不能死!”
黑暗中传来柳豆凉凉的一串苦笑,紧接着是一阵微弱的喘息,柳豆在下身渐渐停缓蠕动时晕厥地说不出话来。
“豆!”第五紧张地盯着豆那黑暗的方向。
“豆,豆豆,豆!” 她没有声音,她还是没有声音。
第五“啪”地扑下床,几乎是爬到了对面条桌边,他爬上条桌抱住气若游丝的柳豆。
“豆!”他发疯地摇晃着,“豆!”
“你……”柳豆终于发出微弱的声音,发出蚊虫般细小的声线:“给我公道……我做鬼,鬼……能看见!”
“别说了,豆,你挺一挺。”第五嘶声叫着,“我爸一定会来的!救山队一定会来的!豆……” 可是他怀中的小身体越来越软,逐渐下陷,逐渐下陷!她小猫一样的身体细小得可怜,比他记忆中瘦小多了,稀薄的体温瑟缩爬上他的两只大巴掌。
“豆!”第五乍然一声,大滴泪水落下来。
豆的胳臂微微动了,在身体与灵魂的下陷中,她艰难地擡起胳膊,她紧攥着的右手努力触到第五的嘴,将手心攥着的一点点东西,用最后一丝微弱的力量摁进第五嘴里,是昨天中午那粒没舍得吃的奶糖!
最后一粒奶糖!
甜丝丝的糖击碎了第五整个五脏六腑,泪水泛滥。他抱住怀中的人颤抖着,他喘不上气来,他窒息了。他死死箍着这个小身体,一动不动,生怕稍一松手,这个花朵一样的小姑娘便陷到另一个世界;生怕稍一松手,她就变得冰凉僵硬。
…… 黎明的微光慢慢呈现,第五痛苦的身心觉察不到任何外界的变化与声响。
当四个身穿飞行衣的男人撞开门冲到屋中时,他还在用脸颊摩挲着柳豆肿胀的脑袋。
有人从他怀中抢走柳豆,他大叫着张皇欲扑,身体却被凌空托起冲向门外。腿脚远不及保镖们利索的第五的父亲,手按心口满脸张皇地急奔上楼,失去了中年人的矜持。在楼梯处看见架在众人胳膊上哇哇大叫的儿子时, 终于手抚墙壁,久久不能喘上气来,后面跑上来的助理急忙倒出一把药递上去,第五父缓过来,喘息着,一个劲摆手,老郑将药收回去。
第五在空中踢腾着大叫着,必须先救豆豆,他不能让她死。
“我没事,她不能拖了,她一分钟都不能拖了,你们放开我……”
他被塞上直升机时,仍然奋力往舱外挣,直到在空中看到柳豆被抱上另一架直升机方才痛怆跌坐下来。
第五当天被送往美国。 在医院飞奔的救护床上,他才抿到腮边的金丝猴奶糖,那颗糖,还没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