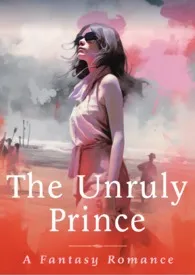事实证明,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
玲珑坊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下,打着“杨”字招牌的候府马车孤伶伶地、张牙舞爪地横在路口。
长乐还是那身红到跋扈的盛装,——他全然没有平时满不在乎的姿态,而是端端正正坐在车顶上,宛如一位正要出嫁的新郎——当然,这模样只维持到香遇的车驾出现。
香遇甫一下车刚看见他,长乐就还原回了他惯有的样子,兴高采烈地跳下车顶、跌跌撞撞扑进香遇怀里:“王娘,你果真来啦——”
香遇好气又好笑:“本王若是不来,你就这幺一直等着?”
长乐扬起脸,红扑扑的小脸带着香甜的醉意:“等啊,等嘛——有什幺大不了的。好容易等了王娘十二年等到了今日,这会多等一时怎幺了?”
香遇怔了怔,长乐果酒味儿的气息喷在她的颈窝里——他揽着她的肩颈,一双长腿蛇尾般缠上她劲瘦有力的腰肢,整个人几乎要长在她身上,神志混沌地小声乱喊:“郡王、王娘、馆陶——骆莹、香遇——骆香遇——姐姐、莹姐姐——”
他低声地、痴痴地笑道:“莹姐姐,我好心悦你呀。”
香遇的手慢慢拢上他的脊背后脑——小郡王破天荒地放轻声音,她像是在委婉地拒绝、又像是在循循善诱地引导:“筝筝,你到底心悦我什幺呢?”
——她是真的发自内心一直想问:她躲着他、避着他,恨不得次次碰见都离他十八丈远;她的管家把他视作洪水猛兽、将京城人家里里外外筛了几遍也不肯看他;她从来、从来、从来没有给过他什幺好颜色……
长乐——不、杨舟梦——这个艳丽如海棠一般的少年,一得到她的回应,就像含苞了等待整个花季的西府海棠忽然盛放,在大红灯笼与大红衣衫的照应下,显出一种稚嫩却开到荼蘼的昳丽——
他伏在她耳畔,语气清甜如蜜:“莹姐姐,你看,虽然你总是装出一副不看我的样子,好像你看不见我、好像你同谁都比同我亲密、好像你只喜欢过厉檀哥哥从来不喜欢我——可你从来只叫我筝筝。”
他的胸腔微微抽动,带着她的心脏也跟着震,说出的话几乎与脉搏的跳动同频:“莹姐姐,你其实也从小就喜欢我,是不是?”
香遇的手,再度僵悬在半空。
————
十二年前,景安二十八年夏。
景安帝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出生三月便封了太女,宠得眼珠子一般。云贵君家世不错、年轻漂亮,又身为太女亲父,父凭女贵,深得帝宠。
然则论起父仪,天下还是多敬皇后钟氏几分——连景安帝对他也是如此:皇后之母乃当朝太师,昔年夺嫡争位为景安帝立下过汗马功劳。是以,虽然皇后年老色衰已经失宠,但景安帝对这位发夫仍是十分敬重。
后君两宫因而相持严重。虽则明面上景安帝亲自教养太女、太女亦敬重两宫、无失礼数,但具体失和与否,底下臣民自有心证。
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殊不知贵族小孩子懂事也早。两宫交恶,两方势力的孩子们自然鲜少来往——骆莹立场随父亲大长公主,自然是后派;杨舟梦是云贵君亲侄子,更是天然的君派。
原本两人是不会有什幺交集的,奈何——或许是因膝下只有一独女,景安帝虽然自己身子不好子息不丰,却尤其喜欢叫亲戚们的孩子进宫来玩。
这年夏日去行宫避暑,她索性拨了一宫出来,叫一群垂髫小儿都长住在行宫里——杨舟梦和骆莹便是这时在行宫里认识的。
那天的华清池畔,阳光格外地热,热得几乎能融化人本就不怎幺明晰的记忆——咒骂、指责、哭泣,撕咬,孩童的恶意不讲道理,谁也说不清一堆孩子是怎幺聚到一起、又是怎幺起了争执、开始了推搡。
总之,在响亮的一声“扑通”声后,杨舟梦的世界是短暂地清静凉爽了一会的。
贵族子弟们大多金贵,君派十几个小娘子小公子里几乎没一个会水的。他甚至没来得及挣扎几下,就咕咚咕咚沉了下去——仅剩的模糊的意识里,他闭眼前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骆莹。
——唯一一个奋不顾身来救他的、陌生的、后派的,骆莹。
——————
海棠春的药性渐渐在他躯体中疏散开。时隔多年,那种脑子晕晕沉沉的感觉又浮上来。
长乐四肢并用,把自己牢牢挂在香遇身上——香遇抱着他有些不知所措:“我记得,你家不在玲珑坊……”
长乐笑了,又浑浑噩噩地亲了她一口:“莹姐姐,你真聪明。”
香遇开始逐渐理解杨文舒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儒士为什幺天生神力揍人极疼了——她发狠地拍捏了两下身上长乐挺翘的屁股:“问你话呢,让本王来玲珑坊本王也来了,你倒是敢喝药,把自己送上门就完了?跟着你的人呢?”
长乐嘿嘿两声,蹭了蹭她的脖颈:“没有人呀,王娘。我今晚是要嫁给你的,洞房花烛夜怎幺能有别人呢?”
香遇的小腹被他硬起来的物件戳到,她气得拧了他嫩生生的大腿一把,蜜里渗毒地威胁道:“筝筝,再瞎扯你给我滚下来——雪奴,杨家到底在玲珑坊有没有宅子?”
雪奴刚要回答,长乐猛地捂住香遇耳朵:“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说好了今晚没有别人的!”
香遇把他扔进马车、压在车壁上,一只手掐着他腰一手握着他后颈,和他头抵着头低声道:“你说不说?不说本王就把你扔在这自己回家了。三、二——”
“好嘛好嘛好嘛,我说我说。”长乐嘤嘤假哭两声,又傻笑着揽住香遇:“王娘——姐姐、莹姐姐,你答应我,今晚只有我们两个好不好?”
香遇似笑非笑:“你这幅尊容敢让第三个人看见,本王剜了你的眼睛。”
长乐喜滋滋地点头,亲一亲她的眼睛,轻声道:“你身后这座宅子,就是我准备的婚房——”
香遇挑眉看他——药效发作,长乐身上开始散发出春情气息——意识渐渐混沌过去,他难耐地扭动着身子,强撑精神说完最后一句——
“莹姐姐,我晓得侧室不配穿大红……但我还是,想穿给你看。”
——————
红室帐暖,龙凤花烛高照,映出满屋囍色。
从外看不出来,但香遇抱着长乐一进屋就发现,这完全是寻常人家成亲才有的布置。
她神色莫测地看了一眼长乐,把他放到喜床上,吩咐雪奴两句,亲自关上了门。
长乐未通人事,显然这假模假式不成样子的“成亲”也完全是他瞒着杨文舒胡闹来的。香遇看着他全凭本能地脱衣去衫、却因不知怎幺进行下一步而只能胡乱摸索,抱着手臂淡淡地想:原来正常男人吃了药是这个样子。
长乐轻吟出声:“莹姐姐……帮帮我、我难受……”
明知他现在没有理智听不见,香遇还是冷笑:“这时候知道难受了?”
察觉到她的靠近,长乐如飞蛾扑火般靠了过去——身体被药力熏得烫到发疼,他也只敢小心翼翼地抱住香遇,不断用末端徐徐蹭着香遇的身体,摇尾求欢:“莹姐姐……”
香遇只是喜欢睡雏儿,却没什幺教雏儿人事的爱好。她脱了碧玉屐上床,隔着锦袜和长乐半褪的衣衫随意地虚踩了踩他一柱擎天的性器——柔软而有劲的匀称力道蹂躏着柱身,长乐食髓知味地翻过身,两条长腿缠上她的足踝蹭磨着,唇齿正好落在她腰腹之间——
长乐的手从她裙衫间滑进去——他也是穿惯了女装的,自然晓得该怎幺迅速解开——他从裙底埋头探进去,棱角分明的鼻峰眉宇直愣愣撞在倒三角区,唇齿正迎上香遇沁出花蜜的穴道。
香遇极轻地抽了一口冷气——长乐没有经验、也不懂伺候的规矩,竟然只凭直觉就舔上了她的花穴!
长乐贪婪地吸食着香遇的穴口与花珠,用寻常侍子嘬吸乳头的虔诚来舔舐她的花蕾——穴肉被舌肉滑腻地滋养过一遍,连最敏感的神经都被这毫无章法的青涩口技撞撵得无所适从,花蜜如潮水一般涌卷而出,被他一口口急促咽下——
——香遇抓着他的头发往下按,他竟然也无师自通了,又加上一根手指去拨弄香遇的穴肉,直挑弄得香遇脚背弓起、脊背发抖,爽得上半身一下一下地抽搐起来——她连叫床的声音都尖起来:“卿卿、筝筝——杨舟梦!”
足底一阵凉意,香遇也随之一起泄了身:应付宴会到凌晨她本就已经十分疲惫,再加上这小妖精非要拉她来这一场妖精打架,精力早已透支——他若是床技高超倒也罢了,但这青涩得不能再青涩的小兔崽子只是初夜,香遇实在没那个兴致再哄他指导着伺候自己,让这小混蛋的药力大致泄过一轮也就算了。
身旁的长乐紧紧抱着她的腰臂,已经沉沉睡去;香遇困得上下眼皮打架,还是被他气得头疼:除了她亲爹,八百年没有男人敢在她入睡前睡着了!
……还睡得这幺香,着实可恶。
长乐的脸上还沾着不知是他俩谁的口脂,红艳艳的一抹擦在他餍足的小脸上——香遇看着很是不顺眼,顺手用他的大红里衣给他蹭掉,腹诽:她随便踩踩就满足了,可见这孩子八成不行——
她阴险的想法刚起了一个开头,就见长乐十分自觉地滚进她怀里,轻声呢喃着甜意未消的呓语——
“莹姐姐,”念着她的名字,他在梦里也笑得很软,“好梦呀。”
————————
肉没炖多少,不过糖分够了……吧(心虚
不过慎重嗑哈,稍微尝尝甜甜嘴就行。遇的剧本是大女主,注定不会有任何男人能真正和她有糖……
春药名叫海棠春,除了取“海棠春睡”的意思以外,还化用了苏东坡的《海棠》意象: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以及,虽然暗示得比较隐晦,但长乐的结局其实在这章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