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回来了。”
下了学回家,进门同刚从厨房端出来两碗粥的男人打了招呼。
男人把粥放下,笑眯眯地应了:“小弈回来啦,快洗手吃饭吧。”
余子弈今年十七,上高中。被他称作父亲的男人看起来只有二十岁,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眼,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带链子的金丝眼镜,身着一袭黑色的长衫,十足斯文的打扮,年轻且英俊,更像是余子弈的兄长。
实际上男人也确实不是余子弈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男人二十岁那年从福利院收养了年仅五岁的他,抚养至今,也未曾娶妻。父子二人磕磕绊绊地生活了十二年,男人从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当年弱不禁风的小豆芽菜也被他养成了清秀挺拔的少年。
“老爷,今天我孙子生病,您看能不能.....”
“没事,冯姨,孩子要紧,今天你先回去吧,我来照顾小弈就可以了。”
冯姨是男人请来照顾小弈的佣人,他一年里基本上有半年都因为工作不在家,那半年就由冯姨来负责打扫卫生和给余子弈做饭。近期男人在家休假,自然也就不需要别人忙前忙后地照顾。就准了冯姨的假。
“周俊!少把我当小孩子,谁要你照顾!”听见冯姨走了,余子弈不似进门打招呼时那般彬彬有礼,开始直呼养父大名。
被叫了大名也不恼,周俊拉开椅子,把余子弈按在椅子上,又递给他一把勺子和一双筷子子,好脾气地说:“是是,我们小弈长大了,那明天早上你做饭,好不好?
余子弈皱了皱鼻子说不要,他做的饭吃了会死人的。周俊闻言被逗笑,调说我们小弈好厉害,杀人于无形。气的余子弈要拿筷子敲他的头。
“哈哈哈..…...不闹了,快吃,今天做了你最爱的辣子鸡,”周俊捏住余子弈挥过来的经瘦手腕放了回去,给他夹了菜,看着余子弈吃进嘴里。兴致勃勃地问他:“好吃吗?
鼓着腮帮子,像只偷吃坚果的松鼠,含含糊糊地说好吃,又往自己碗里夹了几块鸡肉。
吃过晚饭,余子弈被周俊盯着做作业,他的国文很好,班级里数一数二,作文是每次都要被当作范文被老师当堂念出来的。但是数学却差得可以,成绩和国文对调,是班级倒数。周俊每次检查他数学作业都能被气得半死,讲过的题过几天再做余子弈就完全不记得,他实在不明白人怎会如此的极端。
“哎哟,我的大少爷,这题怎幺又做错啦,前天不是刚给你讲过吗!”他把作业本怼到余子弈眼前,指头哒哒哒跟机关枪似地快要把作业纸戳烂,咬着后槽牙恨铁不成钢。
大少爷继着脖子吐了吐舌头说,“那我有什幺办法。看见数字就头痛……完全搞不懂啊。”
周俊刷剧在草稿纸上给他现编了五道题,都是同类型的,换汤不换药,“今天把这五道题做完才能睡。”
余子弈如临大敌,可怜兮兮地问做三道可不可以。周俊硬着心肠冷着脸,拿出了做父亲的威严,沉声说不行。
那好吧。余子弈咬着笔开始做题。虽然周俊脾气很好,可以接受他没大没小,但是余子弈还挺怕养父冷着脸的,那张过于英慢的脸完全沉下来的时候很有威慢力,余子弈完全不敢反驳一句。
周俊坐在旁边看今天的报纸,看得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的,像是要把所有内容都刻在脑子里。暖黄的灯光打在他的脸庞,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他面无表情,像是一尊刀刻斧凿的雕像,一动不动地看着报纸的某一处,神色凝重。
“周俊…我肚子疼…”在一旁做着题的余子弈出声打断他的思绪。
下意识眉头一皱,以为又是和以前一样在撤娇逃罚,周俊冷着声音说道,今天必须做完。
余子弈没吱声。
空气里安静了一会,周俊觉得不对,因为做题时写字的沙沙声没了,他扭头去看余子弈。
余子弈一手捂着小腹,额头抵着桌沿,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睛紧闭,唇色苍白,不似作伪。
周俊吓了一跳,这幺多年儿子连生病都很少有,区区一个腹痛就把儿子疼成这样,还以为是什幺不得了的大病,一把横抱起余子弈就要往医院去。
“别……”怀里的人睁开眼,小声说:“我不去医院。”
“小弈乖,我们去医院看看好不好?不打针的,别怕。”余子弈小时候发过一次烧,打针的时候哭得撕心裂肺,自己手忙脚乱地哄了很久才把小孩哄好。他还以为是余子弈怕打针才不愿意去医院,又像小时候似的低声哄他。
又把他当小孩子。余子弈想,他拽紧了周俊胸前的衣襟,摇摇头说不要,喝杯热水就好了。
周俊看他那副抵触的样子,也没勉强,说那好,要是喝了热水还不见好,就去医院。余子弈看着周俊认真的神色,寻思再拒绝也没用,嗯了一声当答应。
他把人故在床上,摸了摸额头温度正常,但还是从柜子里拿出厚被子给人盖上,然后下楼去烧水。
六七月的上海滩进入了梅雨季,空气中湿热的能拧出水来,闷得人喘不过气,余子弈是最怕热的,每年夏天晚上都要光着身子,只穿一条大裤衩霸占着家里唯一一台电风扇吹着,还要周俊从另一边给他打着扇子才能睡着。
这一床大被子给人捂得汗流浃背,看起来更虚弱了。没一会周俊端着一大茶缸的热水上来,吹了吹把杯子递给他,“烫,慢点,小口小口喝。
余子弈撑起来靠着床头,接过水杯小口小口地喝着,跟猫似的。周俊就坐在一旁看着他喝,没一会儿就盯着儿子水光潋滟的嘴唇出神。
余子弈被他盯得浑身发毛,猛喝了一口把杯子递给周俊,“给,喝不下了。”
他回过神接过杯子,又看了一眼余子弈那有了血色的嘴唇,确认人是好了不少,也没再要求他必须喝完。
“我要睡了。”余子弈躺下来,把被子掀开,露出两条白生生穿着短裤的长腿,“我能不能不要盖被子,好热。
周俊眯了一下眼睛,俯身把被子扯上去掖好,说不行,快睡吧。明天还不舒服了我去给你请假。说罢不等抗议就关了灯带上门出去了。
才不管父亲说的,人一走他就掀开了被
子。贼着肚皮。捏着衣角给自己扇风。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他侧耳仔细听了听隔壁的动静,确认人已经睡下了,才摸黑从衣柜里拿出一条干净的裤裤,蹑手蹑脚地去了盟洗室
勾着内裤的一角把内裤脱了下来,白色的布料上赫然一道深红的血迹,余子弈心道果然是生理期到了。今天周俊回来了他开心过了头,完全忘记了这回事,还吃了辣子鸡,怪不得会小腹痛。
还好没去医院,不然秘密被发现了,父亲可能会觉得他恶心就不要他了
余子弈很怕父亲不要他,从被收养那天起就小心翼翼地保守这个秘密,从没让父亲给他洗过一次澡,周俊也只当是孩子独立过了头,并没有多想。
他熟练地洗了内裤,多打了两边肥皂把血渍洗干净,然后打开淋浴头,叉开腿站立,把阴部暴露在水流下,他低着头,一手按着阴茎,一手拨开阴唇,露出了粉嫩的小逼。水流打在敞开的阴唇上,余子弈抖了一下,小逼一张一合的吐出经血,被水稀释之后蜿过大腿,流进了下水道。
他用手掌去搓阴部,想把黏在耻毛上的血洗干
净。皮肤的纹理蹭过敏感的阴蒂,余子弈轻声噪了一下,咬着下唇继续清理。
手掌来回搓了几下之后,阴蒂探出头来,硬挺挺的在穴口上方,敏感得不行,轻轻一碰腿就要打抖。小逼除了经血,还流出了动情的淫液,混着血液一起,黏糊概的。
余子弈懊恼地吐了吐舌头,怎幺洗个经血也能把自己洗发情了呢。
穴肉自发蠕动起来,里面还泛起痒,要什幺东西插进去才能止住,但是余子弈不想把指头伸进小穴里,他嫌血腥味太重。于是他一手撑着墙。另一只手去揉已经硬艇的珍珠。
生理期身子敏感度上升,揉了一会儿余子弈就觉得要到了,他手上加重了力度,用指甲去掐阴蒂,余子弈爽地小声阵吟,顺着大腿根泄了身。
爽过之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声音可能有点
大,生怕被周俊发现,他草草地把下身洗干净,换上干净的内裤溪回了房间。
他完全没注意到,隔壁原本紧闭的房门,打开了一条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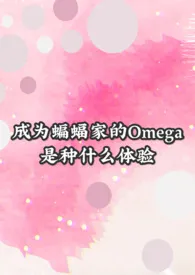
![【耽美】我要这巨屌有何用![系统、高H、NP]](/d/file/po18/77138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