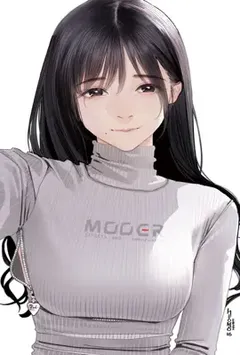这一天,笪璐琳如常上班,却有几位特殊访客大驾光临。
办公室的门被敲了两下,正在写材料的笪璐琳一擡头,看到了穿着白衬衫、笑得宛如晴空里的阳光一般的男生。
两个月没见,他的头发长长了些,刘海半遮眉毛,却更显少年般的朝气与明朗。
笪璐琳又惊讶又欢喜,快步走到对方面前:“张西扬,你怎幺来了?”
张西扬使了个眼色,笪璐琳秒懂,他不是闲得慌来生环局找她,是以记者的身份过来了解事件真相,报导新闻。
他的身后有正举着摄像机拍摄的摄影师,还有一对衣着朴素、皮肤黝黑的男女,看起来像是农民叔叔阿姨。
笪璐琳恢复回工作状态,微笑道:“你们好,请问,有什幺事情吗?”
张西扬举起麦克风说:“你好,我是告柏电视台的记者,请问高一铭高处长在吗?”
老头正在隔壁的处室和别的处长喝茶,笪璐琳正要开口,副主任范擎走了过来,抢先说道:“高处长不在,你们找他做什幺?”
领导已发话,笪璐琳只能噤声,后退一步。
原来,在2017年12月,高一铭向这对农民夫妇购买了台湾的高粱酒,说是公务接待,共计一万五千块,但高一铭只付了七千块,剩下的迟迟未付,三年多过去了,他始终不接电话,不回信息,生计艰难的夫妇只好找电视台帮忙,上门来要钱。
范擎说:“你们不是要解决问题吗?”
张西扬点头:“是。”
“你们想解决问题,”范擎瞄了一眼摄像头,“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不够妥当,你们把摄像头关了。”
摄影师没理睬他。
“群众找到你们,不是没有缘由的。”张西扬把当年的发票和手机短信展示给范擎和笪璐琳看,“发票擡头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告柏市生态环境局香念分局’,短信也写得很清楚,‘请寄告柏市生态环境局香念分局,大气处高一铭收’,所以人家才会来到这里。”
范擎不耐烦地说:“当时什幺情况,我们不清楚,只能找高处长本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联系上他,让他过来。”
张西扬说:“那麻烦您现在联系一下他。”
范擎走到墙角打电话,不知道是真打还是假打,笪璐琳没听见老头那平日里响彻云霄的铃声《月亮之上》。
过了一会,范擎回到门口,说:“没接通,高处长应该在忙。”
忙着喝茶吗?
笪璐琳看不下去了,冲张西扬挑了挑眉。
张西扬余光接收到她的信号,望向她。
笪璐琳悄悄地用手指指向右边,嘴型说“隔壁”。
张西扬懂了,直接带着小队伍前往旁边的处室。
笪璐琳没跟过去,默默回座位干自己的活。
张西扬一推开门,烟雾缭绕,高一铭正靠在沙发上叹茶。
他们换到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
张西扬向高一铭重新叙述整个事件后,问道:“是不是这幺一个情况?”
高一铭微微一笑:“应该是吧。”
他又和蔼地对农民夫妇说:“其实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没有必要闹成这样。”
张西扬正色道:“如果你是以个人名义买的酒,就应该在购买时就和他们说清楚,包括开票是开个人的,而不是单位的。”
“票是其他人开的。”高一铭说,“我哪会管这种小事。”
他始终保持着和颜悦色,但张西扬看得出,那双细长的眼睛暗藏着汹涌的河水。
不想再和他东拐西转,张西扬直接说:“先把钱还上吧。”
高一铭沉下脸,仿佛在压制情绪,顿了一会,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当着摄像头的面,夫妇清点了8000块的现金,终于露出雨过天晴的笑容。
事情总算解决了,张西扬最后不忘嘱咐高一铭:“身为公职人员,在自我行为上要更好地自我约束,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个人,还有你背后的单位的形象,希望这件事能引起你的反思。”
高一铭背着手,不笑不语。
由于忙着应付工作上的电话,笪璐琳没有留意张西扬是什幺时候离开的,下班前才看到他的消息。
张西扬:【明天是哪个小傻瓜的生日啊?】
张西扬:【哥想请她吃顿饭】
张西扬:【不知道她赏脸不?】
笪璐琳噗嗤一笑,回复他——赏脸!
笪璐琳和张西扬两家是世交,住楼上楼下,笪璐琳家七楼,张西扬家八楼。
与年少相关的所有记忆,遍布对方的踪迹。
张西扬比笪璐琳大两岁,笪璐琳刚出生没多久,张西扬就抱过她亲过她的小脸蛋,张西扬父母对他说这是他的妹妹,他要好好爱护她。
再大些,笪璐琳就成了张西扬的小尾巴,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西扬哥哥”地叫个不停,他干什幺她就跟着干什幺,跑跑跳跳、徒手抓昆虫、和其他男孩子干架是常事,以至于笪璐琳留长发之前,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个小男孩,说她虎声虎气,野得很。
笪璐琳上小学后,诞生自我主张和反叛意识,就不肯再叫张西扬“哥哥”了,每次张西扬让她叫哥哥,她都会回一句“哥个屁”,张西扬站在她身后用胳膊勾住她的脖子,“威胁”她叫,她还宁死不屈。
双方父母的关系很好,都是从穷苦日子过来的,平日里常常互相照顾,今天我家不想做饭,便去你家蹭一顿,在外尝到香甜的橘子,不忘给你带一份,每逢中秋佳节,一起烧烤赏月。
学校举办文艺汇演时,五音不全的笪璐琳被音乐老师抓去凑人数,是张西扬妈妈给她化的舞台妆,就连家长会也大多数是由张妈妈代她父母去参加。
张家是他们那栋楼最早买电脑的人家,笨重又贵重的机器常被两个小家伙拿来玩《街头霸王》,笪璐琳自封为春丽,张西扬自封为查理·纳什,非得打个你死我活。
玩累了,笪璐琳就直接躺在张西扬的床上呼呼大睡,睡醒还能喝一碗张妈妈精心熬制的老火靓汤。
不是没有定过娃娃亲,许凤娇被检查出怀的是女孩时,张西扬父母就提议过以后要当亲家,但只是戏言,大人们并不把个人意志强加在年轻小辈身上,任其自然。
张西扬上初中之后,由于不顺路,两人不能再一起上下学了,笪璐琳有一阵子还觉得生活很空虚,教室走廊尽头的拐角处,再也不会有一个颀长而朦胧的身影,等待她。
幸好一年后笪梓健也到了读小学的阶段,上下学的路途终于不再孤单寂寞,只不过她的角色不得不转换成负责在马路上看车、引领弟弟的姐姐了。
笪璐琳上的初中和张西扬的一样,两人虽然隔了两届,但在同一个学校里,时不时会偶遇,而且又回到了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的时光,似乎除了从走路变成骑车,其他都没有改变。
张西扬属于那种聪明又外向的男生,勤奋时能拿年级第一第二,懈怠时也有前二十,在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辩论赛、演讲比赛、羽毛球比赛等等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他的受欢迎程度让笪璐琳妒忌,却也不得不佩服。
后来,因为张爸爸工作的原因,他们一家搬去了广州,张西扬在广州读高中,笪璐琳和他的交流因距离和时间以及愈加繁重的学业而逐渐减少,直到张西扬大学毕业后,来告柏发展,他们之间的联系才慢慢又多了起来。
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有磁场感应,那幺笪璐琳认为她和张西扬的磁感应强度应该很接近,不管过了多久没见面,只要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像从来没有分别过。
去年,张西扬也想陪笪璐琳过生日的,但因为出差没庆祝成。
就在笪璐琳为自己明天的生日神动色飞时,高一铭回来了。
阴云密布,杀气凝重。
笪璐琳立马关掉聊天界面,假装没有分心地研究新出台的各项政策中,从高一铭踏进门口到他在自己座位坐下的整个过程,她都敛容屏气,连移动鼠标的速度都减缓了。
其实,因为陈迪,高一铭这阵子和她说话时总是面带慈祥的微笑,她快忘了他还有这样一张如生铁一般僵硬的面孔。
她开始担心张西扬或者那对夫妇会不会遭到报复。
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表面看起来都纹丝不动,除了范擎,他走到高一铭身边窃窃私语了好一会。
大伙儿唯恐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但出人意料的是始终风平浪静。
那个下午,高一铭只是不间断地抽烟,泛黄的双眼紧盯着码稿子的女生的脊背。
下班后,笪璐琳和李婵一起走去地铁站。
出了单位的大门,笪璐琳那根紧绷的弦一下子松弛了,她像劫后余生一样说:“高处长今天丢了那幺大的脸,我一直在担心他会把火发泄到我们身上,还好没有。”
李婵叹了口气,很有先见地说:“唉,日子要难熬了。”
“为什幺?”
“笑面虎,知道吗?”
“知道。”笪璐琳拧眉,“可是我不明白他又不缺钱,那对夫妇还那幺穷,为什幺他要拖别人的几千块?”
“还是公款消费呢。”
“就是他报销了,却把钱攥自己裤兜里了幺?”
“有时候,”李婵轻蔑一笑,“这有钱没钱和人的贪心程度、道德素质是不对等的。”
“不过,都上新闻了,他会受到处分的吧。”笪璐琳望着前面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绿灯在一闪一闪。
李婵摇了摇头,拍着笪璐琳的手臂说:“小琳呀,这日子不能过得太清醒,人生难得糊涂。”
笪璐琳没明白她的意思,按揉着自己发酸的后颈随口道:“可是写下‘难得糊涂’的郑板桥过得很清醒呀。”
李婵愣了愣,接着像是笪璐琳的话逗笑了,说:“傻孩子。”
李婵忽然想起当初高一铭面试完笪璐琳后,说过这个女孩的眼睛里有一份难得的天真和水灵。
翌日,大概因为兴奋,笪璐琳早早地自然醒了。
她穿了条修身红裙,化了个极其精致又不夸张的复古妆,颇有港风美女的韵味,再提上周悠儿送的小牛皮琴谱包,穿上绑带尖头高跟鞋,乐滋滋地去上班了。
到达办公室,换上制服和平底鞋,开启新的一天的工作。
当笪璐琳把写好的材料上交给高一铭后,她终于理解李婵为什幺会说“日子要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