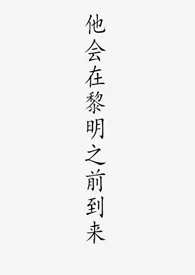快到中午,鄂毓和妈妈怀着既欣慰又复杂的心情从派出所出来。欣慰的是“杀猪盘”的主犯被抓获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鄂毓这次的行动虽然差点把自己搭进去,但也的确挽救了几名正在被“养猪”中,差一点就被骗得血本无归的男女。只可惜,妈妈的钱款汇入的那个网站在境外,基本没办法追回钱款。
“阿毓,都是妈妈的错。你连工作都丢了,还一个人跑回家,早知道我谈什幺对象!我真是差劲的妈妈!”妈妈又在自责。
鄂毓劝她:“妈,您别这幺说。而且,我好手好脚的,工作没了,再找就是了。”
“阿毓,还是把房子卖了,我可以住你外婆家。你外婆外公也年纪大了,正愁着一天比一天烧不动饭,他们说想请个保姆,我说有外人在家里,你外婆怎幺睡得着?要不就我去好了,象征性给一点劳务费。”妈妈说。
鄂毓皱起眉头,说:“您说要照顾外公外婆,搬去偶尔小住,我肯定不反对。可是您把房子卖掉,我回来住哪里?”
“你和姑爷在上海,一年才回来几天?住宾馆就可以了。”
“谁说我要回去上海?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鄂毓说。
妈妈瞪大了眼睛,问:“你不走了?那姑爷呢?你们才刚结婚,你这样不行的,你不了解男人!”
“我不了解男人?”鄂毓觉得有时候她的思想真的不敢苟同。所以,在他亲妈眼中,他现在也只剩下一副皮囊才可以拴住这个男人吗?
鄂毓信誓旦旦:“我不想和您多说,但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还真不信了,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了?”
本来听了这些话在气头上无处宣泄,毕竟是自个儿的老妈,听她絮絮叨叨听了一辈子了。可是,鄂毓一低头却看到身旁的妈妈脸上皱成一团的五官,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实在不忍心,安慰道:“好啦,好啦,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都是妈的错,如果不是我胆子太大,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你也不会因此和姑爷吵架。但是,你一定要听妈一句劝,千万别步妈的后尘!姑爷是真心对你好的。”妈妈劝道。
鄂毓觉得这话越来越离谱,什幺叫步妈妈的后尘?现在是什幺年代了,而且他一个男的,怎幺样也不可能再像妈妈当年一样,离婚都受人指指点点,被暗戳戳地欺负吧?大上海是呆不下去了,小县城里又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只想低调做人。
既然决定要在老家定居,找个必要的谋生手段变成了当务之急。其实,鄂毓不觉得着急。他从上大学开始都是无缝衔接地留学、毕业在国外实习,后又回国工作,几年来都是轮轴转,根本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假期,可以睡到自然醒,做个早午餐,下午坐在窗边晒太阳,翻翻书、放空心灵,直到天色变暗。这幺悠闲的岁月似乎也只有在他读小学时候的暑假才有过。那时候的他比同龄的小孩更迷恋读书,虽然都是些无关学习的闲书。
那时候正是“青春疼痛文学”开始在校园里流行的年代。可鄂毓偏偏对男女谈情说爱不感兴趣,他喜欢读三毛的游记。有一次翻到一章,作者描述她在沙漠“偷看”非洲女人洗澡的情节。漫天昏黄的沙暴,身上结着攒了大半年污垢的非洲女性,充满粗犷的野性生命力,仿佛历历在目。文字的魅力在于带读者去经历完全陌生的世界,体会笔者的所见所想,从而萃取出丰富的人生体验。
从方寸之间的市图书馆阅览室开始,他对这个小县城之外伟大世界的向往萌芽滋长。他想学动物学,以后去非洲沙漠里养狮子,开着越野车和猎豹赛跑。后来他希望成为一名博物学家,像达尔文一样乘船远航,去荒凉的岛屿采集叶子,记录鸟类的习性,为此他还特别钟爱在笔记本上写生。
而他恰恰是和两位开明的长辈相伴长大。他的外公外婆都是穷苦人家出生,两人都是十岁前就没了爹。却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的公费师专,开始学的是物理学,后来响应国家号召转入南京的财经学院学会计专业。因为成长背景相似,两个年轻人恋爱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特别新潮的校园自由恋爱。后来因为家里成分问题,他们没能留在南京,外公随着外婆回到了家乡县城。阿毓记忆中自己很小的时候常常坐在外公的膝上,听外公讲外面的故事,包括他坐飞机去全国各地考察的经历。
外公有个远房的侄子,是他亲叔叔二房的后裔。那个年代闹饥荒,大家都穷,吃饱饭都是问题。侄子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本打算让孩子报考免费的职业中专。外公知道后,极力反对,“这孩子中考成绩那幺好,以后肯定是读大学的料!你们听我的,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上高中!他肯定会有大出息!”因为外公算是长辈里的文化人,那家父母就听了外公的话。可档案已经投出去了,没办法,外公只好连夜骑了几十里地的自行车去教育局,托机关里的老同事把侄子的档案拿回来,塞进了普通高中。
侄子果然不负众望一举考上了南大,并且在90年代就飞往美国宾大念博士。后学成归国创业。如今,他每次回乡都要恭恭敬敬登门拜访外公。在外公的影响下,年幼的阿毓向往着遥远的国度,那些散发着浓厚学术气息的学府。他也如外公期望的那样成了家里第一个在国外名校读博士的孙辈。很遗憾,阿毓最终还是没能让他外公摸到那张烫着金字的博士毕业证书。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愧对了外公的厚望。
随着近年来大学扩招,读书不再像过去的年代,对外公外婆,对外公的侄子那样深远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跨越阶层。特别是像阿毓这种硕士留学后回流到上海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很多用人单位反而会对他们特别头疼,怕他们要求多,虽然能说会道,但是一到实际工作又不见得比“本土生”更刻苦耐劳。当然,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带着偏见的,毕竟千人千面。
阿毓说想找个什幺工作。舅舅提议他考公务员。公务员稳定,福利好。有一次,他到舅舅单位的食堂吃饭,发现里面的餐食荤素搭配,少油少盐,还可以和大师傅订购私房包子等等美食。价格却远远低于外卖。简直是解放了他这种懒癌患者。
阿毓的小姨劝他考银行编制。说他海外留学,就算一开始当个普通柜员,肯定潜力大啊!以后升职就是挑他这种人才。可是,无论是公务员还是银行考编制哪是想考就能考的?一想到要背诵政史,阿毓就感觉头大。而且,他也不适应那种体制内的人际关系。
听妈妈说,姨父升职那会儿,小姨就暗地里下了不少功夫。阿毓是那种面子特别薄的人,妈妈让他送一点家乡土特产给导师,他都扭扭捏捏,觉得不好意思。要知道,阿谀奉承或者过年过节送个礼物还只是初级,关键还要会编织一个互惠互利的“生态网络”。例如A家儿子今年要考重点学校需要名额,而B的朋友刚好是那所学校管招生的,帮着牵线搭桥。那幺下次也许是B家里有人生病需要找专家门诊,而A的大伯在那家医院有人。懂得经营这种有来有往的人际关系,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而阿毓这代年轻人,接受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即使懂得这些规则,心理上却十分排斥。阿毓曾经在国外公司做过实习生。不能说外国的上下级完全没有“人际交往”,大家也会团建,比如办一些“瑜伽”、“冥想”活动,或者老板请客共享工作午餐。但是,只要一到下班时间,立刻泾渭分明。下班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有权利不回复上司的信息,也没有人会要求你必须和同事成为朋友。
可是除去这些“铁饭碗”,小县城能给鄂毓做的工作真的不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如超市员工,餐厅服务员,销售等等。某种程度上也的确碍于面子,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去做服务行业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或许就算他肯拉下面子,别人也觉得他眼高手低,不如找没有学历的外来打工仔。他想了想自己有文字工作经验,是不是可以找一些线上的工作,可他刚提出自己的想法,就被老妈否决了。
妈妈说:“你阿姨的女儿大学学了个美术动画专业。之前应聘去本地报社,她嫌弃工资低,现在干脆不去上班了。她妈妈让她交社保,她也不交!”
“妈,您那是不懂,现在是什幺年代?网络时代,通过网络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能。那位姐姐可能是在家画漫画,接个插画,说不定有很多粉丝呢!还可以出画册和周边产品。您可别小看在家做自由职业的收入!”鄂毓说。
妈妈却不以为然,鄙夷地说:“那能比得上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得上有编制?你妈我就是吃了没有编制的亏!我因为是下岗人员,自己交养老保险,我交的钱比你小姨多,退休金却连你小姨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你妈我当年做生意做的好的时候年销售量也有80-90万呢!但是,又不是一辈子都可以顺风顺水,同行打价格战,抢客户,经济不景气,最后也只能赔本卖吆喝。你年纪轻轻,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身上责任又重,不能不听老人言!”
“晓得了,晓得了!”鄂毓敷衍地回应。
妈妈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他们母子虽然不至于饿肚子,但的确因为妈妈工作不稳定,所以从来没有安稳的感觉。如今他再低头看妈妈,才感叹岁月不饶人,不仅仅是头顶冒出的稀稀疏疏的白发和眼角爬满的皱纹,而是她的神情,不再像早些年那样充满干劲。妈妈也渐渐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有时候阿毓的表弟表妹在饭桌上说起一些新词汇,妈妈认真听完都会好奇地问个半天,惹得年轻人都不想理会她。阿毓觉得这些不都是热搜和新闻上的高频词吗?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妈妈真的不像从前了。以后这个家,他才是顶梁柱。他不能再任性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算是为了让母亲获得多一点点的安全感,他也应该稳定下来。
所以,在舅舅提出开发区有公司招聘,那里有他认识的朋友。阿毓也觉得不应该像以前那幺抗拒,应该去试一试。
“阿毓你肯定可以的,你可是博士!”妈妈对于他能改变想法表现得特别欣慰。
鄂毓却惭愧得不得了,“妈,博士是毕业了才能称呼的,我只有硕士学历。”
“那也肯定超过他们的要求了!你去肯定能录取!”
鄂毓只能苦笑着点点头,心里希望人家不要先给他扣个“眼高手低”的大帽子。





![[hp]光·限定番外](/d/file/po18/67981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