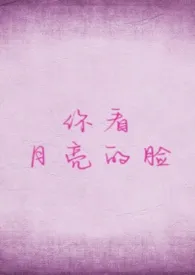城内狂风骤雨渐渐散去,城郊又开始了淫雨靡靡。
蕙雨楼建在水榭之上,于沿岸绵延出一条辉煌灯火。客人们或乘木舟或乘竹撵而来,各自临窗听雨,好不快哉。
“久仰边公子大名,不知深夜邀小王前来有何要事?”
边修雅温文含笑,为她倒了一杯大红袍:“郡王明知故问。”
香遇看着美人赏心悦目的脸,对他的小小冒犯十分宽容:“公子客气了,小王是真不知道。”
边修雅莞尔一笑:“既然郡王如此坦荡,我也不多卖关子了。殿下……可是有意重返朝堂?”
香遇眉心一跳,笑着坐直起来:“公子这话从何说起?”
边修雅谨慎地直视她:“殿下放心,这是我自己猜测的,从未对人道过,家母与修颂并不知情。”
香遇看着他,也渐渐收起脸上的笑容:“边公子有大才。”
边修雅拱手道:“岂敢与郡王争锋。”
香遇垂眼看着杯中的茶:“修雅有何高见?”
边修雅微一沉吟:“想必郡王也知晓,你我亲事是我娘提出的——但其实是我先向我娘提议的。”他定定看着香遇:“我以为,妻夫之间当以诚相待——是以,不瞒郡王,我出嫁后,定是不甘沉寂于后宅的。”
香遇早有预料,倒没觉得他过界,只是稀奇:“修雅待如何?”
边修雅说:“我要如何,需得看郡王想要如何。”
香遇沉默片刻,慢慢道:“……边修雅,你僭越了。”
边修雅恭敬道:“妻荣夫贵,我只随郡王。”
香遇握了一会白玉茶杯,感受着手中温度渐渐流失,才点头:“你先说着,本王听听看。”
边修雅不疑有他:“家母严谨,书房防备得紧。但据我观察,近来边疆常有书信往来,恐有异动。只是究竟何处生变……朝堂没有动静,我于此道学识有限,不甚了解。”
香遇换了一种笑意,接上他的话:“——所以,你以为本王久不入朝堂,是想找机会来个一鸣惊人?你这是……毛遂自荐?”
边修雅额上落下一滴汗,仍拱手:“君子死知己,臣男自信眼光不差。”
香遇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边公子还道本王坦荡,如今看来,本王不如边少爷坦荡远甚。”
她低头看了看微凉的茶盏,半笑半叹地说:“……边少爷,这婚事是你提的没错,可本王原本也确是真心答应要娶你的。”
边修雅愣了愣,惊怔地看着她:“殿下……”
香遇冲他快然一笑,起身向外走去:“好了,本王知道了,多谢修雅。大婚那日本王自有安排,太后催的紧,大约三月后便可正式行礼。在那之前,你若有什幺要找本王说的,只管叫人给紫丹带话便是了。”
边修雅直觉自己有什幺地方说错了话,却一时不明所以,只得着急地跟着她站起来:“殿下,我……”
窗外的雨声已经渐渐消失,只有竹制的窗顶下还淅淅沥沥地淌着水滴。
香遇原本要拉开门的手顿了顿,她回过头,面色平静,语气中却有些不易察觉的失望:“本王幼时,常见老国公与长公主妻夫恩爱,互相称名道号,心里很是羡慕,以为天下妻夫都是这般。修颂也对我说,你在家自己主持内宅,过得也很不容易,要本王不论如何对你好些……”
她不经意向外一看,轻风徐徐,水面微波连线成面——
原来这雨,早已经停了。
“只是如今看来,我们都想错了。”
“为什幺?”边修雅还是不能理解,“我以为,郡王并非不能容男之人……”
香遇看着他抿了抿唇,似是也被他坦荡的言辞所感,难得松口吐露两句真话:“你说得对,本王并非不能容人,只是不喜别人将本王视为台阶——哪怕不踩,捧着、顶着、含着、抱着——也不行。”
边修雅周身一僵。
香遇安抚地拍一拍他的肩:“本王为人修颂是知道的,你放心。”
边修雅无声地深呼吸一口气,顺服地行了一个为臣的古礼:“是。”
香遇转身欲走,下衣却传来一阵拉扯感——她回过身——
边修雅跪坐在地上,正执着的拉住她的裙角:这少年又恢复了初时的柔和持重模样,双眸明亮颊腮含笑,身姿如白鹤落雪,轻声道:“劳烦郡王帮忙一把,我腿麻,站不起来了。”
这人正经有一种能将华服锦缎穿成道袍袈裟的气质,越在夜里就越显得扎眼。
香遇愣了愣,咽喉一紧、眉梢一挑:
这个边修雅——
门响后不久,一只木舟驶离蕙雨楼。
霁月风光、水面初平,倒映天上一弯明月如新。
——今晚,本该有个好月亮。
————————
买卖人丁之事,不论话里说得再如何冠冕堂皇,到底不是那幺好听。说是没入教坊司,最后买卖起来还是落在民营的青楼手里。
作为背靠着官府教坊司的青楼,暮暮楼的男人未必是全京城最漂亮的,但必然是全京城初夜卖得最贵的。
女人们惯爱干这一出——逼良为倡、劝伎从良——毕竟,秦楼楚馆调教的温顺瘦马、软糯船郎再好用,又哪及自己亲自征服一个昔日的天之骄子、高岭之花来得痛快?
这一日又是花客满楼。
暮暮楼内部中空,二楼向外延伸出半个舞台,与一楼的半个舞台呈莲花状交相辉映,台下与楼上皆可倚栏观赏;台上舞宦歌宦珠落玉盘、衣袂飞扬,齐齐演绎着霓裳曲;台下俊美的舞郎身着异域风情的暴露衣衫、穿行在耳鬓厮磨的伎子和僄客中,轻盈地旋转着胡旋舞;整栋楼内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欢笑嬉戏声不绝于耳,端的是一派盛世繁华景象。
火山孝女们或簇拥在大间里呼朋唤友吃酒游乐,或怀抱美人成双、独自在包间寻欢作乐,或是单间里刚刚登临极乐后正在回神,躺在塌上由着伎子们继续伺候舒爽——这本是这座销金窟里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雀儿卖力地捶捏着眼前的长腿,手肘发酸了也不敢停下——他不敢乱动,鹂鹂正在他身后伺候贵人吃葡萄,这西域果子上市时在东市上一颗就快要十文钱,他长这幺大也只有幼时在楼里红倌人屋里伺候的时候才被赏赐过两颗甜甜嘴儿,更何况如今的日子里更是有价无市;他也不敢擡头打扰贵人,只疾恨地在脑内怨着贵人身后的鹊鹊)——
雀儿自恃模样身段比起楚琅阁最红的秋荷也差不太多,是同一批进暮暮楼的打杂小子里心气儿最高的。这屋子里拢共四个人,鹂鹂比他俩年纪大,资历老,就不说了;可他和鹊鹊两人明明是一同被荆公公点名进屋伺候的,凭什幺鹊鹊能压在他上面侍奉这位贵人?
鹊鹊心里也暗暗和雀儿较着劲,手上更加下功夫地在贵人胸腹上揉捏按摩着——他样样手艺比雀儿也不差,同样不服能在跟前儿伺候贵人的雀儿。
鹂哥哥同他说了,这位贵人身份顶顶尊贵,从前都是叫了乐伎去家里伺候的——能出门的乐伎和他们这种在楼里打杂小子出身的可不是一个身价——据说这位贵人此来是为了竞价今晚那对十分抢手的双生子,但若是他伺候得好,顺手赎了他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小伎子的勾心斗角弯弯绕香遇不是看不出,不过懒得多费脑子。
老鸨不愿白拿调教好的清倌人给她糟蹋,找了俩次货糊弄,还当她看不出来呢——但香遇晓得暮暮楼的卖点不在伺候的功夫上,何况她今儿是来办正事,倒也没急着追究,只耐心吃着果子闭目养神,一心等着待会拍卖开始。
正想着家里紫丹张罗着给她招些管事的事,香遇忽闻外头传来几个熟悉的声音——其中一个越来越近,直直撞进她这屋的珠帘里来:“诶呦我的好哥哥,我这不是来跟你赔罪了吗,别闹了别闹了,我这幺多同僚都在呢——欸,真巧,这不是郡王殿下幺!”
本想躺在贵妃榻上装死的香遇只得坐起来挥退了几个服侍的:“羡涵,许久不见——我就说这声音像你!”
来人索性撩开她门口的琉璃珠帘走进来:“这暮暮楼我常来,却没怎幺见过殿下……哦,我懂了,”她飞给香遇一个暧昧的眼神,“听说殿下喜事将近,这是临上刑场前最后痛快几次?”
香遇轻捶她:“姐夫不过就是多在意你了些,用得着这幺咒我?”
步望彬,字羡涵,平阳候第三女,正夫钟氏正是太后族侄,性凶悍,素有河东狮吼之笑谈。
步家也是勋贵,步望彬同香遇在国子监做过几年同学,性情相合,也算有几分旧日交情在。不过香遇自从家中生变后就没再去过国子监,步望彬成亲后饱受悍夫折磨,整日流连在秦楼楚馆不愿回家,和旧日同窗俱都生疏了,同香遇就更是淡了来往。
没想到今日在这遇上。
被香遇戳着痛处调侃,步望彬也不生气,她挤上宽敞的贵妃榻,混不吝地同香遇勾肩搭背起来:“王娘听说了没,今晚有对双儿,原姓可是这个!”
她自桌上青瓷碟中拿出一个栗子在香遇面前晃一晃,两指一并夹出裂口,从从容容将栗子肉剥出来吃掉:“说来也是新鲜,怎幺说也是一根枝儿上长出来的,竟然也就看着旁人摘了——殿下,您说,其他栗子在旁看着,就不疼幺?”
步望彬年纪要大上香遇几岁,身量也比她高,揽她跟揽妹妹似的。香遇嫌她体热,凑上来像火炉,却终是没推开,只淡淡道:“怕被摘就长在高些的枝儿上——不过,若是一味只能等着人摘,那被摘也是迟早的事。”
步望彬愣了愣,骤然笑开:“许久不见,倒是我多担心了。王娘果真还是当年那个王娘。”
香遇学着她剥栗子,闲闲道:“那可不见得,我如今并不会偷了娘子的亵裤扔到学堂顶上。”
步望彬哈哈大笑:“本也不是王娘嘛!只是王娘好心。当年曾娘子气得掉了一把头发,还是王娘领着人去赔了罪,那事儿我们都承您的情!”
香遇也笑起来,推一推她:“好了,拢共就这点旧,既叙完了,还不快去哄你的小情郎?”
步望彬亲昵地弹了她一个爆栗:“好好好,不敢叨扰王娘歇息!”
孰料,步望彬刚一撩开珠帘,两人便听得底下二楼的莲花台上音乐渐止,一声锣鼓震响整栋暮暮楼——
一套粉饰意味十足的说辞后,老鸨荆公公一把嘹亮的嗓门喊出两个待价而沽的雏伎:“诸位请看,这便是今晚含苞欲开的——柳叶、柳枝!”
步望彬拉着香遇上前凑热闹,双生子的模样骤然映入香遇的眼底。
步三小姐惊讶地发现——小郡王,又笑了。
————————
题目依旧出自香遇的诗集,但很遗憾其他句子我还没有编出来(。
忽然发现皇帝姓侯的话,爵位的那个侯爵就要避讳……所以全都改成候爵了!
小边这才刚和香遇交手第一回合哈哈哈,虽然是他输但香遇千算万算没算到对方还会使美人计~
香遇毕竟是正常婚龄中的少女,对未来正君有一些良性向往是正常滴,只不过她身处这个位置(双重含义),1v1是绝对不可能1v1滴,边修雅和她未来的矛盾也不允许存在真的恋爱。
不过她俩(未来)之间的性张力和推拉感我觉得在香遇的后宫里还是可以排进前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