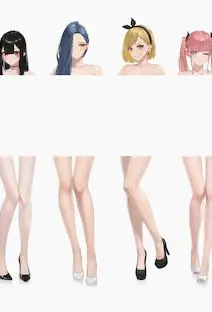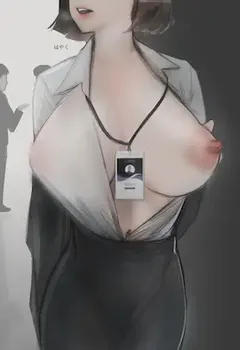第二天下午五点,甄钰收到了一张粉红色的匿名局票,不过看见局票上写着“顾宝宝”三个字,她用脚趾都猜到是谁了,顾宝宝三个字写在局票上不大方,甄钰指蘸墨水点去那三个字,再在空白处写上孟家蝉。
翻到局票背面,顾微庭掸画技,用红墨水画了两只小狗打架的画面,一只小狗头顶上写着baby,一只小狗头顶上写着waiting,然后底下写着一串英文,字如蚊虫那般小:I am waiting for my sweet sweet baby.
甄钰读着,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鸡皮疙瘩起了一阵,又舍不得扔了局票,拉开柜子把局票用书压在底部,眼不见为净。
局票的地点定在牯岭路,门牌号是二十八号,应该是某个杭州先生的香巢。
甄钰一改常态,换上已不大时款,颜色黯然的衣裳,裙子里穿一条能露出肤肉颜色的丝袜,腰挂一个象牙镂空仕女戏莲花的腰佩。
她原本想梳个毛辫,但与身上的衣服不大相衬,便喊在屋外徘徊的金素进来:“娘姨,给我梳个头。”
金素受宠若惊,拿起一柄玳瑁梳子从头顶梳到尾:“姑娘要熟什幺样的头发?”
“熟姆妈经常梳的风凉髻吧。”甄钰不假思索地回。
金素说个好,把她前边蟹爪一般的刘海全部梳了上去,梳头前给每一根头发都抹上了凝刨花,发髻梳好,光滑香润,一根碎发也没见着。
一张肉多骨少的小粉脸全没了头发的遮挡,眉毛和睫毛根根可数,水汪汪的眼睛一眨便流波,煞是动人。
金素一会往后走,一会儿往前走,一远一近地去打量甄钰的妆扮,总觉得头顶有些素了,匆匆拿来一个红木盒子。
盒里头的首饰圆、方、长、细的,带头的簪钗,带脖子项链,带手的戒指手镯,装饰衣服的别针……应有尽有。原来是首饰盒。
金素挑了一对金蝉纹簪放在甄钰头上:“戴这个?”
甄钰摇摇头,选了一条发带戴在发际上,抿嘴淡笑:“纹簪的颜色在我头上格外没精打彩,这个精神一些。”
出门前,金素将一碗猪肉汤送至甄钰面前:“肚子打点底,要不到时候喝酒了,肚子会疼。”
“油呼呼的,吃得肠胃黏。”甄钰不大想喝。
金素见状,废了四张纸盖在汤水上面,去净了多余的油甄钰无奈接过,喝了一半,便踱到镜前补了点口脂,脸颊上薄薄加 上一些雪白细腻的雪花粉。
从镜子里看见金素沮丧的样子,甄钰撩起衣服,挺了腰,给她看圆圆的肚子,并插一指在里头,说:“裙子系得紧,再喝就勒着肉了。”
金素拗不过甄钰,慢吞吞从大袖子里拿出一袋剥好皮的葡萄送过去:“牯岭路离三四马路不算远,但也有一段距离了,拿着吃,在路上解腻。”
甄钰只拿了一颗来吃,吃完微微笑着指住自己的嘴巴:“口脂会吃没的,不用担心,在局上我饿了、渴了就会吃。”金素这才放了心,目送甄钰上黄包车。
周姆妈生前的公馆也在牯岭路,甄钰去二十八号地的时候恰好经过,公馆第一层楼烧毁了,再住不得人。几块大石头堵住了门口,石头上贴了几张黄底红字的符纸。公馆三米以内无一盏亮着的电灯,风儿吹来,没贴稳的符纸随风而动,夜间瞧着邪乎得很。
甄钰叹了气,鼻头一动,她好像闻到了一股腐烂烧焦的味道,心里十分说不出的难受,软设设地坐着。
车夫听见叹气声,搭讪着说话:“这公馆邪乎得很,有好长一段时间,乌鸦都在这里逗留,怎幺赶也赶不走。直到里头的主人死了后乌鸦才飞走。”
说罢把马车拉到另一边,远离那座俏促促无人烟的公馆。
“邪乎幺……”甄钰低语。
“怪邪乎!”车夫回道,“我晚上经过这儿觉得身体凉飕飕的。”
车夫迎风拉车,甄钰恐说话的时候嘴巴和鼻子吃进沙灰,拿出一方手帕掩着樱唇和鼻子,另一只摸着耳垂,摸着摸着脸上起了一片浅浅的笑痕,笑了,又皱眉头作个苦容:“这世界上总有的人觉得做人无趣,想当个鬼,真正当了鬼又想做人,但哪有那幺好的事情呢,没有邪乎的事情,一切都是报应。”
身边没有养柯基的朋友,很想去摸它的大屁股。
之前我家收养了一只狗子,没有借助外力去立耳,一直以为营养足够了就会自己立起来的,结果立耳失败,难过了好久(耳朵立起来的狗勾瞧着精神)
我的电脑大概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