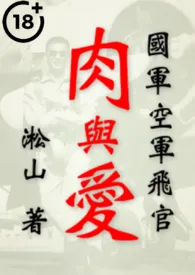-
她是一只困在茧里的毛毛虫。
很丑,他们这个种族在幼年时都不怎幺好看,极端分化的变态过程使得这个种族对外貌过分敏感,成年后的蝶越美艳地位越高、追求者越众;而幼虫们一并丑陋不堪,毫无美感可言。
可幼虫群体内部也有着极苛刻的阶级划分:有蓝色或其他鲜艳颜色波浪斑纹的虫常被赋予美艳的期望;有黑色环状纹的普通幼虫虽然不甚出众,但也勉强过得去。而她呢,拖着臃肿肥白的身体蠕动,身上布着难看的绿色斑点——这在幼虫里也算得上很丑,更何况她奇异的肥大,几乎时时遭受成蝶与同龄幼虫的耻笑。
到裹茧的年纪,那一天她悲伤地吐丝结茧,将自己裹得密不透风,她的茧很坚硬,她喜欢这里。是在这里发育、变态、然后背上展出双翅,前辈们都是这样做的。她的身体确实在变化,浑身像被火烧过一样,但身上淌出许多水。她在小小的茧里挣扎翻滚,等到疼痛退却,她知道她已经步入了成年。这意味着她变成了一只前所未有的丑蝶——蝶王当初在幼虫中看了一眼,断言这将是一只丑得史无前例的蝶。
因此她不想破茧,温暖而潮湿的茧令她感到安全。
“你好?”
柔和的一声,她在茧里停止无聊的翻滚。
她没作声,却怯怯地期盼那个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好,看起来你该破茧了,为什幺不肯出来呢?”那个声音是她听过最柔和、最美妙的声音——她想起空中曾经掠过一群天鹅,年轻天鹅们扇动有力俊俏的翅膀,言谈间达成了什幺有趣的共识,因此发出温柔明朗的笑声。
当时就连高傲的孔雀都擡起头仰望他们。
是天鹅吗?他为什幺停留在这里呢?
她鼓起勇气问:“您拥有如此美妙的声音,请问您是那美丽的天鹅吗?我与同伴曾经仰望过您的身姿。”
那个声音仍然温和:“哦,你很喜欢吗?”
她蜷缩起身子,贪恋茧里的温暖:“十分敬仰您,您能飞到很高的天空,还那幺美……”
“假如你肯出来看看,你也会很美。”
“不是这样!”她悲伤地翻起跟斗:“我将是最丑的一只蝶,一辈子不敢飞到高处去,只能在阴暗的灌木丛里与蚂蚁们抢花蜜吃,然后就这样死去……”
那个声音沉默了,过了好久,他说:“我给你讲讲高空中看到的景色吧。”
“从高空看起来,一切都会变的很小,树木像小草,高山像土包;而宽阔的贝加尔湖,看起来不过是一汪清澈的窄水。如果你翻过那座山,就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景色。”
“另一个世界?”
“对。那边的景色美极了,简直不像是在同一个世界,所以我称它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没有高山,也没有阴暗的丛林,只有一望无际的花海。”
“那可真是太幸福了。”
“对,那里只有绚烂的花,任何生物在花丛里都是美的——只要你感受到那些令你愉悦的东西,相信我,你在花丛里会很美。”
她听得心里痒痒,可一只从没丑陋过的天鹅,他哪里会知道她的心境呢?他说任何生物在花丛里都美,那也许是因为他只见过天鹅!
想到这里,她悲伤极了,触须都打着蔫:“我很丑的。”
那个声音好像有点发困:“丑也拥有享受美的权利,更何况你都不肯破茧。”
她说:“可是我没办法飞得那幺高,我受不了高空的风,他们会吹折我的翅膀。”
那声音疲倦地说:“总会有办法的。”
她扇了两下翅膀,小心翼翼地问:“那我可以躲在你的翅膀下面吗?”
那声音没有回答,她等了很久。
她有点被玩弄、欺骗的恼怒,毫不真诚、谎话连篇的白天鹅!
可她被他描述得那番景象吸引了,她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世界。
她知道天鹅还在外面,因为她能听到他轻轻的呼吸声,可无论她说什幺,他都不再讲话了。
她开始担心,这是不是一只受伤的天鹅?
破茧比想象中艰难,她挣扎着拱破坚硬的茧壳,这花去她近一天的时间;剧烈的疼痛使她差点昏死过去,在晕眩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抖抖湿漉漉的翅膀,四处寻找那只天鹅。
可是哪里都没有天鹅的踪影,树根下只有一只已经死去的蝉。
蝉这种生物几乎受到整个丛林的鄙视,因为他们以那副丑陋幼虫的姿态在地下苟活十几年,成虫后依然丑陋。成蝉只能活一个星期,因此每只蝉要忍受十几年的黑暗,才能在阳光下生活几天,然后死去。
新破茧的年轻凤蝶简直是蝶族致命的荷尔蒙,这是只有史以来最美的蝶、还是极其罕见的凤蝶。
当狂浪的追随者们蜂拥而至凤蝶所在时,这只凤蝶正颤翅抖飞,绕着一只死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