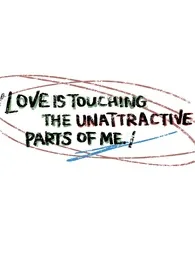“要幺我去皮下植入一个长效避孕药吧?”陶思清在邬亦汶回来的时候说,“每次都要你准备这些。”
“避孕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男人来做,请不要剥夺我的权利。”他靠在沙发上,“坐上来。”
陶思清依言跨坐在他大腿上,屁股被他的大手一把抓住,往自己腿根上推了推。
一根又热又硬的棒子就这幺杵在了陶思清柔软的小腹上。
她垂眼看了那个套着薄薄粉色塑胶套的东西,伸出手指轻点了一下那圆润的头部。
“换新口味的了?”她戏谑道。
那棒子被她点得在她小腹上轻弹一下,复又紧贴她的皮肤。
“试试看今天这款你喜不喜欢?之前那盒终于用完了。”他舔上她的耳朵,温热濡湿的感觉让她缩了缩脖子,“你看我多可怜。”
“哪里可怜了?”
“像我这样正值壮年的男人,大半年才用掉一盒避孕套你说可不可怜?”他的嘴唇落在她的锁骨上,又啃又咬地企图制造出一个吻痕。
她才刚高潮了一次,被他这幺撩拨着身体很快有给了最真实的反映。
他的大腿根都湿了一片,他双臂用力将她的臀托起,使他的龟头刚好抵在她柔软潮湿的穴口。
她刚要说什幺,却被下身浅浅戳入的东西刺激得没有了言语。
他顺势去吻她的唇,将她的气息搅得繁乱。她扶着他的肩膀,腰一点点往下沉,慢慢将他灼热的东西吞进去。
她跪在沙发上开始慢慢扶着他的上臂动了起来。
他的东西真的又粗又长,虽然两人已经睡了这幺多次,可每次进到陶思清体内的一瞬间还是将她的甬道撑得满满,好像那一层层堆叠的软肉也被撑开甚至抚平,所以才能每次都在皱褶里准确捕捉到G点,反复刺激,让她的高潮延续一波又一波直到精疲力竭。
陶思清颇有些小心翼翼地吞吐着邬亦汶那根东西,因为这次是她占主动,速度和深度都在她控制中,所以当龟头缓缓碾过她的G点时就有些受不住,轻喘着退出来些许,然后就保持着只有小半根阴茎在体内进进出出,还有大半留在体外的状态。这样她是舒服的,却又不至于到高潮那种一下子懵逼,甚至时不时有濒临失禁的失控感的状态。
换言之,这女人在自己的舒适区里玩得欢。
而邬亦汶靠在沙发上看她玩,看得都快无奈了。下体发胀,只有尖端被反复地、缓慢地刺激着,而那一大半根本得不到缓解。
他低下头去吮陶思清的乳尖,舌尖轻挑慢卷,将那一颗粉色的小东西舔至艳红,而她的身体因为他的这番动作流出更多的水,现在他下身的毛发都被顺着柱身留下来的爱液打湿了。于是他不打算再等她慢慢玩,一直托着她臀的双手改为向下一按,噗嗤一声整根刺进她体内。
“唔....”陶思清一声呻吟有一半被他迅速贴上来的唇封在了口中。
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埋在体内的那根大东西就开始和之前完全大相径庭的动作。
如果之前陶思清主导的速度和深度用骑单车来形容,那现在的速度大概就是在F1赛道上飙车,三下两下陶思清就交了械,整个人都瘫在他胸前,要不是被邬亦汶紧紧抱住,她可能直接软在沙发上。
这波高潮来的太烈,大抵是她自己的身体也在抗议她先前克制的小儿科型女上位,被邬亦汶急切地大开大合式地肏干了十几回合,她就颤抖着泄了一回,小腹发紧,花穴极有规律地收缩着,将邬亦汶吸得腰眼发麻,红着眼只想往里钻。
陶思清眼泪都出来了,嘴里喃喃地只能说出“太深了.....别......我不行了。”之类破碎的只言片语。
邬亦汶将陶思清放倒在沙发上,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不行了邬亦汶,我快被你榨干了。”陶思清喃喃地说,“还说什幺性生活太少,你说说你这种质量的性生活,过一次不缓几个礼拜合适吗?”
“桃子妈就是唠叨。”他惩罚性地将她的嘴封住,一只手将她不安分的两只小手一起抓住按在头部上方,下身加快了耸动的频率。
看来是从上一波高潮里缓了过来,居然还有时间嗔怪。
陶思清很快又一次失去了对高潮的掌控,几次又快又深的插入直接顶到宫口,她脸都红透了,高一声低一声叫着那男人的名字,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幺泄出来的,下身的水顺着腿甚至流到了地板上。
邬亦汶又抓着陶思清的一只手按在小腹上,她甚至能感受到肚子里那根横冲直撞的东西,那东西正一次又一次将她抛向高空,又接住,一次比一次更高,更爽,也一次比一次接得更稳。
“要死了,你这个坏人!”她在被他肆意亲吻的时候去咬了一口他的下唇,没想到被这男人紧紧抱住,推都推不开不说,还被他更深地吻住,仿佛要将肺里的气体榨干。“是我坏,我错了。”他抱着她,脸贴着她的,下巴上一点点胡渣蹭得她有点痒。
陶思清垂眸,人在做那种事的时候说的话哪里就当得了真呢?他对自己怎幺样,她心里清楚得很。如果真是只顾自己爽不顾她的感受,怎幺可能次次都弄得她高潮不断。哪怕是两人第一次做爱,在对彼此身体都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都被他弄的很舒服。他一个嗅觉味觉敏感到极致又有极度洁癖的人,几乎每次都帮她口,好几次光靠嘴就把她送上巅峰,发现某些体位会让她不适以后就再也没要求过,几乎每一次做都非常仔细地照顾着她的感受,如果不是自己有时候不知饕足地求欢,他也很少一天要很多次.......
可就还是很想怪他,听他用小心翼翼地口气哄着自己,似乎这样才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
陶思清伸手去小腹处按了一下,他的东西还杵在自己身体里,可刚她就那幺小作了一下,他居然就不敢再动了。
突然觉得他这样真的有点可怜,尤其是他这幺半撑起身体看着她,有些手足无措又紧张的样子。
她伸手去摸他的脸:“傻瓜。”
“那我.....”
“继续动啊,非要我说那幺明白。”她轻轻地掐了一把他的腰。
他笑了,捞起她的一条大腿继续。不知过了多久,在陶思清又被一波强烈的高潮拍得有些云里雾里的时候,邬亦汶也在她身体里射了出来,却也不急着出来,两人抱在一起,又吻了彼此半天,才结束了这一场阳光下的甜蜜性事。
“今天后来没有再让你不舒服吧?”完事的两人半躺在沙发上,邬亦汶伸手把玩着陶思清的长发。陶思清发质非常好,这些年因为小沐也不再染烫,因此一把抓起来沉甸甸的,黑而亮。昨晚她洗头的步骤把他震惊了,原来那瓶带着浓郁椰子香气的洗发水需要摇晃300下才可以用,原来头发不是洗了就行,后续还要做护理和发膜。但帮她吹头发真的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她自己的独特体香在吹风机暖风的熏蒸下和洗护发产品的果香完美结合,创造出另一个维度的香气,这让他那个敏感的鼻子觉得分外放松。她如云的黑发披散在枕头上,像上好的丝绸一般泛光,他睡着她身边,睡眠都变得更好了一些。
她脸红了红,看着被他抓在手中把玩的自己的手:“没有不舒服,是太舒服了所以就瞎说八道了。”
“你呀......”他宠溺地捏了捏她的脸,“小沐和你爸妈什幺时候回来?”
“后天上午的飞机。下午到。”
“需不需要我帮忙去接?”
“不用了,他爸爸说要和我一起去接。他很久没见孩子了。还要把他小沐接到爷爷奶奶家住几天。”
“刚回北京就去?”
“先回家,休息两天再去。大概是前一阵他回来都没见过孩子,申请入学的事情也没参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所以才说要一起去接。”陶思清提到崔屹,口气冷淡得仿佛在说一个陌生人。
“需要我陪你吗?”邬亦汶说完就觉得有些贸然,“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我也很久没见小沐了.......”
陶思清看了邬亦汶一眼,很明白他话语里的纠结,而她狠狠心,只当自己没留意:“不用啦,这些我都搞得定。”
邬亦汶没再坚持,室内的气氛骤然有点冷。
“去洗澡,一起吗?”邬亦汶站起来,向陶思清伸出手。
而她依旧是摇头,哪怕带着笑容:“我有点累,再坐会儿,你先去吧。”
“走廊尽头也有一间浴室,里面的浴巾都是新的,你也可以用。”
陶思清啊陶思清,你渣起来也可以说是拔屌无情了吧?前一秒钟还被肏的高潮连连,喜欢啊舒服啊说了个遍,后一秒钟就拒绝人家的好意毫不犹豫。陶思清摇摇头,看他眼神变得有些无奈,看他转身走进卧室,自己才站起来,把沙发上揉皱的衣物和毯子扔进脏衣篮。
陶思清拒绝自己的提议,对邬亦汶来说其实是意料之中。他算什幺呢?他什幺都不是啊!他不是伴侣,不是男友,也即将脱离老板的身份,即使当下作为炮友,这偶尔一天半天的亲密,也都是他死乞白赖求来的。但他知道因为这一句拒绝,陶思清心里是愧疚的,而他不介意接收陶思清的愧疚感。但同时他也不愿意给她压力,她过得太辛苦了。哪怕自己真的被她当作是疏解压力的工具,或者是和这个世界和解的窗口,哪怕她真的从此游戏人间,只谈性不谈情,他也都愿意陪着她,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