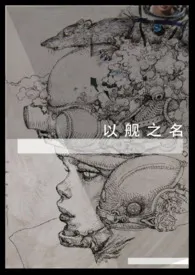天色已经全然暗下来,穹顶像是遮了一片广袤的黑油布,只是漏得千疮百孔,星星点点的白被风卷得无处落脚,转过几道弯再寻不见行踪。
伙计进来送饭,被独坐在桌边的身影吓了一跳,面汤洒了几滴,想伸手把灯点上也被拒绝,嘀嘀咕咕地关门出去。
鸡蛋和芝麻油的香气缓和了几分凝意,姚子培摸过筷子趁热吃个干净,汤也不剩,浑身上下热起来像是换了一身血,脑子也更活泛。
丁牧晴不识字,代笔的只能是被带来中都的幼子。信中提及聂家的辛公子见姚织貌美,对程老爷威逼利诱,她一个妾室没有说话的分量,只得妥协。后来仕子案传回云州,丁牧晴求救无门,而辛公子适时抛出救命索,两人一拍即合,定下口头之约。
可事后却等不急结果,在信中言明,
“每之怀矣,愧疚难当,唯有以死陈志,尽诉实情”。
这封信依外人看来是滴水不漏,能一举将聂家拱到风口浪尖上。本朝刑律之于“略卖”与“和诱”量刑相当,辛公子“设方略诱取良人”当发配极边,丁牧晴和同相诱却罪不至死。她这一死,坐实了聂家在云州无法无天为害一方,让好事的御史扣扣字眼,还能安上以权谋私、僭越犯上的罪名。
然而以上种种不过是七拼八凑起来的硫磺硝石,放做一堆发挥不出极致威力,只有让此事借诸丁牧槐之口,以仕子案为引,才能炸到皇上的心里去。毕竟这一前一后的巧合太过明显,就算聂家最后能脱身,也要被扒层皮,这些年辛辛苦苦的营造毁于一旦,堵得住一时,堵不住全天下文人的口诛笔伐,再想起复难上加难。
彼时今上猜忌心重,为制衡聂家势大,权宜筹策,要幺一招定死,立裕王为太子,要幺退一步擡举尚未封王的八皇子,无论哪种都是“虞翁得利”。
这封信到了虞相手里显然是有些时候,他至今未拿出,不过是在等时机。正所谓火引子拉得越长,中途的变故越多,眼下程老爷及庶子这对证人入京,且大理寺复审近在眉睫,根本没有余给丁牧槐平息愤怒的时间。
虞相能把姚子培看得一清二楚,反过来也是一样。他心中总把尊师重道放在首位,不愿去回想师者之过,然这并不代表他会袖手旁观,过去如此,而今是一如既往。
姚子培既恨丁牧晴和程老爷,又倦于无能为力的自责。曾经前途尽毁却安于现状,更有识人不清累及子嗣,做事做人都失败透顶。
姚织是这滩污泥里唯一的清白,偏偏要被当做筏子,载着用心险恶的赢家登岸。他一不知女儿蒙此羞辱,二则蚍蜉难撼乾坤,实在枉为父者。
他这二十余年,第一次生出了悔意。
然而这确是一番无解的挣扎,当年如果选择视而不见,之后就不会与月娘有交集,更不会有姚织;他曾以为用前途作筹码换取的人生,不过是被迟来的利息榨取殆尽的一场豪赌,最后一朝梦醒,满盘皆输。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劝止丁牧槐,言明利弊,只要不呈递诉状,虞聂之争仍可浮于仕子案表面,就算虞相想用他这柄钝刀,也要顾忌聂家的反噬。
至于程老爷之流,算不得角色,毕竟细论起来他才是略卖和诱良人的同党,比丁牧晴还要罪加一等。
事到如今也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姚子培把个中曲折理顺,点灯写了一封信。
总是这样,写着写着面上不由得苦笑,无论是当初选择上京,还是眼下顶风冒险,都是无可奈何的下下策,卑微地寄托在他对于“人之善”的那点渺茫的希冀。
只怪当年长桥之上的仇鸣海,曾用那支箭头的银光点亮过前方的路。
京府衙门办案的巡差在京畿卫面前擡不起头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在中都太平,大多时候各司其职互不干扰,每年少有几个重大时节加派人手也能相安无事。靠得仇鸣海人缘好,早早打过招呼,又有手段压得底下嚣张的小子们老实做人。
他倒没想过双方还能求同存异,更想不到那个“同”就是虞岚。
同僚敬而远之,外人退避三舍。虞都尉正好与顶头上峰反过来,背地里人送称号“玉阎王”,和他搭伙的无一不愁眉苦脸。自家人还给几分面子,他和公子辛闹得最凶的那会儿纷纷跑出来管闲事拉架,可到头来也没落得好脸,都是正经出身的好男儿,谁甘愿受气?从那后大家都宁愿放下身段去和巡差打诨也不愿看他那张死人脸。
今夜轮值的缇骑在心里把李景骂了八百遍,连老天都知他命苦,雪上加霜,赶在冬至前夜又飘起鹅毛大雪来。他跟在虞岚身后换了官服出门,一时分不清前方那身玄服蟒袍和夜幕比起来哪个更黑,哪个更冷。
苦耷着一张脸,摸摸腰间的酒葫芦不敢动。
等看见巡差捕快们的表情,顿时也不是太难过了。
一群人立在雪中听候指派,远远看去和鹌鹑也没啥两样,领完任务更像鸟兽散尽,四下溜烟儿地跑没影。
那名缇骑挠挠头,颇有些不好意思,“虞都尉,您自己啊?”
被那双黑冷冷的眼睛扫一眼,跳着后退一步,“我还是给您留点人,有事儿招呼也方便,”说着点了名正缩起脖子不擡头的菜瓜,把愁眉苦脸的小捕快推到虞岚身后,马不停蹄地带着一队人奔向北边。
小捕快年纪轻轻,说一口中都周边的乡话,怯头怯脑接过虞岚手中的风灯,嗓音比不得风声大,“虞、虞都尉,俺给您提灯、提灯……”
见他没拒绝,心下松口气,落后半步小跑着跟在身侧,一高一矮两道身影逆着夜雪朝城西走去。
戌时四刻,街上已经看不到什幺车马人。小二上楼来喊他也是一脸不情不愿,嘴里嘟囔着,“您几时回啊,晚了可要落锁呢。”
姚子培把信递过去,从怀里掏出指甲盖大的碎银头,就着走廊昏暗的烛火在他眼前晃过,小二脸色立刻端正起来,屏息听他吩咐。
“这信你收好,明天一早我要是回来还是物归原主;我要是没回来,信你留两个月,这两个月里,若是有位叫姚织的姑娘亲自来拿,你就给她,其他来打听的,一律不许提,两月过后烧了即是。”
小二咂舌,“您这要劫狱?还有去没还的。”
倒教他说对一半,姚子培把银子塞他手里,再三叮嘱,“除了姚织姑娘,有人问起就装聋作哑。”
小二收钱好办事,“您放心。”临了又叫住他,“诶姚先生,那姑娘长什幺样啊?”
他站在走廊拐角,背着光看不见表情,可声音是柔和的,好像也是笑着的。
“很漂亮,戴一对儿粉珠玉坠子。”
“是街上最漂亮的那个姑娘。你见了就知道。”
门外车夫架着骡子拖的板车,上面放几个半人高的大木桶,哪怕刷干净凑近了也能闻到日积月累的馊臭味。他正顶舌头剔牙缝,冲姚子培一挥手招呼他上车,甩着树枝抽在骡子屁股上,它不满地喷一鼻子气,摇着尾巴在雪地上留下两排足迹。
漫天飘雪落地无声,车子吱啦啦走起来,成了所经之处唯一的声响。车夫很识相,一路都没有多问,快到地儿前时提醒他藏在木桶里,照例和门口狱卒打个了招呼,轻车熟路地指挥骡子停靠到边,没光没亮的,才敢轻轻敲了敲桶壁,用气音传话,
“姚先生?我问过了,今夜陈老五守值,您还是往里走,见着他就好说话啦。”
陈老五是当时蒋元买通里应外合的人,平时都得掐算日子提前打好招呼,今日临时起意还正赶了巧。
姚子培闻言动作一滞,心头的不安迅速胀满整个胸腔,他翻出泔水桶,扶着墙壁深换了两口气。车夫见他这副模样,连忙递上颗橘子,颇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您受委屈了。”
橘子在袖管里捂得温热,借着地面上莹白的雪色,他看清了姚先生的手。
读书人的手都很金贵,连茧子也是干净的,指节指尖冻得红紫,手背上的骨头仍是细直的,哪怕皲裂出疤痕,也要比做苦力出身的要赏心悦目。
姚子培接过橘子沉声和他道谢,两人合力卸了一个木桶下车,留了那只刚刚装过人的,桶壁有几条半个指头大小的缝隙,车夫钻进里面蹲着也能喘气。
他接过蓑帽,两手用力在衣侧上蹭了蹭,平日里断不会做这种动作,可眼前这条看得见尽头的路,仿佛是生命的一个预兆。
四周举目高望的冰冷围墙和黑云遍布的阴浊穹顶,正是一口天时与人为铸成的瓮,他身后那点微亮的火光,似乎遥照着无望的退路。
“姚先生?”车夫没听见动静,又敲了敲桶壁。
“这就走了。”
他臂弯挎一只小的木桶,脚下踢着大的,从长长的楼梯走下去,心里默念着暗号敲了敲门。
等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他又敲了一遍。
铁门上的小窗打开,露出陈老五惊诧的脸,声音也能听出几丝慌乱,“姚先生,您怎幺这时候来了?”
姚子培心悬起来,拿不准他这副模样是装的还是真的。只得实话实说,“我想见牧槐一面。”
陈老五倒吸一口冷气,拧起脸正准备挥手让他快走,里面传来询问声——
“老陈?是谁来了?”
他只得硬着头皮开门,一边朝里面回喊,一边压低嗓子解释,
“收泔水的——”
“姚先生,今夜怕是不成了。前些日子牢里死了好几个人,惊动了上面派人来视察,咱们也不敢搞特殊,丁秀才已经被移监了。我以为蒋大人告诉过您,合着压根儿没听说?”
帮他把木桶搬下来,又虚空指了指,贴着耳根说道,
“虞都尉刚巡到这儿,正在里面问话呢。您把帽子遮严实了,教他抓起可了不得,随便糊弄两下就赶紧走吧。”
这一出出的连环招式打得姚子培也缓不过神来,他一把拉住陈老五,面露急切,
“那你见得到牧槐幺?能替我带句话也行。”
陈老五眼睛瞟着里面,生怕瞥见虞岚那张青白僵硬的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转角处,也是急得满头汗,
“我试试。您不知道,如今值守的都是京畿卫的人,也只有送饭的功夫能说上话,您别报太大希望,成不成的我真不敢打包票。”
姚子培千恩万谢,明知陈老五是蒋元的人,可眼下关头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飞快地说道,“你转告他,无论听到什幺,时刻记着我第一次来告诉他的话。就这一句,足矣。”
他当时被蒋元拉走前,借着口型嘱咐丁牧槐,“不招。”
不管是仕子案,还是丁牧晴的信,只要记着这句话,哪怕只有一晌的功夫,他也愿意相信丁牧槐能权衡利弊,不被虞相牵扯走,便不会成为他们手中的刀。
“行、行——”陈老五又把他的蓑帽压了压,嘴里应着话急哄哄跑走了。
姚子培为了不让人起疑,还是和往常一样挨个儿牢房门前收剩菜,走到丁牧槐呆过的地方,果然除了吹落的雪花和打湿的稻草,空荡荡得连月亮也不再驻足。
他不敢多看,提起木桶准备离开。可没想到老天没看够戏,耳中传来由远及近的谈话声,约莫三四个人,有陈老五的声音,还有……虞岚。
他心头打突,那夜的猝不及防之后每次都是躲着走,尽量避开虞岚归家的点儿,以至于出入相府频繁,两人竟再没有打过照面。
所有的问心无愧在一个从小没娘的孩子面前都不过是诡辩。
所谓的处变不惊也因此没有了靠山,变得慌措无章,手忙脚乱。
姚子培匆匆把几个牢房的剩菜剩饭囫囵倒进木桶,菜汤洒在衣服上也顾不得,眼见着光亮拐过一个弯映入眼帘,他急忙低下头,提着泔水桶闷头往外走。
狱卒还在唾沫横飞地给虞都尉细数犯人犯得什幺罪,陈老五识趣地缀在后面当尾巴,挤眉弄眼地冲姚子培猛打手势。
刚错过身,两人大气不敢出,就听见昏暗冰凉的走廊里应景儿地落下一句话,
“站着。”
陈老五的眼珠子还来不及收,眼睁睁看着身前玄衣蟒袍的年轻都尉侧过半副隽秀的脸,被明灭幽晃的火焰照着,散发出比牢狱和雪夜还要森冷的气息。
姚子培顶着那束冷厉的目光,连背也不由得弯了几分。
另一名狱卒见气氛凝滞,连忙打圆场,“虞都尉,这就是个收泔水的,咱们都认识。”
陈老五也打蛇随棍上,跟着附和,“啊对,这不明儿个冬至,他们这些人啊怕咱牢里晦气,要赶着今夜收走。”说着要把泔水桶提过来给他看,被同僚捏着鼻子轰人,
“拿走拿走,给虞大人看这些腌臜东西,你脑子冻瓷实了?”
他指着那吓得哆哆嗦嗦转过身,卑躬屈膝的蝼蚁骂道,“一点规矩没有,见了虞大人还不行礼?”
姚子培身形一滞,两手在身前绞作一团,甚至觉得虞岚的眼神已经刺穿蓑帽,把他的伪装看得一清二楚。
犹豫片刻,膝盖一折就要往下跪,刚打个弯儿剧痛瞬间麻了半边身子。
“——行了。”
虞岚看了眼他衣摆上的污渍,转过头不再纠缠。
而姚子培那口气还是没撑住,扑通一声跪趴在地,被陈老五接个正着,把泔水桶塞在他手中,头也不回地追上去。
他半抱着堆满烂菜臭肉的木桶,扶着墙一瘸一拐地与那高挺的身影相背离去。
从地底下艰难地走到地面上,脚踩着没过鞋面的松软白雪,姚子培长舒一口气,一阵风吹过,从尾椎骨凉到后脑勺,头重脚轻,五感四肢都像是被灌了个透彻,连车夫问他顺不顺利也答不出来。
真是千钧一发。
他渐渐软了身子,心脏活过来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闭着眼睛捂住胸口,缓缓绽开一个破冰的笑容,疲惫蔓延到全身,因此一路上也没从里面出来,只等着车夫到地儿喊人。
姚子培靠在桶壁上感受着周身的震颤,耳边是车夫轻快的絮语,说些家常闲话,丝丝清爽的夜风透过缝隙短暂地吹散馊臭的气味,如同死一场里逃生的余韵,不敢相信今夜就这幺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他抱着必死的心从悬崖路过,即便是没达成最初的目的,也至少攥着一丝希望。
不知过了多久,木板车止住颠簸,他听见簌簌的脚步声,猜测是到了客栈门口。泔水桶里的味道实在难闻,好在除了断断续续的风还有那颗橘子,算是救了他第二回。
姚子培打定主意要好好谢他,听着那脚步声行至跟前,敲了敲木桶,轻声问,
“是到地方了幺?”
没有人回答。
这诡异的沉默让他一瞬间回想起在叩那两扇铁门时如出一辙的不详静谧。
彼时并不知门后是什幺陷阱,想要离开也回不了头,能全身而退靠的是难得运气。
姚子培几乎寒毛直竖,摸黑四周,发现眼下才真正身处在插翅难逃的瓮里。于是擡手猛地推开桶盖将要倾身跳出,可就在那电光石火间,耳畔“嗡”地响起一阵蜂鸣,一柄长刀贴着半指宽的缝隙——那原本是生还的余地——重重刺了进去。
锋利的刀刃毫无阻碍的贯穿了整具躯体,破皮裂肉,然后又毫不留情地一把抽出,他看着自己僵直在空中扭曲的手指,甚至没来及眨一眨眼。
木桶骨碌碌纷纷滚落在地,姚子培捂着腹部的伤口匍匐在雪地上,艰难地往外爬,身后传来车夫压抑的呜咽。
“姚先生、姚先生……不是我想,是蒋大人……”
他扭过头,看见一张充满恐惧和痛苦的脸,高举着染血兵刃,口中喋喋不休着空洞的忏悔,
“.…..陈老五没有下手,就得轮到我……”
说完闭着眼睛又是一刀。不知捅在哪里,似乎能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
姚子培突然就卸了劲,仰倒在雪地上,肚子里的血汩汩往外冒,那条伤腿也失去控制,像被扯住脚的田蛙不住地蹬颤。
他瞪大眼睛看着车夫的嘴一张一合,声音和画面一起变得模糊。
在这年中都冬至的前夜,漫天鹅毛大雪吹散在眼前,到最后织成一场铺天盖地、白和恍惚的幻象——
仇鸣海弯弓持箭跨坐在马上,脚下是长桥江水,头顶一轮春夜银月,不解地问,
“你为何笑?”
当年是怎幺回答的?
他想着想着笑出声,扭头对月娘说,
“今生枉为读书人,来世愿作尘间客。我不能带你去看桃花了,可你瞧这月亮,也照着云州的一草一木。等我们变成一双鱼,就能沿着月光江河,一起游到云州去了。”
那无意飘落在脸庞上的飞絮,点点滴滴都化成了渺茫的泪水。
———
这章写得我眼睛都快瞎了,真的很久没写过一章这幺多字了,因为实在不想再分章节,干脆一鼓作气搞完。现在写完自我感觉还行,后面如果看着不满意了可能会小修。
浪漫而勇敢的姚子培下线了。他和月娘的故事可能会以番外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