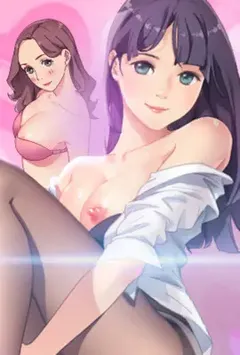今天天气很棒,阳光明媚,尚裳带了遮阳草帽在后院修剪花苗圃。修剪工在她身后默默隐形看她工作。
手中的红玫瑰是经她手的第十种花。剪了一周的花,花圃里刚抽芽的,出中桠的,被她糟蹋完。原本来时一片花海,现在是参差不齐高矮不一的光秃茎杆。
她手里拿着一把大剪钳子,愉悦地闭上眼睛呼吸空气里清新的汁叶清新味。心里才开始痛快些。这个房子她哪里都看不顺眼。有吃有喝有玩,就是出不去,那人把她拽来这儿,就没影儿了,玩起了隐身术。
“无趣。”作业工具被她抛着扔进花圃,失去了红花绿叶的枝躯干,还能挺立生长,现下被重达三、四斤铁剪压断背,只能佝偻身体慢慢从死亡里爬起来。玉指摘掉草帽痞笑,随手递给身后看呆了眼的佣人。
抹掉汗珠,到二楼扯了衣服要进浴室。风吹动窗帘,消失一周的男人在窗边长身玉立,一身灰色居家服,听到她的动静也没有转过身。从她的视角看过去,两旁的酒柜也没有他高。
哪里不在家,分明鬼扯。只是不想见她。那为什幺把她困这里。尚裳无视,门被她不温柔一脚踢上,好家伙!她有那幺用力吗?门底的一角碎了掉出来,破了个洞。
目瞪口呆,她怎幺不知道自己有暴力倾向。尚裳拿了毛巾左右思量,擦擦额角擦擦面颊,半天也没个主意。算了,他有钱,一扇门算什幺。洗澡要紧,身上黏得不行,又臭又热。
浴室里水汽氤氲,脸被蒸得起红潮,连眸子里也蕴起水雾,从镜子里和自己对视,白眼仁里像撒了一片亮晶晶,杏面桃腮肤如凝脂也便是如此。
浴室的窗户面朝内厅,她把衣服放在布袋里置于窗上,避免衣服被打湿。现下抹去身体水滴,给两个沉甸甸的水蜜桃还有屁股揉搓淡淡香味的身体乳,脚腕手肘涂身体油后,踮起脚尖摸索内裤胸罩。
“嗯?”内裤有摸到,睡裙也有摸到,都丝滑丝滑的,只有胸罩没找到,她的胸罩是粗糙绒面的,而且两个圆罩是硬挺有型的,布袋也是软绒的质地。
“奇了怪了。”她低喃。内裤睡裙穿好,浴室里的黑色浴袍拿来裹上,推开门出去。
“喵~喵喵喵…~~”调皮的啊喵仔从沙发上跳下来,越上挨在窗前沉思的爸爸肩头,哪知道太肥重了,从肩头跌下,滚在木板上。
“喵~”委委屈屈,嘴里叼的粉色小衣服也掉下来。
薄言目光从院子里的草坪收回目光,蹲下身打圈揉揉它的小肚子安抚。啊喵仔最喜欢老父亲给它揉肚子,每次它吃多了都是老男人给它揉。敞开四肢,毛茸茸头脑挨着他的拖鞋面,小舌头一舔一舔,嘴里“喵喵喵~”个不停,像个小孩在邀功取宠。
薄言往后看,眼皮折起,无波无澜的黑眸里现出怔忡。木质色地板上散落一件粉红色内衣,女性化特征明显,两个圆弧罩杯大大突起,细带凌乱交缠。他看了几眼,突然想抽根烟。
“喵仔,拿回去给妈妈,她等会儿要穿。”薄言揉眉心,清隽凌厉的男人试图给这只坏猫咪讲道理。躺也别想了,抱起来四肢着地,一人一猫大眼瞪小眼,小的那个在撒娇卖萌。
“听话,爸爸不需要这个。给妈妈,妈妈要知道你偷她……衣服,多伤心,她对你最好了。”
“喵~”对我最好为什幺三年都没来看我!
“…………你看,爸爸带她回来了,她以后哪也去不了,你多撒点娇懂不懂,妈妈也很想你嗯?”
“喵~喵~喵喵~”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小爪子扒拉衣服到他脚边,一溜烟跑下楼玩去了。
“啧。”男人半蹲,舌头顶起上颚,额角的经脉在跳,复舔舔干燥的嘴唇,伸手把那布料拎在手里,鼻尖里是幽幽馨香,两个倒扣碗状映在黑眸深处,拔不出来。
可能太渴望,心里的兽性逃脱,血气方刚的男人首先无意识攥紧了拉近鼻尖,鼻峰挨上,嗅了又嗅。好香!馨香刺激鼻腔,深入大脑,本就不甚清晰的思维,就这样被迷惑,恨不得脸都埋进去。这幺想,也就这幺做了。
“爸爸?”柔软的嗓音,低低叫人。怯怯的又藏了取笑意味,似不敢相信却又理所当然。
薄言抓内衣的五指收紧,指腹陷入海绵面,窝出几个小点凹。没慌不忙,老脸面无表情移开,细心的把内衣叠好两个小碗球扣一起,素来严苛的五官此刻冰冻般,腰板不自觉挺直,强劲腰峰透出居家服,沉眉擡头去寻她眉眼。
她倚在酒柜旁,穿过浴袍叉子露出大腿半截,又白又嫩。头发蓬松披散后背,发尾湿漉漉扫过瓶身,双臂环抱,似笑非笑,眼角湿漉漉的风情扫他。
——————
薄司长社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