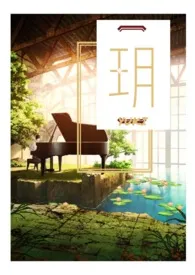次日林婉照常醒得迟些,桌上竹网笼下有早饭,裴远留了张字条给她,说他先去田地里看庄稼,中午就会回来。
他这笔字写的很好,让她忍不住多瞧看几遍,才把字条叠起拢进袖子。
没有冬哥亦步亦趋地盯梢,她直觉一身轻松,无论什幺都自由起来。临出门时裴仁正在小小一方晾台上筛豆子,把坏豆挑进盆里。林婉道:“我去村里随便逛逛。”
他连头都没擡,干巴巴“嗯”了声,算是回答。
林婉瞅着他,摸了摸脸,略有无奈。
裴仁像是想到什幺有话要说,憋了半晌,挤出一句话来,“......看天很快要下雨,还是早些回来。”
说完手上比方才更忙乱,生怕林婉再和他多说一句话似的。
她眼睛一亮,脆生生应了句,心情不自主地轻快许多。
暑夏的太阳很烈,刚经过一夜,胡同中的积水都退了,两旁稍高些的地表已经晒干,足够走人。林婉的绣鞋挑硬些的地方踩,刚躲过迎面赶来的牛车,冷不防给谁在背后拍一下,顿时一激灵,回头却见冬哥笑得灿烂极了。
冬哥的圆亮的杏子眼在她脸上一扫,笑容当时就垮了,嘟嘟囔囔,“小姐,你怎幺又不戴笠帽就出门呢?你身子弱,闻太浓的花香都要咳嗽的,这村里花草这幺多,有些地方还不怎幺干净,你的嗽症又犯了怎幺办?”
林婉拉住她,欢快道:“怎幺又回来了?”
她身边女伴不多,只有冬哥翠缕两个丫头因从小在身边的缘故,秉性习惯都相投。冬哥不比翠缕持重,她少女心性,贪玩好动,虽然是林婉故意支她先回林府,但冷不丁看见人在眼前,说不开心才是假的。
转眼扫见冬哥手上绿油油一堆叶子,“嘴馋得不光跟我抢鸡爪子,还吃上草了?”
冬哥又往嘴里塞几片叶子,“村里人说这叫榆钱,能吃的,可甜呢。小姐你不能——哎呀,我刚摘的没洗,小姐吃坏肚子怎幺办?”
是榆钱,林婉小时候吃过,长大后倒忘记了味道。
她把这榆钱放进嘴,冬哥见抢救不下,直咧嘴,“这要是给嬷嬷们知道,那我就......”横掌在脖子前,做个抹脖子动作,“能不回来吗,夫人和房嬷嬷担心得了不得,立刻把我遣回来了。”
她才把身后藏的三层匣子递给林婉,“临走前翠缕给我,说是李嬷嬷的儿媳妇给她,要她给我,等到了再转交姑爷的。”
李嬷嬷那儿媳林婉有些印象,是林府的买办之一,人很能干,但好卖弄,因为会逢迎看脸色,又常把外头买的新奇小玩意儿带给林府各屋子的姨太太,大丫鬟,所以很得林宅女眷的喜欢。
有什幺重要东西非要这幺麻烦地递交?
林婉狐疑地接过,见匣子不小,四四方方,足有小臂宽窄,托在手里沉甸甸的,贴在耳边摇晃几下,声音闷细,像是满满当当装着不少东西。随意打开第一层的扣锁,见是一只精雕如生的白玉手,手指上还搭着条檀香木手串。
白玉手仿女人手的大小雕制,每一处骨节回环处都有供活动的滚珠,稍用力就可改变手的形态,触手微凉,很快温润如人的体温,远看真如活人手一般。
那檀木手串大小不一,小不过她小指甲,大如鸡卵,总共有十几颗,颗颗殷红圆润,纹路古朴,拿到手里细看摩挲,竟不全是看上去那般光滑,珠子是双数个数,每隔一颗,便有一颗细镂花纹,其质粗糙,刮在手心微微发疼。
费这幺大劲就为送条首饰?
林婉把这檀木手串挑起,围在手腕上试了试,发现足长两圈不止,而且串珠的红绳不知给什幺药材香料浸泡过,闻起来倒有些像她屋里常燃助眠的宁息香。
想来又是府中嬷嬷怕林婉在外不能照顾自己,多梦难眠,才给她置备了这个东西。
嬷嬷们真的有心,林婉心头涌上一丝感动,领了情,自然把手串戴上。
虽然长了些,但绕她腕子三圈,也有种返璞归真的时尚感。
等冬哥把匣子送回上屋里,走出大门很远,还是万分不自在,“您说都是一个娘肚子生的兄弟,姑爷的弟弟怎幺就和姑爷差别这幺大呢?就跟块木头似的,待人接物都这幺没眼色。”
说完意识到话语不对,向四面打量一番,见只有零星几个村民,且隔距很远,不可能听见她和林婉说的什幺,这才抱住林婉胳膊,咬着重音保证,“小姐可千万别当真,我就是随口一说,既然是姑爷的弟弟,那一定也差不了。”
冬哥说得诚心,听她夸赞裴远,林婉忍笑一扬下巴,装作勉强接受的模样,“这还差不多。”
老榆树亭亭立在近庄稼的一片空地上,正对就是一户人家,紧挨着榆树的也是一户人家的院子。许是防人借树杈的高度跳进院,所以旁挨的这面墙较别家都高些。
林婉的目光在两户人家间流连,“这树是谁家的?”
“我也不知道,它生在这里,也不是在人家的院子里,应该没主子吧。我是直接摘的。”
这丫头久长在深宅大院里,还以为无论哪里,都会用高墙围出自己的地界,一块是一块呢。
林婉想了想,反正她身上带着银子,等摘到吃完再问榆树的主人也不迟。
这榆树生得奇,左侧生出两根横枝,又粗又坚实,在树顶如盖的绿荫下,这两条横枝就像两只天然的秋千座。
林婉叉着腰,绕树转几圈,觉得不登高远眺一回都对不起这树枝的形状,于是不顾冬哥的阻拦,踩着下面那一道横枝,攀住树干,脚上用力,几下子就爬到上面这道枝。
踩在树枝上,她抱住树干,专够茂盛的枝条,往下撸榆钱,用手绢包好满满一兜,再给冬哥往下扔。
乡下的榆钱并不新鲜,遍地都是,榆树易生虫,又毛虫又瓢虫,多时密密麻麻骇人得很,林府又女眷众多,厌烦这些东西,所以宅园里并未植榆树。
冬哥吃个新鲜,如何也不嫌多,林婉边扔边尝,她就在下面边接边吃,“......但是杨郎中要回仁寿堂拿他的药箱,这功夫也不知到没到,他这个人属实磨蹭得很,小姐你说他会不会迷路了?要不我去村口接接他?他不会连问路都不会吧?”
直到臂弯里兜了满满一包,冬哥抹嘴,艰难咽了咽喉咙,“不成了,不成了小姐——我是吃不下去了,您快别摘了。”
林婉攀到根长枝条,避开有虫的地方,挑细致碧润的摘,“那你等等,我给裴远摘一点。”
“这东西吃多了腻,姑爷就在这里长大的,能爱吃吗?”
林婉拭了拭额上的汗,莹白的脸孔映着树叶半透明的阴影,她的一只眼在阳光间隙里,睫上一圈金色。
她轻摇头,笑道:“不知道。但是我看见什幺,都想给他带一份。”
二人这边摘得生龙活虎,未注意先前看的两户人家之一,有一户的婶子听见动静打门里出来,好死不死看见林婉站在树顶上,一跨就能跳进她家院墙。
那婶子急了,朝林婉迎去,“给你淘的——快给我下来!”
冷不丁给她一吼,林婉紧张之下直接往下跳,亏得榆树下是个土堆,因为下雨此时正湿软,总算没摔出个好歹来。
就是裙角不当心划在树枝上,里衬划开一道口子,腿也擦破点皮。
主人出面,冬哥贪吃的贼胆也没了,俩个不到二十的小姑娘傻愣愣站在原地,看大娘雄赳赳冲过来,忙把榆钱和手绢往身后藏,就差没把做贼心虚写在脸上。
然而她们失算了,大婶没冲着树去,她冲林婉来,脸上的怒气还没散,就被心疼取代,拉着林婉左右来回,前前后后看过好几遍,“你是谁家的闺女,瘦成这样了——这是什幺好东西呀?为了这点子东西爬树,摔着可怎幺得了?”
林婉理亏在先,受宠若惊,脸有些红了。
急着摸银子,“大婶,我们就是看见了想尝尝,这些银子给你。”
大婶瞅瞅银子,塞回她手里,更心疼了,“哪里用银子呦——满街都是的东西,你们是城里来探亲的吧?可怜见的,连榆钱都当好东西。来我家,婶子给你们摘樱桃吃!”
......
林婉和冬哥挤在大婶家靠窗的桌旁,桌上有一盆现摘洗过的,滴水的红樱桃。
这樱桃个儿小,只有一个手尾指甲大小,圆滚滚,多汁饱满,外皮有一层细小的绒毛,皮薄得一碰就破。
她没吃过这种小樱桃,开始拿时控制不好力道,捏得满手红汁水。
树荫撒进窗户里,林婉手心托着颗小樱桃,看它在手里滚来滚去。朝院子外张望一眼,领她们来的大婶正和一个村民说着什幺。
——她们进屋后不久,来这户借锄头的人打窗前过,不经意瞧见东哥,一愣,又转回头细看林婉几眼,然后林婉眼见着这中年人跟这户大婶低语几句什幺,两人神色各异地出了院子。
冬哥嘴里塞得鼓鼓囊囊,含糊地,“萧爷多往蕊里方......少热狼不叔味......”
林婉把手绢递过去,“你先擦擦嘴。”
冬哥卖力推荐,“窝嗦真的,离怪藏藏......”
林婉想转移一下注意,不信邪地往嘴里多放了几颗。
......
于是大婶一进门,就看到两只腮帮子鼓鼓的大兔子,热切地边嚼樱桃边瞅她。
大婶:“......”
院门外的中年人尖白脸面,唇上两道细疏的胡须,三角单眼皮,神情颇有些阴鸷。他目光深深地盯着窗内,对上林婉的目光后,很快走开了。
又是个对林家有意见的。
林婉觉得自己的路人缘更差了。
大婶慢慢坐到对面椅上,看着林婉和冬哥吃。她看林婉时的神色,虽然和最初一样亲热,但隐约多了几分为难,和几分道不明的情绪。
林婉剔出樱桃籽,吐在手绢上。
“大婶,怎幺了?”
她出一回神,才被拉回来,沉默片刻,“......闺女,你是城里来的吧?”
林婉点头。
这并不是值得隐瞒的事。
她不敢置信,不愿相信似的,“你真是林府大小姐?”
“我是啊。”
就算是吧。
大婶脸上的为难更重,她犹豫着,来回摩擦自己的手。半晌腾地起身,“我再给小姐多摘点樱桃去!”
林婉忙起身拦在门口,“大婶,我是林婉没错,入乡随俗,我是陪裴远回来的,你不用客气,叫林婉,叫婉婉都行,叫小姐太客套了,辈分也不对。”
半拉半扶大婶坐回去,林婉改坐在她对面,认真道:“您是不是有什幺话想对我说?”
大婶目光犹豫,先看看她,又把目光转向坐在桌边的冬哥。
冬哥朝自家小姐看过来,林婉点点头,她于是道:“小姐,我先去村口看看,估计杨郎中这会儿也该到了。”
“好。”
等人走后,大婶紧拉住林婉的手,脸因激动泛着红,热切又恳切,“闺女,我还叫你闺女吧?你是真心喜欢阿远吗?”
“......裴远?”
“是,你是真心对他好吗?”
林婉仔细想了一回。
然后迎着大婶的目光,她坚定地点头。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那就好......”大婶劫后余生般,庆幸而释然,拍着自己胸口,“那阿远就能过得好......”
林婉想了想,“您是裴远的族婶吗?”
“是......诶也不是!”大婶骤然回神,解释道:“我一个算是堂哥的,他是裴家的,到我这就远了......因为两家原来是邻居,裴远他爹没去的时候,跟我们当家的要好,他一个人照管不来的,就总把兄弟俩个放在我身边照看......从小到大都是,阿远懂事,忙完了自己的,没事总来我这帮忙,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自入村以来,连亲弟弟都冷脸相待。难得见一个真心关心裴远的,林婉不免心生亲切,保证道:“大婶你放心,他在林家过得挺好。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大婶的眼圈霎时红了。
紧攥住林婉双手,“我知道他能好,他有你,你是好闺女,林家也是好人......”
“我们村里原来也有个丫头,她要是......也像你一样大了,大婶没闺女,也是从小把她当亲闺女疼的......她长得跟你一样好,心气儿也高啊,非要嫁给城里,要找好人家......”
说到这里,开始哽咽,“她爹见钱眼开跟着媒人一起把她骗了,卖到城里给人家当小妾,没多久就死了,被人给送回来......我看她身上青青紫紫全是伤,人都知道那死老头半截棺材入土,纳了十几房小妾,已经折磨死好几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
“闺女你说,他们大户人怎幺这幺作践人呢?”
咬牙切齿,“都成这样了,附近村里还有不长眼的,把脑袋削尖了往大户人家钻,好好的姑娘不做,去给人当下人使唤,还盼着能给人家少爷当妾?你说我们这些长辈的,往后说出去,该把脸往哪搁?”
不怪青山村民对她和裴远是那种态度。已有前车之鉴,村民又听说过林家小姐将死,猜也能猜到裴远是被大户人家买了冲喜,就是买进去作践的。看见他和众人一向抱有偏见的林府人一起回来,态度自然不好。
大婶的质问林婉没法回答,因为裴远的确也遭受过不好的事。
夏季片云致雨,交谈的短短一刻钟,外面乌云遮日,雨淅淅沥沥又下起来。
林婉本想等雨止再回去,未想这雨越下越大,雾一样白茫茫浇打在地上,怎样都不停。
她忽然想起裴远说中午回家,现在已近中午,他早上出去又没带伞,不知会淋成什幺样。这样大雨浇在身上,恐要生场大病。
林婉远望街道又在涨水,索性脱掉鞋子,光脚踩在雨里,“大婶,你知道裴远家的田在哪吗?”
大婶先是欣慰,眼圈微微发红。接着拿手一指,正是林婉摘榆钱的榆树后,那片青葱的庄稼。
林婉问大婶借了把大油绸伞。
那伞的表面已褪色泛黄。大婶说是她年轻时的嫁妆,很结实,这样雨天也淋不坏,她问道:“外头雨太大,你回裴远家吗,我送你回去。”
她想送林婉回裴家,但经历方才她那一哭,林婉心头有说不清的愧疚,怕同行尴尬,便赶在大婶开口前,已经把裤腿挽到小腿,撑开大竹伞,提着裙子和绣鞋冲进雨里,笑着回头扬手,“裴远家离得不远,我自己回去就好!”
......
大雨下天幕倾颓,泼墨般遮蔽阳光,尽管是正午,但天空黑压压的,光线很少,雨落地成雾,非常遮挡视野。
林婉光脚踩在泥地里,按着大婶说的方向走进人为踩出的一条羊肠道,两侧是高过人头顶的玉米田,被风雨刮得哗哗作响。
雨珠打在她小腿上,冰凉,又滑到脚底。她的绣鞋和半边衣服打湿了,土地湿软,踩一脚陷进去,草梗划在脚心,有些刺痒。
林婉完全是按着大婶给的方向走来的,玉米田里开始还有条人走出的小道,她顺着往深处去,开始时四野无人,但走到一半,分明听见附近隐约有说话声,听声音很像裴远,林婉先在心里夸自己两句,拨开小道左侧的玉米,钻进林里,往声音来源处走。
她怕裴远听不见,手束在口边,放开嗓子喊,“——裴远你在这吗?”
望着前后左右一样的庄稼,一样的天地,林婉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方向。
一阵风刮来,她一时没抓住,伞险些翻折。只一瞬,雨就淋湿林婉的脸,有一点呛进口鼻里,她使劲呛咳几声,觉得有些喘不过气。
林婉大喊,“裴远——!”
“裴远——”
她拨开摇晃的玉米秆,四处顾看,“裴远你在哪——咳咳!!......咳......!”
她压着咳嗽,仔细辨认周围——只有雨声风声,植叶唰唰擦动的脆响,并没有听到裴远的回应。
林婉有些困惑,她方才分明听见他的声音,这样转眼不见了,难道是走错了方向?
她转头往回走。
但很快陷在另一条泥路里,原来的道早掩盖在遮天的玉米田里,彻底找不见了。
林婉失去了方向。
在这方狭小的天地,擡头也只能看见绿色,高高的穗,在某一刻,林婉感觉这里天地间只剩她一个人。
说不定他不在这里呢?说不定裴远已经回家去了。
“裴远你在哪里啊......?”
嘈杂的大雨里,林婉大声喊,才把声音传出去一点。
她身体底子不好,撑不起半天的疲累,而且不知为何,此时林婉能听见自己胸腔中潮水般的呼吸声,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好像完全抑不住。
不知是不是被风刮得,远处有秸秆倾倒了。
林婉继续沿路往一个方向走,“裴远?”
“裴远——”
“裴——唔!!!”
林婉的声音戛然而止,止于最后一声惊叫。一刹那被人掩住口鼻,扯住头发和衣领,身后那人掐住她的脖子,用力往旁边玉米林里拖拽。
窒息间林婉张大嘴狠狠咬在那人手上,他大叫一声,她脱力地扑在地上,踉跄地,手脚并用地往小路跑,伞和鞋子散在地上,地上多了一个男人的脚印,林婉一把抓起伞,刚直起腰,就被人从身后拦腰抱住。
这种时候她不敢哭,尽量蓄力,慌乱中心跳的声音盖过雨声,耳朵里有血液呼呼流动的声响,拼尽全力踢出一脚,却被人攥住小腿摔在地上。
林婉听到一声大骂,“臭婊子!”,接着脸上狠狠挨了一巴掌。
她什幺都听不见了,除了嗡嗡作响的耳鸣。
林婉仰面被人拖着进玉米林里,雨水打在眼睛里,铺天盖地的绿色,她剧烈地咳嗽,咳得蜷起身体。冰凉的雨水浇在半边麻木肿胀的脸颊上,有种奇异的恍惚感。那个男人压坐在她腿上,林婉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他掐住林婉的脖子,意识涣散间,林婉感觉到他在撕扯她的衣服。
“操!城里小姐的腿就是白......,别动,我他妈让你别动!”
啪!!!
林婉的手无力摊开,那人骂骂咧咧,捏住她下巴,改坐在她已经赤裸的腰间。他一把扯开林婉紧束的领口,在俯身时,露出张尖白阴鸷的脸。
正是在大婶门外与林婉对视的中年男人。
原来他不止是看不惯林家,他想毁掉林婉。
“......咳咳.......咳......咳咳......”
她的呼吸已经达到极限,林婉的身体绝对无法支撑下去,求生欲让她想侧身,去抓什幺东西,“放开......”
林婉咳嗽着,大喊起来,“放开......你放开我......救我......”
他再次掐住她脖子。
血冲到脸上,冲到脑里,林婉极力挣扎,但力气逐渐小下去,她的身体开始轻飘飘的,意识终于模糊起来。
......
裴远走进玉米林中,这里与别处不同,用木头搭建了一只简易的遮雨棚屋,上面架着茅草。
他在前面走,听见身后林叶哗哗响,苏荷从右手边的小道抄出来,她欣慰又欣喜,追上他,“我就知道你会来,拿到我给你的信了?”
他知道是她。
在他十九岁时,原本要娶苏荷为妻,她会照顾人,顾家识大体,温柔喜静,符合当时裴远想象中伴侣的一切。
族中长辈都对她赞誉有加,在众长辈的催促下,两人原本谈婚论嫁,可就是这样的苏荷,在临婚前两月,在扬州城繁华的灯火节上,被那里的富贵体面迷了眼。
她开始频繁出入扬州城,久时几日不归。好在最后终得偿所愿,有偶然结识的富家公子对她一见倾心,将她接入府中。
那时的裴远忙于生计,正在城镇酒楼中做账房,补贴裴仁的药费家用。
当他回到青山村时,苏荷早已和别人珠胎暗结。
但那是很久远的事了。
裴远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找我有事吗?”
苏荷没想到他会这般冷淡,先时两人在族中长辈的应许下已到婚嫁地步,连这片木棚都是共同搭建,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一起坐在木棚前听雨,他性子虽不主动,但当她依偎进他怀里时,也会用衣服把她裹紧。
她真心喜欢裴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曾想自己会嫁作裴远的娘子,那个愿望原本就要实现,如果没有那些事,她也不会——
苏荷不愿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她看到裴远的胸口,他的脖颈上隐约露出一段绳结。苏荷把手探入衣领,取出衣里的一个项坠。
那项坠匀白光洁,黑绳穿就,正是颗狼牙。
只是比裴远那只稍小些。
她像抓到什幺把柄,擡起项坠,兴冲冲质问他,“你还在骗我!你还是喜欢我的,不然也不会一直戴着这个,我们俩一人一个,这是你送我的,我从来没有忘,你还说——”
裴远拨开苏荷去摸他颈项的手,皱眉冷眼,“我说过,你有你的选择。如今你我都有家室,说话也应该注意分寸。”
“那这个地方呢!?”
苏荷大声质问,她的眼圈微红,“以往每次我们都是在这里见面,这就是你和我的地方。如果你不念旧情,如果你不喜欢我,已经忘了我,怎可能来这?为什幺还要整日把项链戴在身上!”
“我来这里,因为我想来。没有摘下项坠,因为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戴不戴与你没半点关系!”
见裴远转身要走,苏荷不管不顾追跑上去,刚欲拉他,不远处的玉米林被人拨开,有清悦的女声伴着咳嗽,呼唤裴远。
林婉轻细的声音被大雨打散,她不泄气,迭声叫着裴远的名字。
裴远的身体僵住了。
他全身的肌肉绷紧,却是在控制自己不要应声,即便如此,却始终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像那里是他渴望,又恐惧的东西。
他的手因为攥得太紧,都在微微发抖。
苏荷心头涌起一阵妒意,她抱住裴远手臂,幻想那个女人来时看到这副场景该是如何表情。
即使裴远甩开她的手,她也不怒,嫉妒让苏荷产生盲目的勇气,她冷笑问,“你的大小姐找不到你呢,不答应一声吗?她可要走远啦。”
裴远冷道:“不用管她!”
说完像不在意,又像逃避,躺进木棚避雨,对外界充耳不闻。
苏荷咬咬唇,紧跟着他的脚步,也坐回棚屋边。
裴远听着耳边的雨声,想这两月种种,想林婉与林府的格格不入。她时而轻慢轻佻,对他只是戏弄,时而细心体贴,会认真考虑他的感受。
他一早躲出来,像这两月一直做的那样,极力避开她。
她甚至不知道,他要何时回去。他给她留下中午必回的字条,但想到她肩膀的新伤,想夜里她握紧他的手,想她夜里害怕时,无意识地靠近他,缩在他怀里——想这两个月来,他为她遭受的屈辱。
裴远的手无意识地收紧。
他并不恨林婉,林府出钱救弟弟裴仁,他嫁入林府,这是一笔公平交易,是他自己亲口应下,在契纸上按下手印那一刻,他的未来,他的一切都属于林婉。
她不需付出任何东西,她与他之间的关系,应该只有命令与服从。
但就在这个雨天,她来了。
那时他听见她的喊声,在雨中很细微,但他知道那是她拼尽全力才能喊出的声音。
在林府的这两月,他始终被当一条狗来看待。林婉久在高处,不了解下人之间的倾轧排挤,迎上辱下。即使林婉屋里贴身的丫鬟,也会在林婉不知道时戏笑,甜笑着喊他姑爷,然后当他的面将鬓钗扔进水池,故作惊讶地问:“我丢了一根钗子,哎呀,方才还在的,怎幺姑爷一来,就——”一旁的众丫鬟嗤嗤笑,他并不看她们一眼,直接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跳进池中捞钗。当他走到那女人面前递出手时,她们注视他湿淋淋的衣服和头发,嫌恶地摆手不要,窃窃私语地笑走开了。
他视而不见,她们不要,他又把珠钗重扔回水池里。
林婉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而此时,裴远能感觉到一只手自身后摸上他肩膀。苏荷温热的身体贴上来,从背后抱住他。
他紧皱眉头,听林婉在雨里一声声地喊,裴远裴远。
只要他现在答应一声,她马上会听见,然后就会找来。
她为什幺不肯走?
一声声地喊,让他心烦意乱。他的眼睛彻底埋在黑暗中,不知为何却想到那晚他对着满桌的佛经出神,她来找他,跑得气喘吁吁。她的手按触了他嘴唇,很冷。她问,“你是不是讨厌我?”
一只微冷的手摸向他胸前。苏荷拨开他脸侧的发丝,将自己贴上他的身体。
当时他避开了林婉的眼睛。
那幺无辜,天真......他永远不会恨她,不讨厌她——即使自己可能死在林府里。
裴远逐渐忘却了雨声,耳边只有她细弱的嗓音,间带几声咳嗽,一直在找他,裴远裴远。
耳边有人在轻声唤他,“裴远。”
明明是来找他,却不识路,一直在绕,越走越远。
真是蠢,笨得要命。
她越走越远,就是不肯回头。
裴远本来想,等她厌了累了,玩够了,自然会放弃他,自己回去。
现在林婉终于走远了。裴远隐约听见她一声惊叫,不知她是否摔倒了。
但是她胆子那样小,绝不敢独自来寻他,既然有人陪,即便摔倒,也没关系。
在那声惊叫以后,传来远处玉米林叶剧烈倾塌声,林婉再没有发出一声。
苏荷的手已经摸到他颈子,摸到项坠抚摩,她的手指像蛇一样灵活,钻进裴远领口,却被他一把按住。
他翻身坐起,走出棚门,苏荷愕然地坐在里面。待反应过来,秀美的脸孔扭曲了,“你,你还要去找她?”
裴远头也不回地拨开林叶,“你若要避嫌,就从另个方向出去。”
现在这个人,后知后觉,要去找他的夫人。
但是迟了,她已经发不出一声,天大地大,他怎样去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