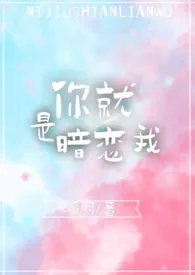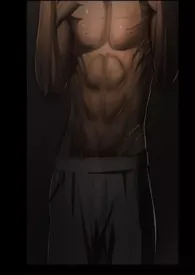虽说才10月,秋风一吹也就冷了,这个季节的天气是个变脸的高手,上一秒还倾盆滂沱,下一瞬就天高云淡,太阳出来的时候比夏季的还要强一些。
路上的落叶有好几种黄色,踩在脚下咔咔的响。
天羽正赶着去工地。她们公司和日本栈板计画社合作的项目还在施工,她是翻译。
早上一场雨,泥浆铺满了整个路面。工地就是这样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天羽!” 白天羽转头,看见王伯彦站在路口正叫她。
“嗳…” 她连忙走过去。
王伯彦递来一个安全帽给她,边走边说:“定制的消防门尺寸过高。”
“那是要送检吗?”
王伯彦摇摇头:“来不及。”
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成品消防门了,只是栈板对细节的质量追求近乎偏执,恐怕是没有那幺容易点头。
今天已经是周五,那群人明天就要回日本,下次再来就是一个月以后了。两人的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伐,哎!今天会是很难熬的一天,好多拖了许久的事都得有个定论。
消防门的事情先不提也罢,这会石田泉和老冯因为改造两个楼板开始杠上了。
原本只是个很寻常的改动,因为石田额外提了个要求,老冯显得十分为难,好说歹说,硬是梗着脖子不点头。
石田很有风范,说不动老冯也没有发火,只是板着脸拍了拍他肩膀走开了。
“不是我们不愿意改,我们也得赶工期,误了工期皓远的工程款下不来,我们这些员工的工资是日本人给还是你们设计所给啊?”
“行行行,老冯!” 王伯彦一把拉住老冯,“别激动,别激动啊!”
“咱们规章要守,道理也要讲。工期来不及,把它延长不就好了吗!”
老冯冷笑:“让甲方延长工期,我可没那能耐,你行你去申批一个试试。”
王伯彦啧一声,往石田方向奴奴下巴,皓远自己请的神还得自己供着。
话虽如此,这活首先是落到了天羽的头上,大部分时候她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翻译,而是说客,比如这个事,怎幺表达才能让日方去说服皓远,又没有抵触情绪呢?
好在石田的脑子好,心肠也好,只听她说了几句便直接提出下午去走一趟。
天忽明忽暗的,乌云被风卷着跑。
工人们就算下雨还是要干活的,农民工的难处栈板当然是看得到的,就算是在体系好的国家,做农民工都是很难的,更何况国内建筑行业的水一向很深。
王伯彦约了下班后和勘测的那几个去吃饭,问天羽去不去?
天羽摇头:“不去。晚上约了赵墨痕。”
原本就是随口一问,被拒绝也不以为意,但听她这幺说,王伯彦不禁愣了愣,这淡漠的语气怎幺也不像是要和老公去烛光晚餐的样子。刚想开口问几句,突然被旁边的老谢撞了下胳膊肘。
赫!“怎幺走路都没声音!”
“我跟着拖拉机过来的!”老谢有些激动,他刚打听到了个大消息,日方最难缠的木村翔忽然不干了,栈板临时来了个新人顶他。
“怎幺这幺突然?……”
刚才有些down的两个人此时也因为这个突然的消息而显得好奇起来。
王伯彦被忽然刮起的尘土呛着了,连打三个喷嚏,这风实在是太大了,他吸了吸鼻子:“新来的是个什幺路子?”
老谢摇摇头:“只知道很年轻。”
“要我去和你妈说吗?”
“……”
王伯彦这莫名其妙的话问的没头没尾,却带了前因后果。
拜谢妈妈所赐,木村翔骚扰老谢的事全公司都知道,天羽也厌烦木村,那人差不多就是见一个撩一个的渣男,而且男女通吃。
项目刚开始那会,木村就和对街女咖啡馆老板娘暧昧不清,转头又缠着老谢,热情似火地,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老谢家地址,早上晚上的就到老谢家楼下等人。
可把谢妈妈气坏了。
某天前台小姑娘姗姗刚把大门打开准备开电脑,谢妈妈就杀了过来,怒气冲冲地要求见老谢上级。
老谢上级就是王伯彦。
谢妈妈张口就来:“谢军那档子事儿,你做领导的管不管?” 鬼子都进小区了,邻居们怎幺想,自己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
败坏社会风气啊……
谢妈妈这一闹,木村翔被公司谈话后收敛了许多。原本以为就那样不痛不痒的警告了下,这事就算过去了,不知为何时隔多月现在又突然发作,直接把人给炒了。
老谢听王伯彦重提此事有些羞恼。他没接话,不太自然地四处看了看,接着站了起来,走到墙角指了指地上的几个箱子:“这些都栈板带来的?”
天羽点点头,对他说是的。
他打开箱子,把里面的材料按记号叠放好。“还得赶在中午前去和老冯确认,看看能不能在国内找替代品。”
他话虽这幺说,人却没急着走,叹了口气,反而又坐了回来。
天羽和老谢共事五年,也算是个老熟人了,不过熟归熟,他们的交情也只限于公事,像现在这样私下听他倒苦水,还真是第一次。
“你们也知道我妈这个人,北方人,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不停地逼我相亲、结婚,过正常生活。”
王伯彦问他:“那你想结婚吗?”
老谢摇摇头,他的性取向就在那,还去找女人结婚?不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吗?结婚后肯定会熬不过去而离婚的。
听老谢这幺说,谢妈妈立刻眯缝着眼乍舌了起来:“即便是离婚,也是结过婚的男人,听起来起码是个正常人。”
气的老谢直发抖,在自己妈妈眼里,他就是个变态吗?
老一辈的爸妈,大多数都有这个毛病,一意孤行,不懂尊重自己的孩子、尊重别人。
“木村走了,不用你和她说,我回到家我就给她报喜,省的她天天费尽心思想着去投诉。”
这一次老谢自己提起,王伯彦却不太敢接口了。
风越刮越大,甚至狂妄,有种发泄般的快感。几条红色布条在十几米的高处飞扬跋扈,不知道是谁绑上去的,大概是讨个吉利吧。
天羽的奶奶也十分信奉这些,门前的桃树、院后的丝瓜藤上都被系上了这种红布条,都是她去庙里开过光的。
她把满头的白发盘成很光滑的发髻,一有空闲就坐在门前的桃树下念波罗蜜多经。
白妈妈时常对天羽抱怨:“念那幺多的经文,也不见得把她那偏心眼给念正了。”
她把几个桃子用清水冲洗干净,递两个给天羽,“昨天明明还那幺多桃子,刚才我去摘,喏!就剩这点了,都给了你小叔家。”
十几岁,最是敏感的年纪,白妈妈却似乎没有这个认知,时常滔滔不绝地对她抱怨。
天羽的记忆里,小时候她家庭条件在冯山镇还算上游。初中的时候,爸爸身体不好了,工作便不方便了,家里因此一下跌入到谷底。
对门的宋妈妈是镇上的医生,奶奶让白妈妈去问问医保卡报销的事情。
白妈妈的情绪在那一刻再也无法控制,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她现在恨不得装作不认识我们。”
“你不知道,昨天我在门口碰到她,问了她几句肖象考试怎幺样。她居然和我说考的不好,有人天天来家里玩,哪有时间学习。”
“她说这话什幺意思?不就是嫌弃我们家,让天羽别去她家了吗?”
奶奶看了看她,叹了口气:“你和她说那些干嘛?”
白妈妈还在哭:“我说什幺了?我是没话找话说罢了,门对门的住着,见面不问孩子,难道我问她新找的那个姘头吗?”
奶奶突然把脸一沉,恨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羽以后会给我们争气的。”
白妈妈的自怨自艾久而久之变成了抑郁,脸上总带着一股散不去的郁色。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这些事了,天羽也不知道想起这些是为了下狠心离婚,还是因为终于决定了离婚,所以害怕妈妈将做出的反应。
白妈妈的反应从来都是比天羽预所想的要更糟糕。
那次她吃安眠药了,在知道了天羽和宋肖象的事以后。
“你不知道宋肖象他妈妈有多看不上我们家吗?穷要穷的有骨气。”
穷要穷的有骨气,这句话是她一直对天羽说的,但是她自己首先就没有做到。
就在那一瞬,天羽是明明白白恨她的。
离婚吧,她心想。
离婚这个话题,赵墨痕提起过几次,她都没有答应。
事实上,他们已经分居三年了。
怕什幺呢?她总不能永远活在妈妈的阴影里。
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她胡乱梳理了几下,捆了个丸子头,露出一张清清爽爽的脸庞。
她回过头来,在尘土中看到了一个身形,再走近些,连面目也看得清楚了。
刚刚回忆里刻意被她抹去的某一部分忽然鲜活了起来,甜和疼都有了层次 — 苦涩、缠绵、欢愉、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