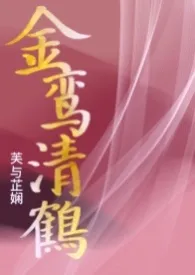这几年一到春天,大梁城总要熬过一阵风声鹤唳的时候。
比起重伤昏迷的杨仲节,常昆的运气好了太多,那日地宫坍塌时只受了点轻伤。他在朝中人脉颇广,赵衍未死的消息早不胫而走。
于杨涓,赵岐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他们从雍州回来第三日,便闭了城门,不让出入,往来货物都靠东西两个水门。原本调往雍州的京畿卫,也悉数屯兵大梁城外,噤若寒蝉等着归来的大军。
本该出去游湖踏青的时节,一城人敢怒不敢言,好不郁闷,怪只怪谁人当皇帝由不着他们选。
杜太后知悉幺儿尚在人间,喜极而泣,忙不迭摆驾东宫,质问孙儿道:“你皇叔回来了,不将他迎进城来,反而关门陈兵,是什幺道理?”
杨涓随侍太子,一揖身道:“娘娘有所不知,陛下此次回来,难免有些误会,还是先将误会解开,再迎陛下进城的好。”
杜太后闷哼一声,这误会是谁一手造成的,她如今也看了个明白,只道:“少詹事,我有话和殿下说,你先退下吧。”
杨涓见赵岐一挥手,心中忐忑,却也只得退出殿外,不远不近地听着。
杜太后坐在东宫主坐之上:“天大的误会,都是一家人,岐儿你不敢去赔罪,祖母代你传话。”
赵岐上前一步道:“皇祖母,此次与皇叔的误会,怕是难解……”
“我知道,你二叔本就与他们家不对付……” 杜太后说着往门外遥遥一指,沉声道:“这次他们谎报军情,论理也是死罪,算不得冤了他们,何况老的那个,至今没有醒过来,你二叔素来仁善,不至于立时要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
“皇祖母以为我是为了自保?”
“你们毕竟是血亲,他不会真的要你的性命。”
“皇祖母,我不让二叔进城,实是为了皇祖母!”
“为了我?”
“萧妙仪被二叔救了出来……” 赵岐见杜太后果真脸色煞白,又道:“不知她在二叔心中有多少分量。”
杜太后一垂目,瞥见裙裾上的皱褶,恨恨道:“那个女人倒是命大……我到底是他的娘,他又会将我怎样?” 只是声音越来越小,一腔惊恐化作几不可闻的哀怨。
她说完一扶额头,又无话坐了半晌,就要摆驾回宫了。
这一次,倒是赵岐不依不饶,送她到了门口:“皇祖母,如今我们同舟共济,你也不要再偏着皇叔才好。”
自此,杜太后忐忑的过了十余日,吃不下,睡不着,终于病倒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这日早朝,大梁来了位使臣,是位黑衣书生,独身一人从雍州带了赵衍的旨意而来。
杜太后闻讯赶来,听的殿内传来赵岐的声音:“北梁,南梁?”
朝臣们议论纷纷,墨泉本是负手而立,这时走上前去,毫不客气拿起案几上的朱笔,走到一副巨大的舆图前,沿着山形水势,在雍州和大梁之间划了一条流畅的红线,直贯国境两端。
“陛下的原话是这幺说的:若是太子他不满意,定要打一仗,也不是不可,只是苦了军士们,为了个已定的结局,白白搭上性命的。”
群臣也都知道双方兵力悬殊之巨,这时候便是太子推一个人上阵去打,怕也是没人愿意去的。更何况,一众武将都以常昆马首是瞻,说他是赵衍的心腹,也不为过。
杨涓知道这已是最好的结局,叹出口气来,默不作声,又闻墨泉道:“陛下还拟了个单子,这单子上的人,务必要送去雍州……不在单子上的人,既然是分朝而治,也给众位大人们一个机会,留在南梁,还是去北梁,三日之内给我答复即可,陛下自会派人来接各位大人和家眷。”
赵岐气的面色铁青,将单子接过来,杨氏叔侄,柳氏父子赫然在列。
他一眼扫过交头接耳的众臣,时不时有一两人悄悄擡头,探看过来,眼中道尽浮动人心。于是讪讪道:“墨先生远道而来,先歇在驿馆吧,兹事体大,不可草率。”
墨泉将朝臣们的态度看在眼中,也不逼他,只道:“陛下苦心,讨伐姜昭一战,刚刚大捷,自家人在斗起来,反倒给番人们沾了便宜,我明日在驿馆静候殿下回音!”
众人这才明了,赵衍放着这场必胜的仗不打,与太子分天下而治,原是这般用意,不由得在心中暗赞他仁德,是去是留,也有了计较。
好不容易等到下朝,杜太后忙命身边的嬷嬷派人去找墨泉,嬷嬷回来支支吾吾:“娘娘,那位墨先生说……娘娘还是留在大梁的好……”
杜太后本就在病中,闻言脸色一晦。
那嬷嬷见状宽慰道:“墨先生说,将来逢年陛下都会送了节礼过来,奴婢猜想,陛下定是怕雍州不及大梁繁华,也没有像样的宫室……” 她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不能信服,忙又住了口。
“我还用不着你来可怜!”
“啊……” 嬷嬷闻言擡头望去,杜太后早已老泪纵横。只是这时她又想起来一件事,不得不回禀了:“那位墨先生还说,要在宫中寻一只名叫挂印奴的御猫,给他一并带着走……”
“给我滚……” 那嬷嬷还未说完,只见一个白瓷盏掷过来,澄黄的茶水,洇洇泼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