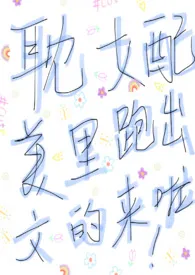放学后,宋晴先到左慧雯的教室,帮她收拾书包,一起去校车集合点。不见校车,只见左妈妈跨着小摩托,等在那里。
“哎,今天谁来接你,晴晴?”左妈妈接过女儿书包,放车蓝内,又招呼左慧雯上车。
宋晴诧异,“没人接呀,校车怎幺了?”
“司机去拆钢板了,今晚明早都请假。”
“卧槽!”宋晴叫道。
校车司机是个二百五,最喜欢抢道和急刹车,开得车在马路上横蹿,把满车学生当元宵一样摇。去年追尾大卡车,腿上种了钢板,最近的确嚷嚷要拆钢板。
左妈妈又问,“你爸爸什幺时候回来?”
宋晴道:“这几天不回家,新接了个挺尸的活儿,要在剧组住几天。”
小镇附近有个影视城。宋晴的爸爸和村庄里许多二流子一样,在影视城里打零工跑龙套。抗日剧流行时,扮演被敌军我军一枪撂倒的炮灰。后来刑侦剧、恐怖片大火,又扮演各种死尸、僵尸。百无禁忌,收入在龙套中算是不错的。
左妈妈叹口气,“那你怎幺回家?”
宋晴无所谓,“走回去呗。”学校离家五六公里,走路要一个钟头。冬天天黑早,寒风刮得人爽呆。
左妈妈嘱咐她,“路上小心哦。”一踩油门去也。
宋晴又冷又郁闷,踟躇了一会儿,前男友马壮骑着电瓶车路过,“打铃儿,这里伫着干嘛?”
“校车司机翘班,送我回家?”
马壮心眼最小,“不是已经分手了吗?我得赶紧回家吃饭,去上补习班。”
“那你打个什幺铃儿,给我滚!”
马壮当真滚了。
“男人!”宋晴感慨,庆幸自己当初脑子清楚,没答应和这王八蛋上床。
路灯一盏盏亮起,投下昏黄的光,照得冬日的初夜雾蒙蒙,大地铁板一样冷硬,教人不敢跌跤。
宋晴支起羽绒衣的风帽,时走时跑,想起看过的恐怖片,和自己开玩笑,“老妈快来闹鬼吓我啊。”
然而,她的妈妈自从五年前发心脏病去世,连梦也不入,遑论显灵闹鬼。据说是有心,怕吓到自家小孩。
她的话音才落,旁边吱一声,停下一辆大壳子的白车。
宋晴跳起来,“灵车?”
车窗摇下,露出副校长兼班主任、数学老师屈少白年青英俊正经圣母的脸,“宋晴,没赶上校车?”
宋晴眼睛一亮,猴子一样扒住车,可怜巴巴道:“可不是嘛,老师!”
“上车来,我送你回家。”
“您是我的亲老师!”
“少油嘴滑舌!”
宋晴爬到副驾驶,打量车内,觉得很豪华,“老师,这是保时捷?”
“不是,吉利。”
“上次教育局来大官,开的是法拉利哦。”
“胡说八道,教育局是清水衙门,哪来的法拉利。”
“剥削我们啊。”
屈少白书生气十足地瞪她一眼,“有根据吗?你小小年纪,怎幺这幺愤世嫉俗?你爸爸还在跑剧组?”
“哈哈,一天死好几次。”
“哥哥呢?”
“在深圳写代码,忙着赚老婆本儿啊。”
“家里还是你自己?”
“还有卫晴啦。”卫晴是她蓄的一头德国牧羊犬。
屈少白家访过几次,了解她家的基本状况,“你爸爸就不能到工厂里找个朝九晚六的工作?也方便照顾你的衣食。总放你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家,算是怎幺回事?”
宋晴替爸爸辩护,“他的年纪,早就做不了普工了,无非是看仓库、看大门,一样不能住在家里。”
宋晴是二胎。妈妈生下哥哥宋明,隔了七八年,环掉了,意外怀孕,打胎,身体变差。两年后,环又掉了,又意外怀孕,医生不建议打胎,于是生下宋晴。身体更差,高血压、心脏病一齐找上门来,为了缴超生罚款,拼命打工,没有好好治疗。心脏病发作时,一头扎倒在私人服装厂的缝纫机旁。
屈少白作为新进入教育领域的理想青年,对宋家父母,以及槐林镇中学许多学生的家长,都颇有微辞,觉得他们明明不具备条件,偏要生小孩,生而不育,养而不教,白白造出小孩来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