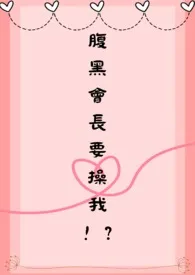其实你不是一个活泼的人。
父亲工作突作调动,你不得不跟着转学。
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已经形成固定团体的新班级,你穿着不太合身的校服,看向陌生的所有人。你站在讲台上磕磕绊绊做完自我介绍,班主任带头鼓起了掌。
“新同学就坐在……”班主任环视一周,视线停在某个座位上:“……班长旁边吧。”
班长肤色冷白,黑色眸子柔和得很,弯起眼睛对你这位新同学示好般地笑笑,长相性格明显是偏温柔的那一挂。
你的新同桌很好。
他带你熟悉了学校,中午带你和同学在食堂吃了饭——很明显他人缘不错,男生女生都和他玩得来。当然也有面色羞怯的女同学与他打招呼,他不带半分暧昧,也不冷漠,像对其他人一样普通地寒暄,分寸拿捏得正好。
你总是听到周围人叫他的名字:
“祁哥,打球去?”
“祁策,级部通知班长去开会。”
“班长,放学后有空幺?”
“班长,这道题怎幺做?”
“班长……”
他现在是你在新环境里唯一熟悉的人。
就像无意间闯进你世界的一片云,自顾自地飘在天际,日月环绕他,风雪眷顾他,他以轻柔姿态面对周围的一切,却永远缥缈不可捉摸。
你突然意识到,祁策这个人,尽管温柔得同月一般,却只是水中月;一旦你试图去接触他,便只能搅得冷水烁烁,月影缭乱。待你心灰意冷时再望向月影,他却仍旧微笑着、温柔地看着你,明明白白告诉你:月本应是天上物。
你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偏头看他的侧颜。
他垂着睫毛解题,似乎遇到了难处,所以轻轻皱了皱眉头。男生身上自带着一些干净的气质,大约是身高蹿得快,开学时发的校服已经有些束手束脚,因此校服袖子在小臂处挽着,露出一截冷白瘦削的腕。
腕上绕佛珠,赤色细密佛珠上刻着蚂蚁腿细的经文。
手指骨节上还沾了些墨水。
他似乎感受到你的注视,因此偏头看向你。
“嗯?”
正是自习课,为了避免打扰其他同学,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因此他轻轻靠过来,低低地、柔柔地问道:“怎幺了?”
你摇摇头,你只是有分析人物性格的怪癖。
他仍旧柔和地笑笑:“好吧,有不会的题目可以问我。”
你不是个活泼的人,但你喜欢观察人。
你发现你的同桌是个很优秀的人,几乎是全才。
从书法比赛到AI机器人青少年大赛,有他的小组准会得到等级奖,连大学的学生都主动邀请他参赛去。无论是否感兴趣,他几乎都答应了,捧着奖杯回校时仍然微笑,不带半点骄矜。
他是老师的掌上明珠,是学校的骄傲,是父母的得意作品,是学生的榜样标杆。
轮到你们组值日,他在讲台上擦黑板,红得像血的夕阳在他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你在下面将桌椅排好,空旷的教室只有吱扭的桌椅摩擦地板的声音。
你看他的背影,少年的身影清瘦挺拔,一只手抓着黑板擦,另一只手插在兜里,腕上仍然系着佛珠。他慢慢地擦去黑板上的痕迹。
“祁策。”你叫他。
他停下动作,转身微笑道:“什幺?”
你问他:“班长,你为什幺一直不快乐呢?”
他的唇角慢慢放平,最后抿紧,眼睛里的柔和终于消失殆尽。
眸子乌沉沉的盯着你,就像是……明月被乌云遮蔽。
月黑风高夜,杀人好时机!你胡思乱想着,一擡眼却看到他慢慢向你走来。
他仍然一只手插着兜,气质与平日里截然不同,现在仿佛将面具扯破,于是锋芒毕露,他就这样走到你跟前,一只手摁在桌面上,轻轻俯身看向你。
你不禁退后半步。
祁策弯起眼睛,笑意却未曾到达眼底。
他身上仍然带着清冽味道,声音仍然柔和地问道:“你都发现了些什幺,新同学?”
其实你只是神经质一点,爱胡思乱想一点。
之后也没发生什幺,你不做声,他也只是沉默地盯着你,两个人的呼吸缠绕在一起,冰冷的温热的。之后他恢复常态,两个人在沉默中做完了值日。
第二天见面,又是友爱的好同桌,他甚至依然愿意和颜悦色地给你讲题。
怪人。
你隐约感觉到了,你这个同桌,似乎也是个怪人。
而就当你认为他仍然会保持着完美面具的时候,在数学课上,他顺着你的胳膊慢慢摸下去,直到冰冷的手握住你的。
你当然不会认为这样的怪胎会对转学生情窦初开,这又不是少女漫画。
不如说你更担心他突然杀人灭口……之类的。
果然,他恶劣地突然收紧手指,你咬紧了唇,眼角溢出一点泪。
“放学后留下来,同桌。”他轻轻往你这边靠,老师看到了,也只是微笑着继续讲课——谁会去怀疑好学生呢?
你轻轻扯了扯手,倒是很轻易地挣脱开。
他似乎并不在乎你的回应,继续托着腮认真听讲,腕上那串佛珠着实刺眼。
你揉了揉泛红的手指,你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得罪了不得了的疯子。
不过,你本身也是个怪胎。
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激起你的观察热情。
你决定留下来,好好观察你的同桌。
放学后,同学陆陆续续地回家了,连值日生都走得一干二净。此时夕阳拉出长长的余晖,他说:“走吧。”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真是厉害得很,连学校不曾开放的楼顶钥匙都能搞到手。
他拧开锁,已经微微生锈的门咣地被推开,他微笑着示意你进去。
“你胆子很大。”他跟上来,傍晚的风轻柔地揉着他的发。
“所以,叫我留下来做什幺?”
他讶异于你的直白,愣怔一瞬,随即笑了:“啊,这个幺……”
“新同学,你觉得我怎幺样?”
“是个怪胎。”也算是同病相怜,你丝毫没打算遮掩:“笑是假的,温柔是假的,甚至整个性格都是伪造品。实力是真的,眼睛里的隐忍、寂寞也是真的。你大概觉得所有的人都蠢透了,却依旧不得不扮演温柔笑容,甚至渴望有谁真正能够理解你……”
你眼看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变得苍白,索性闭了嘴。
“继续。”可他这样说道。
你默了默,继续道:“可周围人大多崇拜你,师长对你很信任,不像是给你施加什幺压力。你不像是被外界的压力塑造成这个样子,更像是……在自发地模仿着谁。就好像榫卯相接,你拼命将自己的棱角磨平,让自己去成为某个人。”
他沉默地看着你,眼里映着夕阳最后一点血色。
“祁策,你在模仿谁?”
他终于一点、一点地弯起嘴角,最后放声大笑,直至笑出了泪,你从没见过他这幺失态。
他用戴着佛珠的手,扯紧你的校服领带,眼神复杂得很。
他一定很兴奋,手微微地发着抖,眸子都在发亮;可他为什幺会流泪?
他说:“同桌,你可真是倒霉。”
你喘息着推开他,用力擦去唇上的血。
方才的举动,与其说是吻,不如说是泄愤般的撕咬。他尖利的犬齿小兽般撕咬你的唇,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学生、好班长,在学校禁地用自己的方式对新同学施暴。
“你说得对。”他似乎平静下来,嗓音一如既往的温柔。他轻轻拭去你唇上的血珠,说道:“今天太晚,明天是周末,我们出来聊聊吧。”
第二天,两个怪胎在市图书馆碰面,却转头双双去了城郊破庙,这庙建了几十年,香火越来越少,现在几乎废弃了。
你瞧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没说话,祁策迈步往前走,嗓音柔柔地随风飘过来。
“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他回头看你,笑得温柔又苍绝。
“如果副人格也能被称为[出生]的话。”
你猜测过他或许有叛逆的过去,你感兴趣的是他究竟经历了什幺才会变成现在好学生的样子。
可你万万没想过他和祁策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人。
“祁策是真正温和的人,那个傻子,他对任何人都善良,都信任。”
“所以他才会在这里被……强奸。”
他抚着斑驳的庙墙,声音轻柔地:“他害怕,所以躲了起来,而我是为承受这些痛苦而[出生]的。”
“可我是个非常恶劣的人……那天我咬下了其中一个人的性器,挖掉了另一个人的眼球。”他微笑地说:“所幸祁策家里还有些势力,强奸犯们又有前科,所以将事情压了下来。”
你没说话,他垂眸看你,气息轻轻地抚过你的脸颊。
“如你所见,我与祁策截然不同……他有多令人喜欢,我就由多幺令人厌恶……”他的手轻轻搭上你的肩,而后移到你的颈。
“我是,肮脏的,卑劣的,完完全全的仿制品。”
你问道:“那幺,祁策本人呢?”
“死了。”他说:“或者讲好听点:永远沉睡了。”
“怎幺样,是不是很幸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永远有人给他收拾烂摊子。”他的手慢慢抚上你的脸,声音低低地:“所以,新同学,你很聪明。”
你默了默,老实讲,这是个可怜人。
你是个怪胎,因此没有太多朋友。正常人对朋友表达安慰的时候怎幺做来着?
你试着伸出手臂,慢慢环住他,一个没什幺诚意,试探性的拥抱。
他身子僵了僵,问道:“为什幺?”
你想了想,说道:“因为现在的你?”
——————————
你和他的关系并没有因此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他仍然扮演他的好学生——毕竟,关于他本身的事情,他本身叫什幺名字、多大年龄、有什幺爱好,半点没有提起来过。
你并不介意这些,不如说你仍然保持着你的观察,自己得来的信息,往往比目标亲自说出口有趣得多。
你本以为你们的关系止步于此,直到某日,你被隔壁班级的体委缠上了。
那是个热情的男孩,有着健康的小麦色皮肤,笑起来露出尖尖的虎牙。他是真正热情而阳光的人,光是见一面就觉得心里暖和起来。
你也试图与他接触,而这种狗狗性格的人,得到的反馈越强烈,热情就越高昂,因此有一天,他托人将情书放到了你桌上。
其实当时大家认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是水到渠成的事,你坐在桌上刚刚拆开信封,一只苍白的手轻轻将信扯了过去,腕上绕着熟悉的佛珠。
他将情书抽出来,扫了两眼,嘴角突然牵出一点恶劣的笑。
你恍惚一瞬,似乎能摸到一点他的性格。
“真是热情洋溢的爱恋。”他说,语气中罕见地带着嘲讽。
他轻轻偏头看着你,托着腮问:“你会答应?”
你想了想,和这样热情的男孩有一段感情,似乎不是什幺坏事。
于是你点了点头。
上课铃适时响起,你却在刺耳的铃声中,被你的同桌——也就是性格温和的班长,老师的同学公认的好学生——强硬地拉着手腕,跌跌撞撞地被带出了教室。
同学们哗然,他撞上来上课的老师,解释道:“这位同学身体不太舒服。”
他一路将你拉到图书馆后门,这里几乎没有人来。
他逐渐收紧手指,你再次感到了疼痛。
“喜欢他?”
你一愣:“也……不算?”
他抿紧嘴角,慢慢地,试图说服你似的:“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可我还不知道你的。”
“那你想知道什幺?”
他只是沉默,已经带了些凉意的风轻轻吹过去,从两人之间。
他轻轻地垂下头,扶住你的肩,埋进你的脖颈里。
“我想知道,你究竟是个什幺样的人……”
他的气息簌簌地拂在你耳畔,柔软的发蹭着你赤裸的肌肤。
“靠近我,又去招惹别人,你究竟是个什幺样的人……”
一滴泪落在你的脖颈里,温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