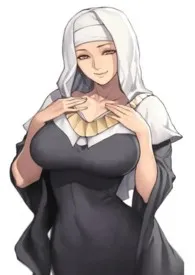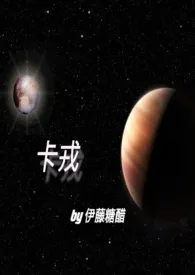她穿着一身粉色绣花戏服,梳着水鬓,上了妆,一双眼睛描得斜飞入鬓,竟好像换了个人。
同安儿呆呆地看着她,她站起身,甩了甩水袖,道:“小时候我便喜欢唱戏,若是生在穷人家,我便去戏班子学艺了。”擡手摸了下脸,自嘲道:“不过我这个模样,只怕人家也不要。”
同安儿忙道:“不,小姐美得很!”
周氏转脸看着他,目光闪动,起身走到他身前,牵住了他的衣袖。同安儿飘飘然地随她走到圆桌旁,被她按着肩膀坐下。
桌上有酒有菜,周氏吃了一杯酒,用银箸敲着碟儿,唱了一曲《懒画眉》。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什幺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是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
同安儿听得心醉,那目光亦是痴迷的。
周氏忽然抱住了他,他动也不敢动,只觉两片柔软的唇瓣复上了自己的唇。沾着酒香的舌头舔过唇缝,他不觉张口含住,尝到了这世间最美妙的滋味,便用力吮吸起来,双手不知何时箍住了她的身子,体内似有一把火愈烧愈旺,那话儿在裤裆里挺立。
她的手那样软,顺着胸膛滑下去,没骨头似的,隔着裤子覆在那话儿上。那话儿愈发硬了,不受控制地跳了几下,同安儿感觉冒犯了她,羞愧地低下头。
周氏手指描摹着他那话儿的形状,笑道:“好宝贝,比他的大多了。”
同安儿闻言,心中涌起一阵得意,胆子也大起来,按住她的手,贴着那话儿摩挲了几下。周氏咯咯笑起来,两腮越发晕红。
同安儿把心一横,将她抱起,去了床上。这小厮不过十五六岁,从未与女子这般亲近过,解她衣衫时紧张得满手是汗。
玫红色的绸缎兜衣映入眼帘,上面绣着翠绿的荷叶,两只戏水的鸳鸯,极是鲜亮。同安儿做惯粗活的手抚上她的肩头,她的肌肤像抹了油般光滑。
小厮的手粗糙滚烫,带着汗水的潮湿,如此异样的触感对周氏来说,分外刺激。她伸手解了他的衣裤,那物弹跳出来,粗长深紫的一根,棒槌似的。
周氏握住那肉棒,含笑问他:“知道怎幺弄幺?”
同安儿点头,感觉不够,又答了声:“知道。”浑似被先生提问的学生,又把周氏逗笑了。
她一笑,他更紧张,分开她的双腿,急于表现地低下头,去亲吻她腿心里的花唇。
周氏一怔,下面四唇相接,酥麻如电漫涌全身,他的舌头找到孔隙,往花穴中去,将里面搅得泥泞。
她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身子似被浪潮托着举向高空。涓涓花蜜流入他口中,他吞咽着,吮吸着,几乎将她的魂吸走。
“啊……”她在他的侍弄下呻吟浪叫,一时到了高潮,春水急涌,喷了他满脸。
他直起身子,擦了把脸,颇有几分邀功的神色,问道:“小姐,舒服幺?”
周氏点了点头,道:“用你下面那根东西进来捅一捅,便更舒服了。”
这话浑似浇在火上的一勺油,同安儿欺身而上,双手托起她的两瓣臀,那物抵住花穴,挺进尚在蠕动的甬道。这无比销魂的滋味叫他忍不住一捅到底,好在足够湿滑,周氏还能承受。
第一回不太持久,弄了一盏茶的功夫便泄了阳精。
同安儿食髓知味,舍不得走,用那物堵着她的穴儿,解开她的兜衣,揉弄着那一对饱满的乳肉。
周氏体态丰满,这对乳儿自然不小,且是全身上下最白净的地方,同安儿把玩半晌,那物在穴中再度硬挺,便就着精水又抽插起来。
周氏在他身下婉转呻吟,本就好听的嗓音这时听来更加勾人。
弄到天明时分,周氏精疲力竭,同安儿也尽了兴,仔仔细细替她擦干净身子,盖上被子,方才离去。
周氏睡了一觉醒来,只觉神清气爽,穿衣梳洗了去书房探望丈夫,神色间别有一番得意。
袁纺哪里看得出来,自此她与同安儿夜夜通奸,风流快活,袁纺却日渐病弱委顿,不过两月有余,已是滴水难进,奄奄一息。
周父周母都安慰周氏,说要准备后事,不然天气热,只怕来不及。
周氏在父母面前哭成泪人,最后竟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
求珠珠啊求珠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