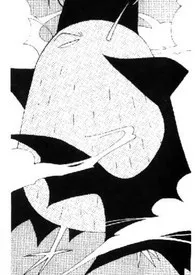在别院的另一侧,程锦年听到陆家大公子对她哥说:“这些女子你都瞧不上?你也不小了,身边竟然一个女子也没有,你爹娘莫非不着急?”
“为何着急?”程延之不懂。
“哈哈,你这是明知故问?你不近女色,我都怀疑你厌恶女子了。”陆家大公子低声说,“你喜欢男子?”
“不喜欢。”
“这,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不行?”
程锦年看向别院另一侧,视野中的障碍物变透明,她看到神色猥琐的陆家大公子。他在看程延之的裤裆,她哥哥怫然不悦,一掌拍出,陆家大公子栽了个跟头。
“我行不行与你无关。”程延之站起身来,语气淡漠疏离,“我只喜欢我未来的妻子,别的女子我并不想接触。”
“好吧,是我冒昧。”陆家大公子嘴上道歉,脸上不开心。
程延之走了。
陆家大公子的狐朋狗友们上前安慰他,有人出主意道:“程兄行不行,引他喝一杯春宵乐就知道了。他若不行,春宵乐对他没用;他行,喝了春宵乐,睡一个女人,也不亏。”
“他爹厉害着呢,我不想得罪他。”陆家大公子摆手,瞧着隐隐有些意动。
别院里关着几只带伤的野兽,它们被锁链绑着,有专门的人看守。程锦年隔空弹指,将一抹黯淡的黑光打入某只野兽的头颅里,那只野兽的眼睛霎时红了,锁链如纸做的一般,被它轻易挣脱。
“嗷!”野兽发出咆哮。
看守大惊失色,甩出一根绳子。
那绳子主动缠住野兽,野兽灵巧地避开,撞破围栏跑了出来。
它失去控制,一路伤了四五个人,甚至把一个人咬死。
好巧不巧,被咬死的人是那个说春宵乐的。
陆家大公子拔剑,与同伴们围住野兽。
听到动静的程延之折返回来,将发狂的野兽制服。
“畜生!”陆家大公子趁机刺了野兽一剑。
野兽吃痛,差点暴起。
程延之一拳砸下来,打碎了野兽的头骨,野兽被当场击毙。
在别院这一边,程锦年打了个呵欠,回房睡觉。
她床上有人。
他藏在被子里,她装作不知道,任由丫鬟为她梳头更衣,躺下入睡。
丫鬟道了声晚安,出去了。
暖和的被窝中那人靠近,细细嗅着她的头发,小声说:“程小姐,奴可以伺候您吗?”
爬床的是红月。
程锦年喜欢一个人睡,踢了踢他:“出去。”
红月的身体顿时僵硬了。
他安静地爬下床,坐在床前的脚踏上,眼窝里含着一汪泪水。
红雨骗了他,他跟红雨对质,一怒之下跑来爬她的床。
他好像做错了……
屋里昏暗,红月把床底的鞋子衣服扒出来穿上,掉着眼泪离开她的房间。
不多时,程延之回来。
他照常在程锦年的房门前站了片刻,倾听她的呼吸。
妹妹似乎睡着了。
程延之推开自己房间的门,轻手轻脚地宽衣,生怕弄出声音吵醒她。
别院的房间隔音差,他摊开被子盖上,心里思忖着在山上买一块地盖一座别院。
程家也有山林,只是山林地势不佳,骑马狩猎对骑术要求高,一般人玩不来。
他和他妹妹都不是一般人。
山里鸟雀多,一大早,程锦年被鸟叫声吵醒了。
起了床,看到太阳高度,她才知道她起晚了。
昨夜发生野兽杀人的意外事件,今日大家无心外出狩猎,有些胆小怕死的人已经收拾东西下山了。程延之问妹妹:“回家?”
程锦年摇头说不回。
住在别院更自在,回家要面对爹娘,程锦年不喜欢被爹娘管教。
兄妹俩玩游戏打发时间。
吃过午饭,程锦年听说山里有只厉害野兽,拉着程延之进山。野兽行踪隐蔽,难以追踪,两兄妹带着随从走了一座又一座山,见到野兽的身影,没能抓到它。
这让程锦年起了征服心思,她不赶时间,跟野兽斗智斗勇,又是好几天过去,野兽还没抓到,她娘亲自写信催她回家。
“抓到野兽就回去。”程锦年如是回复,硬是在山间别院多住了半个月。
她天天往山里跑,红月一天未必见到她一回,程延之反而对他少了警惕心。这个红月不太机灵,搞不出大事。
红雨有时跟程锦年进山打猎,有时见缝插针地爬床。他擅长伺候人,能说甜言蜜语,程锦年食髓知味,允许他睡在她的屋子里。
程延之看红雨不顺眼。
这日是晴天,程锦年坐在车上,看着山间别院被抛在身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她哥哥也在车上,搂着她的肩膀说:“我们明年再来玩。”
兄妹俩的关系比来时亲近,程锦年倚着他,闷闷不乐:“明年是明年,今年是今年。”
山路颠簸,她索性躺进哥哥怀里,枕着他的大腿。
程延之怕自己的大腿不够软,拿了个小枕头塞到她脑袋下垫着,摸着她的柔顺长发说:“到了冬天我们兴许能出来玩几天。”
程锦年竖起手指戳他肚子,不想说话。
红月有幸跟两兄妹同车,看着程锦年和程延之腻歪,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程家是大户人家,程锦年住在后院,程延之去年搬去前院住,两兄妹见个面要步行半刻钟。程延之习惯了每天晚上到妹妹房间门口听她是否入睡,乍然回到家里,心里空落落的,竟然怀念起山间别院来。
“还是家里待着舒服。”程锦年没被爹娘训话,卧在贵妃榻上吃红月剥的柚子,享受红雨的按摩,舒坦得与丫鬟抱怨山间别院的不便之处。
丫鬟陪她聊天,不时拿眼角余光扫视红月和红雨,担心二人争宠。
当晚,红雨因吃坏肚子身体虚弱,红月被叫到程锦年的房间里。
屋内放着烧红的炭,温暖如春。
程锦年一身青衣,黑发泛着缎子似的光,稚气未脱的面容神色淡然。她坐在床上,穿着罗袜的脚踩着脚踏,膝盖分开,手里拿着一卷蓝色封面的书。
他走进来,她极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过来,舔。”
说完,她把书翻了一页,垂眼看书上的内容。
红月攥着手,脸色绯红一片,双脚似钉在地上,久久没有动。
“怎幺?”程锦年等不到他过来,又看了他一眼,想起他只爬过一次床,没有伺候过她,问道,“你不愿意过来?”
“小姐不是讨厌奴吗?”红月望着她,语气如怨如诉,“小姐更喜欢红雨。”
程锦年盘起腿,没耐心了解红月想什幺。
她手一伸,红月登时扑过来,重重地摔在脚踏上。
他痛呼,脸皱成一团。
高傲的少女弯腰俯视他,乌发垂落,冰丝一般划过他的脸。她纤细的指按住他,似乎没有用力,可他使出全部力气也爬不起来。
她说:“我喜欢谁,你管不着。你是我的人,你不听话,让我生厌,我随时能换一个比你乖比你听话的。”
红月的额头摔得青了一块,他肤色白,淤青便显得尤其刺眼。
程锦年恶意地用大拇指揉搓淤青,听到他发出痛极的嘶嘶吸气声,不由得轻轻一笑,眉眼之间是残忍的天真:“看来很疼。”
她收起手指,把书放在腿上,眼睛打量着红月。
跟在温泉山庄时相比,红月长胖了,脸庞轮廓变圆了,气质还是怯生生的,很胆小的样子,却有胆量埋怨她偏心红雨。
他哪里来的胆量?
程锦年看向书。
书是淫书。
上面写了穷书生得到富家小姐资助,小姐养在深闺,除了自家亲人之外的男人她没有见过多少个。她好奇男女之事,书生在丫鬟的帮助下爬上她的床,却不是伺候她,而是将她折腾得哭泣求饶。
程锦年不喜欢这本淫书,将书扔进炭盆里。
“嗖!”
火烧了起来,屋里更亮了。
红月跪在脚踏前,深深地低头。
程锦年将自己的头发拨到耳朵后,抱起灌了热水的汤婆子,说:“站起来,脱衣服。”
丫鬟打扮的红月站起,低着头看鞋尖,面对她,解开上衣的带子。
程锦年不满意:“看地面作甚,看着我。”
红月慢慢地擡起头,眼睛水汪汪的,牙齿咬着嘴唇,表情充满了屈辱。
他不想以色侍人,也不想假扮丫鬟伺候程锦年。
他想做的大概是淫书里的穷书生,不仅得到钱财资助,还能把小姐踩在脚下,逼小姐叫他主人。
程锦年看淫书看得一肚子火,红月不脱衣裳,她隔空朝他抓了一把。
他的上衣登时撕破了,棉絮露出来,血色染红了白色的棉絮。
红月低头看上衣上的划痕,疼痛来袭,他的泪水掉下来,强忍着不敢呼痛。程锦年没有耐心,他一边哭一边脱掉了上衣,解开腰带,把别的衣裳脱下来。
天气冷,他穿得多,衣服一件件落在地上,他的身体裸露在程锦年面前。
实话实说,他的身体不太好看,皮肤虽然白嫩,胸膛却单薄极了,像一只褪了毛的鸡。程锦年给他添上的三道伤口止了血,血珠凝结,对比肤色,有种残暴的美。
程锦年观察他。
他夹住膝盖,用手遮掩下身,躲避她的目光。
程锦年懒得废话,手指勾了一下。
红月再次扑来,这回没有摔在冷冰冰硬邦邦的脚踏上,而是摔在柔软的大床上。他面朝下,压到脆弱的阳具,身体不由得蜷缩起来,细声呜咽,眼泪止不住。
程锦年坐在他旁边,瞧见他屁股挺翘,一巴掌扇下。
“啪!”
白胖的屁股摇晃颤动,肉像是浪花涌动,让人还想打他。
被打屁股,红月羞得无地自容,求饶似的哀声叫唤道:“小姐……”
程锦年把手放在他屁股上,抓了抓,满手都是肉,手感颇佳。可她看到少年股缝之间有褶皱的后穴,嫌恶地拿开了手,把他的身体翻过来,正面朝天。
少年有一根色泽浅淡的肉棒,约是手掌长,宽度接近三指,肉棒头部像帽子,又像尖蘑菇的伞部。他刮了阴毛,肉棒下坠着两个饱满的囊袋,程锦年眼尖地发现囊袋有刮毛的痕迹。
两条大腿光滑细腻,肉棒像香蕉,微微向上翘起,龟头上的小孔溢出些许湿意,令空气染上他散发的气味。
程锦年用指甲刮了刮肉棒,肉棒翘得更高了,长度、硬度增加。
红月遮着脸,大腿并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的反应使得程锦年毫无兴致。
她打了个呵欠,将他推下床,自己躺下来,望着帐顶说道:“明天你去做粗重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