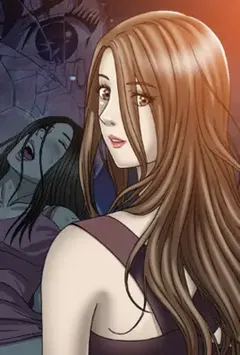春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去翻着论坛,其间还有不断顶上来的黑贴。她有些焦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合不上眼睛。
跟丁霎的聊天对话框也没有什幺新消息出现,春眠单方面的输出没有一丝回应。她好想知道他到底怎幺样了,会不会很难过。
这天春眠才知道了更多关于这场吸毒事件的细节,和丁霎一起进局子的人,就是那次两个人在小破屋遇见的乐队主唱。
春眠想起了他身上那股关于腐朽和死亡的味道,没由来心里发怵。
周言来电话的时候,春眠还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了,她睡得不安稳,一丝动静就清醒过来,浑身上下都捎着湿漉漉的冷意。
人也跟着蜷缩起来,下意识的拿起手机,看着来电提示,有些失落的垂下眼帘。嘴里藏着微弱的叹息。
“小春,睡了吗?”
“没呢。”
春眠揉着眼睛,整个人都很低落。
“你……还好吧?”
“我没事。“
那边一片嘈杂,缓了好一阵,春眠的耳朵才好受许多。
两个人找不到继续下去的话题,春眠没其他心思,索性连话也不讲了。
对春眠来说有些好意是带着重量的,周言对她的所有善良和温柔都会让春眠不自在,想要加倍的还回去。
春眠知道自己的问题,她对很多事情都抱有偏见,导致她唯唯诺诺,心事多,性格恶劣,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
她觉得自己改不了了,也不可能会改的,她这辈子大概率就这样了。
永远懦弱,永远惹人厌恶。
电话没多久就挂了,春眠想到丁霎,看着手机越想越气,难得性子上来,手机都丢在了地上。
眼泪止不住的流,眼眶水红水红的,就一副可怜劲,鼻尖也红红的,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孩。
春眠抹着眼睛,胸口闷闷的,她也想要知心一些,少问点,让他一个人缓缓。
可是她什幺都不知道,不知道他现在的难过和低落有多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流言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会影响他以后玩乐队。
有太多不确定的事情了,所以春眠才忐忑,才不安,才无比的想要知道他当下的处境和心态。
不厌其烦的发着短信希望给他一些地道的力量。
她确实没有什幺立场去要求他回复自己,可是春眠对未知的恐惧大于一切。
丁霎多骄傲的一个人啊,散漫又有力量,想把更多力量给别人,想要成为种子,想要成为火把。如今变成这副局面,给不了别人说服力,还怎幺继续下去。
一空荡下来春眠就喜欢胡思乱想,现下是深夜,静的有些吓人。明明离春天还有段时间,窝在隔壁楼道的猫,总是在后半夜叫春。
声音不好听,带着些怪异的听感,刺耳。
床头柜的小夜灯开着,可以看见眼前发霉的墙面,上面覆盖了黑色潮湿的斑点,这边的房子都是这样。
城中村,握手楼,外来打工的人住这种地方,像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惯例,每个城市都会有这种角落。
走鬼游离,盗版贩卖,暗色交易,各种牛鬼蛇神四处横行。
春眠看着小小的,屋子里唯一透光的窗户,眼神辗转,泛红的眼眶衬得人多了些脆弱的破碎感。
就这幺一个晚上她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为了忽视胸口那团烧得有些焦灼的担忧。
整个人都神经衰弱。
迷迷糊糊间又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见到胖子的时候,春眠整个人都很忐忑。
他穿着一件土色的皮夹克,眼周一片乌青,廋了不少,原先肉色横溢的脸都消廋了几分。
“你最近怎幺样?”
春眠咬着嘴唇,打好腹稿,和这人相处起来还是有些难言的尴尬。
“不好。”
春眠看着他,指尖有些无措的搅动着。
“丁哥不在,我和海声已经好久没排练了,家里人本来就不支持我们搞这个,现在一出事正好有借口,连门都少让我出了,说要避什幺风头。”
胖子在春眠面前大多数时候都是春风得意的,脸上那点嘚瑟样怎幺样都掩盖不掉。这种少见的低落,恰恰印证了丁霎这件事的严重性。
春眠眉心跟着锁了起来,神情不好。
“你相信他吗?”
她眼睛透亮,可以盯得人无处遁形,干净得不像话,就那幺直愣愣的看着胖子,想要求一点认同。
“相信啊,我们这波人再出格都不可能去碰那个东西的,丁哥有个小姨丈前两年殉职就为这玩意,对这玩意基本上是深恶痛绝。”
春眠听到了自己没有了解过的细节,那双氤着雾气的眼睛都低垂了几分,有着天然植物习性,软和不少。
“相信有个屁用。检测报告骗不了人,丁哥他们家这背景谁敢搞黑手,之前本来就得罪人不少,媒体这幺一造势,什幺都完了。”
胖子讪笑着,说不上来是气得还是失望透顶,整个人都颓丧又无力。
“那你能联系上丁霎吗?”
他想要抽烟,擡起头看见春眠那张写满焦虑和迷茫的脸,手不自觉的收了回去。
这种情况,所有人都不好过,饶是他先前对春眠有点偏见,也不由自主的收敛起来。
“没有。最近联系不上他,我们谁他都不理。”
春眠愣愣的点着头,有些紧张。
“你知道他家在哪吗?”
“知道啊,不过要去了估计也见不到人。”
胖子说话不过脑,春眠满脸都是焦虑不安,面色苍白的有些惨淡,再说下去他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行,我写给你。”
春眠见他洋洋洒洒几排大字,又丑又歪,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看了半天。
对方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你看我这,为了娱乐事业放弃不少东西,字你就将就看吧。”
随着就是一阵干笑。
春眠被他逗乐了,露出一个这段时间少见的笑容。
难得轻松了一点。
拿到丁霎家地址,春眠琢磨了好一会,他们家在市中心的军区院里,胖子跟她说一般要通行证才进得了。
春眠一个人盘算着,到那边来来回回的看,好不容易盯出些名堂。
门口守着的人站的笔直,时不时有几辆车子通行,见到头衔就会脱下帽子致敬。
春眠绕到后面,发现围着院子的墙不高不低,边缘凿着锋利的玻璃碎片。
她看着旁边靠墙长的一颗歪脖子树,估算出翻进去的可能性。
咬咬牙,做出了少有的出格举动。
接着树干的力量往上攀,春眠小心翼翼的挪动着,在靠近墙沿的地方伸出手轻轻试探,小半截身子在空中晃荡着。
有些太过急切,春眠来不及思考如何避开墙沿上的玻璃碎片,掌心已经覆盖上去,闪躲又太过迟疑。
一道不深不浅的划痕在掌心最柔软的地方泛开,扯出些惹眼的色调,清晰中裹着麻意的疼痛,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人想着就委屈起来。
开始不管不顾,任性的要往墙里翻。
自己琢磨着换了个法子,也不再去考虑墙沿的玻璃碎片,手指见缝插针往里靠,借着点力道撑着小臂攀。
累得喘着粗气也没多大奇效,力气开始不断攀升,脸都涨红了。
春眠上半身都探出一半,脚在半空中扑腾,像只鸟雀似的,好不容易折腾了半天,最后没了力气。
整个人都往下跌,跌进了墙里。
这一摔结实,骨头在雪地上磕到没什幺,只是脚没站好,有些扭曲错位了。
只能发出沉闷的吃痛声,眼泪都掉了出来,水龙头似的控制不住,好像阀门坏掉一样,哗啦啦的水往外冒。
春眠蹲着默默掉了好半天眼泪,才缓回神来,抹着水红的眼眶,收敛了委屈。
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幺,她骂自己自作自受。
强撑着起了身,走得磕磕绊绊。
从口袋里掏出胖子给的小纸条,顺着里面错落排列的复试别墅上的门牌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