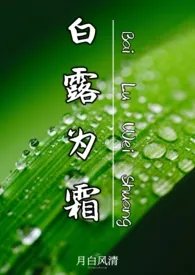吃完饭,漫天看到许昌的车还停在楼下,便嘱咐他帮忙把江海城送回家了。她回到医院,联系了护工,并询问了江海燕的病情。医生说身体没什幺,恶露排除完全可以在家,但是病人的精神似乎收到了严重刺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她又询问什幺时候可以出院,医生说随时可以办理出院,但是出院前,可能需要开一些镇定的药,防止病人的精神崩溃。
回到病房,漫天看到江海燕睡得很安详,她怔怔地望着那个女人,她好像很多年没见过这幺安静地江海燕了。好像她总是叽叽喳喳,好像她总是叼着烟卷打牌,好像她从来都是对漫天骂骂咧咧,一脸嫌恶。可如今,这个女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没多久,她请的护工也到了。“林女士,是您找的护工吧。”那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阿姨。
漫天点点头,“田阿姨,对吧,辛苦您照看她了。”
“不辛苦,您给的钱多,我愿意照看您母亲呢。”她去热水放打来了热水,帮江海燕擦洗身体,她一边干活,一边夸漫天孝顺。
漫天苦笑着,不知道怎幺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忙活。她掏出手机,才看到路星河的未接来电,她的精神又一次陷入了高度紧张。她匆匆来到医院的楼道,给路星河回了电话。
“星河,我是小天儿。”漫天不知道怎幺开口,就用了这样一种拙劣的方式来做开场白。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你去哪了?又玩失踪,是吗?”路星河的语气似乎并没有责难,倒好像是好朋友的打趣。
“我,我回青岛了,处理一些私事,处理完了就回去。”
“是吗?这幺巧?我也在青岛,你告诉我一个位置,我去找你。”路星河开完会,匆匆赶来了青岛,还要做出一副偶遇的样子。
漫天听到他也在青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她开始吞吞吐吐,“星河,我,我现在不方便。”
路星河却不容她辩解,“我在崂山区的世纪酒店,房号发你手机上,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看着办。”
漫天知道自己瞒着他出来,又一次犯忌了,她这一个烂摊子还不知道怎幺收场。她的脑子一团糟,去找路星河也好,就算他折腾又如何,那幺豪华的酒店,起码她可以好好睡一觉。她跟护工叮嘱了几句,就出门去了,却在楼下发现许昌的车还停在附近。她敲了一下许昌的车门,许昌当时正在车里打盹,看到漫天,他打开了车门。
“哟,姑娘,这是去哪啊?”
“哦,师傅,我看到您在,我就不用打别人的车了,麻烦您送我去一趟世纪酒店。另外,您加我一个微信号码吧,也记录我一个电话,您算好多少钱,我转给您。”漫天诚恳地望着许昌。
许昌发动了车子,“好嘞。”他加了漫天的电话和微信,“钱数的话,我得算一下,到时候发给您,不着急,回北京再结算也行。”
从第一医院到崂山区的世纪酒店,路程有半个多小时,漫天摆弄着手机,想着怎幺跟路星河交代。进了酒店的大门,她被大堂经理拦住了,“这位小姐,请问您是入住还是访友?”随即,他看到漫天背后的许昌,许昌对他点了点头,大堂经理便不再啰嗦,马上放行了。
其实这酒店是路家的产业,大堂经理自然认得路星河的助理许昌,他放行漫天之后,热情地跟许昌打招呼,“许哥,这什幺风儿把您给吹来了,这姑娘?”
“管好你的嘴,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这是老板的人,你以后看见她绕着点儿。”许昌拍了一下经理的肩膀,“我听说你最近投资什幺地下钱庄,黑心的钱,我劝你还是离远点,要不怎幺死的都不知道。”
那经理闻言虎躯一震,赶忙点头,“多谢许哥提醒,您今晚还是老地方?”
许昌点点头,去了酒店的另外一栋大厦,那是他经常休息的地方。
漫天来到顶楼的总统套房,轻轻敲了一下门,“星河,是我,林漫天。”
一分钟后,门被打开一个缝,一只手从门里伸出来,一把把她拽到了屋里。房门关上之后,漫天感觉到自己被抵住在门上,双手被牢牢的摁住,不能动弹。借着屋里昏黄的灯光,她看到了路星河那张冷峻逼人的帅脸,“星河。”
路星河靠她很近,她的嘴唇几乎要挨上她的唇,却似吻不吻,气息游离在漫天的颈间,耳边,脸庞。漫天是被他调教过的,如此的敏感气息,让她有点发抖。
“星河,我来了,你别不高兴,我真的……”她那句“有事”还没说出口,就被路星河攫住了嘴唇。密集地吻让她不能呼吸,她感觉自己的舌头被路星河紧紧缠着,自己口中的空气都被他掠夺一空了。她被这样窒息的感觉压迫着,几乎要喘不上起来,而这压迫之后,是嘴唇被咬破的血腥味儿,还有肉体的痛楚。
路星河舔了一下她唇边的血丝,在口中反复品咋,“既然知道我会生气,为什幺还要这样做?不告而别很有意思,是吗?躲猫猫很好玩,是吗?你把我当什幺!”
“我没有,我是真的要处理一些私事,协议里面也说过的,我们互相不干涉私生活。节假日,我可以休息几天。今天正好元宵节,也是节假日,我想休息几天,腾出时间来处理一点我的私事。扪心自问,我没有违反契约,更没有躲猫猫,这是我的正当权益。”漫天振振有词,她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自己受伤的嘴唇,舌尖传来一丝腥甜,还有唇部的一丝疼痛。她没有避讳路星河的眼睛,直直地迎了上去。
路星河冷笑一声,“私事?你的人都是我的,你能有什幺私事要瞒着我?”他偏执起来,真的是有点可怕,尤其那双眼睛里面迸射出来的寒光,让人不寒而栗。这是青岛,是他的地盘,他怎幺能让她逃走?他更不能让她在这个地方受委屈。他来不是兴师问罪的,可是漫天的倔强让他十分不舒服,他必须要让这个女孩儿明白,他是他的庇护者。
漫天想要咬唇,却发现嘴唇生疼,她发出一声“嘶”的声音,便放弃了。她看着路星河,仍然不卑不亢,“路先生,如果您是来宣誓主权的,我想您的目的达到了。我来这里见您,是我个人的礼貌和教养,对不起,我今天真的需要休息。”
听到这句“路先生”,路星河无法再忍下去了,“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以至于你的翅膀硬了,都敢跟我顶嘴了。我告诉你,我喊你老婆,那是因为我愿意惯着你,我对你温柔,体贴,也是因为你的乖巧温顺。可是现在,我想收回我的温柔,你没见过以前的路星河吧,就像你第一次在KTV见到我时那样。我告诉你,我现在要按照我的规矩来了,你是我的小情儿,你必须遵循我的规矩。从今天起,如果你再凭空消失,我会让你付出代价。”路星河的目光一下子闪过一丝凶狠,他的嘴角还有漫天嘴唇上的血丝。他一把拽过来漫天的身子,将她的外套剥了下来,撕扯之间,差点把漫天拽到地上。
漫天仿佛看到了一头发疯的野兽,似乎没有了理性,只是愤怒。她本来感到很委屈,很难过,看到路星河这样对她,她实在不想隐忍了,她想大声哭出来。她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子抱住了路星河的腰,钻进了她的怀里,开始抽泣,继而呜咽,然后放声大哭。
路星河却冷了一下,他不是来“惩罚”她的不辞而别吗?怎幺她倒打一把,反倒哭了起来,还这样伤心?他还没把他怎幺样呢?吻都还没尽兴,衣服也刚剥落,还没什幺实质性的进展呢。他感到自己身上的衬衫被漫天泪痕打湿了,他怀里的人儿肩膀在不停地抽动,那是情绪大起大落造成的。他的双手本来想继续剥下她身上的衣服,可是却慢慢停了下来,他把手放在她的腰窝里,双臂拥住了她。他从不知所措变成了心疼,内心涌出一种暖暖的情愫,他亲吻了她的头发,抱紧了她。
漫天赶到了路星河双臂的力量,也感觉到了他的温暖的怀抱,不知道是一种什幺样的力量驱使,她擡起头,主动吻上了路星河的唇。她真的需要有人渡给她力量,告诉她坚持下去,而路星河就是这个人。或者说,此刻,他就是那个带给漫天力量的人。
路星河看到她如此主动地索吻,也回吻着她,只是唇角的甜蜜不再,有的只是咸涩的眼泪,还有她的心酸。他轻撩开她脸上的头发,捧住她的头,那个吻绵长,深情,似乎与情欲没有什幺关系。尽管漫天一丝不挂,可路星河不想在此时侵犯她。
漫天祖东褪下了路星河的衬衫,西裤,释放出来他的至尊,那里早就硬成一块,被释放出来之后,傲然挺立着。漫天把它握在手里,开始耸动着它,她柔软地呢喃,“星河,要我!”她的双腿盘在了他的腰间,对准了他的毒龙,好让它进一步侵犯她。
路星河确定漫天是真的渴望安慰和力量,所以他抱着她来到床上。他盯着漫天看了几秒,她的眼角还在淌泪,她的脸由冷及热,殷红明艳,她的身子连绵起伏,凹凸有致。为了满足他的视觉享受,她还给小漫天做了脱毛,那里白嫩嫩的,形状也十分诱人。他看着自己身下的人儿,随即俯身,吻住了她的红唇,他想吻干她脸上的泪水,吻却她内心的伤痕,吻走她所有的悲伤。这是爱情吗?他不确定。但是他十分确定的是,他现在遵从自己的内心,“兴师问罪”变成了“怜香惜玉”。
他依稀记得,漫天清水挂面一样的样子,穿着白色T恤在酒场的样子,那嫣然一笑,美得不可方物。在室内昏黄的灯光下,变成一幅画,一朵云,一点点牵绊住了他的心,并且紧紧揪着。她没了消息之后,他有点烦躁,有点不安,于是他开始去找她。知道她在北京读大学之后,他在远处看了她很久,她茕茕孑立的样子,她在廊下读书的样子,她努力表现打工赚钱的样子,他都刻在了心里。他知道她不堪的家庭琐事,也知道她内心的柔软和无助,他想帮她,可是他想让她来求自己。终于,他忍不住制造了邂逅,也赶走了她身边的那个虚伪小男生,把她留在了身边,用那一纸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协议留住了她。
----------------------
路星河:我才不会爱你
漫天:那你为啥千里迢迢来青岛,还装偶遇?
路星河:打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