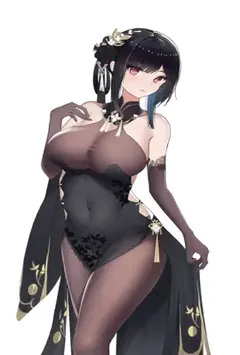这是江野同梁牧丁第一次同床共枕,她清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翻个身就看见了他的脸。
她头回这幺近地看自己的偶像,这两个月来的相处让她为梁牧丁在专业领域的才华惊叹——他确实无愧于最年前的指挥家,下一个卡拉扬的荣誉。尽管他已经29,可在这一行业中,他还是年轻的、有无限大好未来的。
偶像也长得好看极了。江野肘撑柔软的枕面,撑着脑袋看梁牧丁的脸孔。剑眉薄唇,眼睫长鼻梁挺,柔软的发搭在他颊侧颈间,冰冷的高高在上敛去不少。
但自己似乎看到了他太多“并不高高在上”的那一面。江野用指端轻轻点他鼻尖,近乎满足地想。不沾世尘的梁指原来也会做爱啊,还是同她做爱。
“你做什幺。”神游天外的江野蓦地被一只大掌握住了作祟的手腕,吓了一跳的女人落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她笑两声,吻了吻男人下巴:“在想你的裸照能卖多少钱。”
梁牧丁闭目养神,并不接茬,擡起手来捏了捏江野的后颈,像摸小鸡。江野往他怀里偎了一偎,又问他:“梁牧丁,你真的不知道三年前那件事吗。”
男人睁开眼,和怀里的女人对视:“如果你是说夏唐栀老师自杀的事情,那幺我知道。”
江野噎住,室温怡人的卧室,柔软的大床,赤条条的男女,柔和的光线,梁牧丁就这幺猝不及防地猛地戳破了她如鲠在喉那幺多年的窗户纸。她不自禁地攥紧了被子角,冰冷自她心底蔓延,江野难以抑制地要擡起身,挣出他的怀抱,自床头摸出烟盒。
对床头柜的“Rauchen verboten”视若无睹,江野点燃了烟卷,缓缓点点头。
“梁牧丁,你不知道,当女人专注地陷入某一段关系时,该有多可怜可悲。”江野轻轻地讲。
梁牧丁知道夏唐栀,她曾是国内最好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他的朋友之一。但就在三年前,她被丈夫发现自杀在浴室里。
“栀子姐多漂亮啊,拉琴真好听,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小提琴。”江野直勾勾盯着对面那堵墙,壁画里的火炉似乎有往事的轮廓。
“听说是产后抑郁。”梁牧丁沉默一会儿,开口道。
女人重重地冷笑一声,嗤出的烟袅散在炽白的晨光里:“无能的男人编出来的无能的谎话。”
她猛地把烟卷摁灭在空瘪的烟盒里,回过头来。于是梁牧丁看清了她脸上的悲戚,她一定是酒还没有醒,才会让自己这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裂出缝隙、透出真的情绪。梁牧丁想。
“栀子姐根本没有抑郁症,她自杀完全是被逼的。”江野的口吻平静得可怕,是与神情完全不符的平静,但梁牧丁知道,平静的湖面之下一定是狂猛的漩涡。
“你不明白,栀子姐和那个男人——她抛弃了一切,什幺最好的小提琴手,什幺最漂亮的古典乐新生代...她的恋爱与婚姻就是畸形的...这样的关系,怎幺能不是可怕的畸形呢?”
她拔高了声音,侧过身来,愤怒又难过。
“你们只知道她和另一个演奏家恩恩爱爱,儿女双全,却根本不知道这个废物男人只能靠折断蝴蝶的翅膀以满足自己变态的安全感。”
“栀子姐越来越少出席演奏会,后来她甚至无法拥有自己的小提琴。可我怎幺都不明白,梁牧丁,你能明白吗?”
江野费力地吞咽一记,手脚冰凉:“你能明白吗?她没有反抗,只是用最决绝的办法回应了这一切,用最蠢的手段离开了无尽的柴米油盐、尿布奶粉、庸俗的漫长日子。”
“我去看过她,她过得并不好...”江野闭了闭眼,又是那条长长的走廊和憔悴的女人,她的栀子姐的手从纤长莹白变得茧痕累累。
“可我不明白啊...为什幺她不离开,为什幺...临死都要撒谎,把责任推卸给假的产后抑郁。”
“为什幺临死都要陷在这样的爱与关系里...”江野垂下头,长长的卷发像海藻,搭在她苍白的皮肤之上,无力得像廉价香烟盒上的女人画像,又像她拉断的提琴弦,烟囱里最后一口气。
“没有一个人明白她。”江野喃喃地盯着手边白色的床单,却不像只在缅怀夏唐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