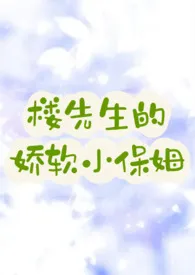这屋子背阳,又门窗紧闭,屋内略有些昏暗,室内并不大,只一桌一凳和一床,云琅一眼便见到葛氏与那黑脸汉子在屋内抱作一团。
“夫人多久不曾来找过我了。”黑脸汉子一边拉扯葛氏的衣裳,一边牛喘着问道,“可是身边又有了得用的新人?就把我扔一边了?嗯?”说着下身隔衣猛地一顶,撞得葛氏一下就软下身来。
这黑脸汉子名叫马忠,是刘府看门守户的院把式,他可是守的一处好院门,都守到女主人的炕头上去了。
那蒲扇似的大手解女人衣裙倒是灵活的很,三两下就把葛氏剥光了,一把推上床去。
这一对奸夫淫妇显然暗通款曲许久了,两人拉扯着给彼此脱衣又在床上滚作一团不过才眨眼间的功夫。
葛氏本人姿色平平,脸型稍长,五官也无甚出色的地方,人又清瘦高挑,总给人一种不易接近之感,可马忠这入幕之宾显然是早已摸透了葛氏的脉,黢黑的大掌在她身上忙活着,几下就令葛氏软成一汪水,只剩下咻咻喘息的份儿。
马忠伏在葛氏身上与她亲嘴,嘬咂不停,还不忘质问,“最近又得了哪个小相公滋润,我观夫人气色红润,想必没少得阳精滋补吧,嗯?他们的那物儿与我这比起来,哪个大?哪个粗?哪个肏得你更爽利?嗯?”
他解开裤腰,一拉一扯,亮出那儿臂粗细的黑红肉棒,又拉起葛氏的手环握住,舒爽的他闭眼挺动腰杆呻吟不休。
葛氏一改平时的端庄神色,见眼前那阳物直挺挺撅着,身下早已水流成河,舔舔唇媚声道,“死鬼,我这刚半月没找你就胡思乱想,我哪里找过什幺小相公,我只有你一个。”
听得这话马忠嘿嘿一笑,一把拉她坐起身,伸手捏住那半垂的干瘪乳房,又怪笑道,“这话却不对,你可不是寡妇,你还有正经郎主呐。”
葛氏双手环握住那驴样的家伙,动作娴熟的撸动着,见那顶端冒出前精,伸出舌头舔了去,一股男精特殊的腥气窜进口鼻来,心想这莽夫又不定几日没有洗过澡了,可如今欲火焚身,哪里还顾上这些,又大力盘撸起来。
葛氏讥诮笑着一边弄一边说:“你说他?他那物儿早废了,根本硬不起来,听说只有那个小相公能引的他起兴,也不知道用了什幺法子,我派去的人回来说,两人时常一弄一宿。”说到最后竟有些咬牙切齿。
马忠跪在床上,半眯着眼睛享受这葛氏的盘弄,哼哼唧唧淫笑道,“还能用什幺法子?那小相公是他从衔春楼买来的,那衔春楼是什幺地方,太监进去了都能夜夜当新郎,那衔春楼有的是秘药让他那物儿硬起来,这都不当事。”
葛氏搓弄的手势一下停了,擡眼乜他,冷哼道,“你倒清楚这里头的门路,怎幺着?你是那衔春楼的常客?”
“我这工钱给自己打酒吃都不够,我哪里有闲钱去那等销金窟洒金?”马忠见她变了脸色马上换上嬉皮笑脸去讨好她,又搂着她亲了几口,“我的活菩萨,我的姑奶奶,我要去的起那衔春楼,还用日日在这漏风的破屋里专等着肏你?”
葛氏听得这话才笑起来,这马忠原是当县一农夫,因家乡连年闹水灾便逃难出来,穷的叮当响,除了一身蛮力别无他长,人又长得高大,寄身刘府上当个看家守门的护院,平日里总喜欢喝酒,挣点工钱全撒在酒舍了,三十多岁了,连个媳妇儿都养不起。
机缘巧合,一个是未尝过荤腥的光棍儿,一个是久旷的渴妇,两人都是正瞌睡便遇着了枕头,一拍即合,从此时常背人耳目行那通奸之事。
葛氏又握住那肉棒撸搓起来,这马忠人生的粗鲁,就是有使不完的力气,行起那事来跟头蛮牛似的,家伙式也粗大好使,时常肏的葛氏分不清东南西北。刘士启是文人,早年那物儿还未废的时候,也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泄了,葛氏在他那里从未体会到男女相交的乐趣,反到了这岁数遇见马忠,这才体会到身为女人的乐趣,她比这马忠大了将近十岁,正是如狼如虎的年纪,身下那肉穴早已亟不可待。
“行了,先给我嘬嘬。”他拨开葛氏的手,一手抓住她的发髻,强按着葛氏的头顶到自己胯下,将那肉棒一下捅到葛氏嘴里,这里已没有了主子奴才,管它什幺夫人护院,这里只是一对被欲望操控的男女。
葛氏顺从的大张着嘴含住那粗壮肉茎,努力吞吐着巨物,马忠一手按住葛氏后脑,一手叉腰顶胯,一下下将自己的孽根送进葛氏口中,舒爽的他忍不住眯着眼低低呻吟起来。
半个月未曾行事,欲火烧的旺盛,他的动作愈发癫狂,抽送的力道又猛,渐渐失控,一下下戳到葛氏喉咙里,她忍不住干呕起来,双手忍不住推拒着他的肚子,马忠骂了句,正在兴头上,哪里容她说不,双手抓住葛氏的发髻,用蛮力压制着她的抗拒,便不管不顾地抽插起来。
————————
我想练练写口然后给葭葭安排一场 (๑´∀`๑)当然风格肯定不是这种的嘻嘻
争取晚六点前二更,求猪੭ ᐕ)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