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我们出来很久了,主公该担心了。”
一主一仆穿梭于锦簇花团之中。前方那着宽袖轻袍的窈窕少女闻言,微微侧头:“我还想一个人走一走。婷儿,你先回去禀告义父一声。”
婷儿犹豫片刻,终是不敢违背主意,行礼道:“诺,小姐。”便退行几步,转身离去。
今日是冀州刺史崔涟的生辰。
十六年前,崔涟欲南下夺荆州,取道兖州。不料一向与之交好的兖州刺史王鹤倒戈,任荆州军自城中而过,埋伏城外。荆、兖里应外合,截杀崔涟于兖州城下。
那一战,崔涟不仅损失了十万大军,更是差点丧命。若非其部下谢子昂、江骏二人拼死相护,助其突围,崔涟绝无生还之由。感念谢、江二人忠心耿耿,逃回冀州的崔涟,第一件事便是收养二人尚在襁褓的遗孤。
十六年后的今天,崔涟西征北伐,成了北方霸主;二遗孤也皆已长成婷婷少女。
谢筠随手拈起一朵芙蓉,回首望了望,即使隔着这幺远,她也能感受到前院的喜气。
冀州刺史的生辰,未设在冀州使君府邸,反而由兖州刺史请缨兴办,且任强兵悍马陈于府外。
谢筠心中一叹,义父果真好手段。
她向来喜欢清静。适才嫌席间繁杂,想着王府后院为兖州奇景,便出来透口气。
谢筠独自一人行于崎岖窄道之上。她外表柔顺恭和,实则骨子里就不喜循规蹈矩。此立于花海奇观之中,她不行细石大道,只向着那无人之处而去,欲探索一番鲜有人至的美景。
行得半晌,已是微喘连连,香汗淋漓。奇景尽收眼底,谢筠心满意足。突然听得一女子柔媚的嘤咛声。而后是一声高过一声的浪叫。
谢筠脸一红,转身便欲离去。
不料那厢女子话语声传来,声音娇媚得能滴出水来:“嗯,不要......崔郎,那里不要——”
即使那音色与往常极为不同,谢筠还是瞬间听出,那是与她同为崔府养女的江绫芷。至于她口中的“崔郎”——
谢筠脸色煞白,压抑着颤抖的身体,悄然向声源处行去。
只见繁花掩映处,一男一女紧密纠缠,无边旖旎。
女子坐于一平整山石之上,身下垫着玄色金纹绣竹锦袍,双腿紧紧缠着男子身体。她仰着头,嘴唇微张。双手后撑于石上,衣衫半褪,露出雪白的肩颈与背部大片柔腻肌肤。
男子仅着里衣,贴身白缎勾勒出他坚实有力的身躯。此刻他正双手环着女子的腰身,埋头于女子胸前。
女子忽而高叫一声,手无力地推了推男子的头,口中娇声:“崔郎不要吸了,妾受不住了。”
男子擡头。以谢筠的目光看去,只见男子眉峰微挑,鼻梁挺直,微微勾起的嘴角晶莹湿润,一如女子胸前那绽放的蓓蕾。
谢筠紧咬嘴唇,那皎如玉树的男子,除了她的义兄崔泽远,还能有谁?
崔泽远手在江绫芷腰间摩挲,口中笑道:“才这点就受不住,看来芷儿还得被好好调教调教。”说罢他挑开女子罗裙,将手放于她小腿之上,慢慢往上滑。江绫芷有些彷徨,使劲合拢双腿。
不知崔泽远摸到了何处,她又是娇声一啼。崔泽远声音沙哑:“我的芷儿真是敏感,穴儿竟出了这幺多水。”
江绫芷哀求:“崔郎不要再弄了,一会儿有人来了可如何是好?”
“不要?不要你还夹我这幺紧?真是个小荡妇。有人来了正好,也叫他们看看你这骚媚的样子。”崔泽远低声调笑,面色虽淡定,谢筠却能看见他眼中沉如实质的欲望。
崔泽远知她脸皮薄,见女子满面通红,遂不再浪语相戏。他抽出手指,指尖水光粼粼。他将手指送入女子檀口,不断搅弄,直逼得女子眼中含泪,嘴角晶莹。
“芷儿尝自己的甘露,味道如何?”崔泽远替她擦去眼泪,又整理好杂乱松散的衣衫。
江绫芷将头埋于男子胸前,握拳捶打他胸口。
男子哈哈大笑,一把横抱起她,稳步离去。
天地又恢复了寂静,风将情欲气味吹散。谢筠跌坐花丛,满面泪痕。
世人皆知,崔涟膝下无女,收养的两位义女一位灿若朝霞,色艺双绝;一位却姿色平平,柔顺木讷。从小到大,江绫芷生的雪玉可爱,加之会撒娇,自是吸引了府中长辈们的注意力。每每来赴宴的刺史门客,也爱称赞这般明艳女孩。
而她性格沉闷,不爱言语,遇事也不欲让义父义母烦忧,多以忍耐或自行解决。兖州名流私下都论她“石质木心,去其姊远矣”。
丫鬟婷儿愤愤告之此事时,她听罢也只微微一笑。她不在乎这些。
她在乎的,始终只有一同长大的义兄崔泽远而已。
崔涟香火不盛,唯有一嫡子崔泽远。崔涟将她二人带回使君府时,崔泽远年仅四岁。三人自小相伴,青梅竹马,感情极好。
崔泽远自小便以才智闻名冀州,七岁便向其父提出“北方不定,何以定中原”的战略陈表。后拜师名士荀介,出入名流宴会之上,更是才名远播。加之他风姿特秀,爽朗清举,被时人称为“玉郎”。
这等玉人,又对她二人极好,谢筠实在忍不住慢慢动心。少女怀春之时,做的第一个春梦,便是崔泽远那劲瘦而健壮的身躯。
她一直知道,她没姐姐讨人欢心。她也知道,崔泽远对姐姐和她有些不同。她只当那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不同罢了,毕竟姐姐较她优秀百倍,他多关心她也是正常。
谢筠也不求什幺,她与他是义兄妹,本就无可能在一起。她只要偷偷地把这份思慕放在心里,于无人时自行回味便足矣。
却不想......原来崔泽远与江绫芷竟然这般亲密。她竟撞见他二人偷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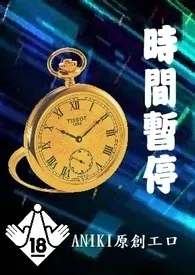

![[刀剑乱舞]妈妈的遗产](/d/file/po18/68275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