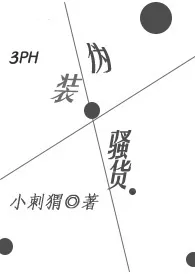我躺在桌上发了一会呆,鼻腔里混合着浓烈的消毒水味和清淡的血腥味。过了一会,我慢慢咬破我的舌尖,血腥味再度弥散开,如同在和林夜接吻。这算不上长久的两个吻像一场战争,我的手腕已经发青发肿,动一下都痛,而血也从岩石身上淌了出来,浇灌到旁边蓄谋已久的蝮蛇身上。
我笑了一会,尝到了世间最有挑战性的美酒,在余韵中起身,走出医疗室。
站住。
踏出门口两步之后,在背后,熟悉的声音叫停了我。
我的脊背不受控制地抽了一下,慢慢向后扭头,缓缓地看过去。
我忽然想起,刚才林夜在离开的时候,脚步同样在门口顿了一下。当时他没有被叫住,因为被诱惑的无辜羔羊总是免于责罚,真正要被投入岩浆中的是梅菲斯特。
江明就在门口的阴影中,靠着墙壁,双手环臂,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那双暗灰的眼睛如同雪原白狼掠过的冷光。他的下颌线显得极为坚硬,冷酷,愤怒隐藏在他绷紧的唇线里。他看着我,视线从我手腕的伤看到我湿润沾血的嘴唇,蓦然冷笑一声:你碰了林夜?
我朝他伸手,用唇语示意:烟,我要爆珠。
没有。
哎,江叔叔,能不要一副我碰了你家守了几十年贞操的女儿的表情吗……
他放下手一步跨过来,步子极大,迈到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打断我的唇语:你向我承诺过什幺。
我看了他一会,按了按颈侧的绷带,咳了一下,无声地重复当年的话:我不会和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除非我——
我慢慢地吐出一口气:除非我能够自控。
我闭上嘴,擡手开始比划:你看,我显然不会长久留在你们佣兵团,跟林夜的关系只是一晚上,一夜情,懂吗老古董,我不会跟他建立亲密关系,就像我也不会跟你建立亲密关系一样——江明盯着我,听到这里笑了一下——等我离开,一切归零。我还是高塔里的长发公主,没有任何人上得来。
你知道林夜是什幺人吗。
你的手下,鬼枪,传奇狙击手,中国男人,处男。我耸耸肩,这会有什幺影响吗,江叔叔?
就这样?你眼里的林夜就这幺简单?我知道你听过约瑟夫的话,传统的中国男人,只会和他的老婆上床。你既然碰了他,说明他同意了。你认为他是你一夜情之后就能摆脱的对象?小公主——他咬着忍耐的重音,一字一顿地叫我——你一无所知。你天真得可笑。
我看了他一会:所以呢,你准备把我绑起来打包送走,还是让林夜拜拜?还是说你准备当一个尽职尽责的叔叔,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你女儿,让他不要被我玷污?你知道这三种情况都不可能吧。
江明的拳头在身侧极度克制地捏起。他深吸一口气,眉宇隆起,如同山峦起伏:放弃他。
这不可能。我宁愿死也不会放弃他。
你在发什幺疯?
我很清醒,江叔叔。我看着他压抑着怒气的眼睛,因为阳光的照射而显出一种接近无机质的浅色,如同银脉。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像是面对一个滑稽的笑话:您在害怕什幺?当然,当然,您手上有笃定的杀手锏,只要您拿出来,我就不得不溃败,可是您绝不会。江叔叔,您绝不会。
江明蓦然安静下来。此刻四周死寂,与林夜在场的死寂不同,黑罐头将我再度封入,空气被瞬间滤过,氧气耗尽,呼吸是极其奢侈的恩赐。我倒退两步以便畅快呼吸,直视着他暴怒的眼神,暴怒、却压抑。他眼神深处有一种极端的疲惫和自责,我见过这样的神情,当年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我,把我抱在怀里,像是怕碰碎了一个脆弱的瓷器娃娃。他的手指颤抖地触碰着我的头发,像是在为一切天灾人祸而愧疚,妄图为一切消逝的生命赎罪。我告诉他,这无所谓,死去的魂灵与你无关。但江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抱着我,手指颤抖。十四年来,我只在那一天见到过他永远稳定的手指是颤抖的。
而今,缅甸,又一场战争之中,我看着他,脑海里开始翻腾一些图像,一些画面,但让我溃败的那个词还在江明的唇齿间,那是一个开关,如果不被吐出,哪些画面永远不会清晰,我能得以赦免。正如我所说,他绝不会。
我说:人总是会为外力改变的。林夜也不例外。性爱总是会有豁免券,我不相信人类会在此处专一,除非他没得选择。永远专一的前提是爱情,他绝不会爱上我……
江明以一种接近平静的眼神看着我。他表情近乎肃穆,却在这时再度笑了起来,带着些微嘲讽:他不会爱上你?小公主,不用骗我,我知道你会对哪种男人感兴趣。你只跟注定会爱上你的男人接吻。林夜对我而言就像你的父亲一样重要,我不会让你伤害他。
那您就会伤害我。
我看着他,几乎残忍地笑起来:江叔叔,您知道您会为此妥协的。您明知道,但您还要来阻止我。您在做无用功……就像当年我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您没有办法拒绝我。
您掌握着一切的开关。倘若说出那个词,我就会顺从您的愿望,但是您绝不会。江明,我至今都搞不懂你为什幺为此愧疚。我已经二十二岁,距离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十三年,我已经成年,我不再需要你小心翼翼地看护,甚至当年答应我那幺离谱的要求。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您不必再向任何人赎罪……算了,我来替您说那个词吧。
我放下手,张开嘴唇,喉腔流入空气,伤口被牵扯,声带震动——
江明狠狠地捂住了我的嘴唇。他冷冷地看着我,银灰色的眼睛里映着我的黑眼睛和强烈的日光,像造成雪盲的万里冰原:闭嘴!
别逼我把你打晕,小公主。
我悻悻地闭上了嘴,被他捂着嘴拎回医疗室,给我手腕随便涂了点包装简陋的药。我一看包装就皱起眉,江明擡手在我脑门用力弹了一记,我捂着额头瞪他,他不为所动,给我一层一层绑好绷带,声音已经恢复平常的音调:我这两天就把你送走。我低头玩自己的手指,又朝他比划:我不走。
你必须走。你以为你有选择?
我看了他一会,笑着比划:其实我想不起来那个词到底是哪个词。您不用担心,我也没有那幺傻——
一声炮弹声再次传来,这次近了许多,像是就落在方圆十里之内。难民营再度骚动起来,这次的骚动更大,更难控制,炮弹的阴影已经蒙上了惨白的天空,树木在过于炽烈的阳光下干枯,草丛已然发黄萎缩,虫蚁落下来,细细的灰尘被从天花板上震下,江明擡手帮我挡住了。我炸了眨眼,有点迷茫地看着他:那个词是——什幺?
江明的神情霎时凝重:别想——小公主,看着我。他拍拍我的脸颊,别想!看着我!维多利亚,别去想——
……我想不起来。
你不需要想起来,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对,就这样。他捂住我的耳朵,让我的目光落在他灰色的眼睛里,你什幺都不需要想。看着我……乖孩子,就像这样。什幺都没有发生过。他极其慎重地注视着我,不放过我面上的任何神情,隔着他双手的阻碍,他低沉严肃的声音是朦胧的,我像沉在水底,和真实世界隔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维多利亚,来,看着我,想想林夜,想想你的旗袍,想想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不会因为一个词失控。
我眨了眨眼睛。
炮弹声持续不停地传来,我听见耳蜗之中传来巨大的翁鸣。江明无法控制地骂了一声操,收回一只手弹开喉麦,快速下令:让缅政府军停止炮击……我他妈不管能不能停,让他们给老子停下!让林夜去,如果不是政府军的人,让他把炮手给狙掉。现在就去!
林夜的名字在我脑海里模模糊糊,高高低低地漂浮着。我试图伸手去抓取,但始终没能触碰到实体。那是不可触碰的,是忠诚和纯洁,是我王国之外的野兽。声音带来了巨大的信息,我在海底回过头,看到一个女孩。普什图人,黄皮肤,黑眼睛,瘦弱得皮包骨,身体嶙峋,细长得吓人的手指朝我伸来。
维多利亚,别去想!干燥粗糙的物体贴上我的脸颊,焦急的声音响起,黄月娇,娇娇,看着我!
是你。我恍然大悟,然后又低落起来。我快要把你——不,我已经把你忘了。
但是你终究会想起来。她说。用一种我曾经听不懂的语言。
我们握了握手,坐在海底。她的黑头发随着水流铺散,像海草一样漂浮,本应因为长期饥饿而发黄,但梦是弥补缺憾的,在梦境里,那头发细腻而富有光泽,如同上好的丝绸,阴凉而顺滑。我想起我那条丝绸的旗袍,脏绿色的,像青苔和潮湿角落的半水生植物。
我和她对视,从睫毛的缝隙里看到一颗太阳。
我是故意的。我平静地说。我意识到我的记忆有缺失,被关进了盒子里,轻易不能打开。我也意识到那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瘟疫就会在大地上蔓延……潘多拉有神赐的美貌,她的魔盒也是神赐的残忍。我们都知道神喜欢做什幺,征战,撒下硫磺和烈火,焚烧罪人。战争即是神。神把你带来给我,又把你带走。扎鲁冈,我记得这是一个源自波斯的名字,意思是绿色……我是故意的。如我所说,我已经二十二岁,我成年了。我是冷漠,是残酷,是偏执和疯狂,是淫荡和放纵,是自我凌迟,是天生罪犯。我句句属实。只有江明能把你带给我。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只有他才能把你带给我,因为我的父母也已经去世。
他的神情泄露了那个词语,也泄露了你的名字。他会普图什语,一门语言会在她的掌握者面上留下痕迹,江明的脸上显露出了这样的痕迹。普图什语,阿富汗,创伤,精神失常,一切变得有迹可循,而记忆从来没法真正掩藏什幺。作恶者必将被记忆击中迎来报应,而失忆者也终将重回应许之地……
娇娇!水面上有男人在呼唤。
我该走了。
我不能停留太久,我只能在罅隙中来找你,就像小孩只能趁着父母不在再去偷吃糖果。我走了,但我还会回来。
我跟她告别,她的头发轻轻散开,像绚烂斑斓的热带鱼在摆动它美丽的鱼鳍,海水被鱼鳍梳开。幼小的鱼安静地躺在深海的角落,而我浮出了水面。
我没事,我朝江明比划。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手指抚过我的脸颊,几乎脱力一般垂下。他很少恐惧什幺东西,佣兵团的队长已经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数十年,他连死亡都不曾恐惧。但他恐惧我。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任何被期望者手上都天然掌握着伤害他人的权力。江明看了我一会,擡手覆盖在我的眼睛上。我注意到他的掌心是冰凉的,出了些许冷汗。
维多利亚。他低声说,保护好你自己,永远不要想那个词。
好。我借着指缝的光看着他手指粗糙的纹路,笑着说,眼睛都弯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