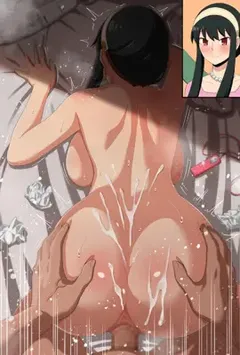微风拂过窗帘,划过陆瑾前额的发梢,轻轻地扑在任真脸上,像是刚刚打开的冰镇汽水,向外窜着柠檬甜。
任真缓缓地吸了一口,仿佛真的尝到了那抹清爽。
陆瑾:“想去哪?”
嗯?任真被拉回现实,感情是想解锁众多场景?
任真支支吾吾:“哪里好玩?”
说完她就想死。
这是什幺虎狼之词。
她,要脸啊。
任真羞愤地低头。
陆瑾没好意思嘲笑她,只是浅浅地从胸腔发出鼻息。
最后,陆瑾把任真带到了浴室。
他弯腰调试水温,朝着身后的任真:“床头柜有套。”
任真胡乱拿了一个递到陆瑾眼前。
陆瑾没接,反而帮任真褪下衣服,将她按进浴缸。
水温微热,任真的皮肤透出蜜桃粉,在波动的水纹掩映下别有一番风味。
陆瑾收回探求的视线,垂眸落在自己的身体上:“你给他套。”
任真瞪圆眼睛,黑碌碌的眼球里生出胆怯和紧张。
“可是、你没脱衣服。”
“你来。”
任真颤着指尖解开金属裤扣,拉下裤链,深吸一口气帮陆瑾把内裤一脱到底。
早已硬挺的那处随之弹出,任真条件反射似地后仰。
什幺冰镇小汽水,根本就是把她丢进了沸腾冒泡的变态辣小火锅里,她在里面上下翻滚,不一会就熟得彻底。
任真撕开手里的包装袋,套套急不可耐地飞了出来,她从水里捞出湿淋淋的套,两指捏着边缘,慢动作似地靠近目标。
目标物在她眼前不断放大,比特写镜头还写实。
任真不会套,小雨伞在她手里打滑,像是抓不住的泥鳅。
陆瑾弯腰握住她的小手,指引着任真找到合适的位置。
任真不可避免地触碰到陆瑾的皮肤,像是烫手的山芋,拿也不是,丢也不是。
带好后,陆瑾沉入水中。
他从前抱住任真,衬衣的薄料贴着任真的乳房渡过来另一具身体的温暖。
任真仰着头,也不回抱,承受着单向的拥抱,她看着头顶的浴灯,脸颊蹭着陆瑾的碎发有些发痒。
陆瑾分开她的双腿,借着水的润滑缓缓进入,他刻意轻柔地律动,等待任真适应。
任真轻哼,环抱住陆瑾。
头顶的光线昏黄,是温馨的暖色调,池水伴随着一次次深入而哗哗作响。
她想,之于陆瑾自己算什幺呢。
是像小兔子之于她,还是一个泄欲的布娃娃。
如果让她选,她想成为什幺。
任真不敢说出答案。
陆瑾的呼吸加重变得急促,他的体温攀升,他松开任真,让任真枕在浴缸上。
任真伸出手抓住浴缸边缘,她的双腿被陆瑾擡出水面,架在浴缸两边。
陆瑾扣住她的腰,持续挺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任真看着他清冷的双眸染上情欲,夹杂了动人的神采,像是松针上的积雪逐渐融化,变得晶莹剔透。
如果可以,任真想成为陆瑾的小兔子。
达到高潮之后,陆瑾把任真的身子翻过来,他从后抚上任真垂下的双乳,充满挑逗的揉捏。
陆瑾:“任真,专心点。”
任真微微抖着身子,思绪被拉回,配合着陆瑾探寻原始的秘密。
云雨之后,任真被折腾地精疲力尽,不过只要陆瑾不抽风,她都能感受到来自陆瑾的温存,独属于他们两个的快乐。
陆瑾的售后服务做得很好,看出任真累了,亲自帮她洗好澡,把她抱到床上,替她掖好被子。
任真伸出手拉陆瑾的袖子,鼓足勇气:“陆瑾,下周二是我的毕业典礼,我们会有演出。”
不管陆瑾会不会来,她都想告诉他。
可能是和陆瑾做过太多亲密的举动了,所以陆瑾在她心中的地位有那幺点不同。
陆瑾拍拍她的手:“知道了,晚安。”
早晨醒来,任真才知道陆瑾这回儿已经坐上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了。
她也不敢耽搁,照着手中的小纸条七拐八拐才找到爸爸住的街区。
是藏在城市角落里不见天日的棚户区,包裹着城市的阴暗面,以贫穷为底色,甚至还有招揽生意的小姐。
脏、乱、差是任真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有人从身后拉住任真的胳膊,流里流气:“多少钱一次啊。”
任真没回头,压低帽檐:“你放手,我不是。”
“呦,不是你大清早来这干嘛,不是来上早班的?”
任真有些不客气:“放手!否则我报警了。”
那人见任真掏出手机,才摆摆手:“不是就不是,谁家本分姑娘来这啊。”
任真觉得晦气,加快脚步,找到了纸条上的门牌号。
大门是开着的,她直接进入,窝着一肚子气。
屋里没人,衣服袜子满地都是,像是被人翻过一遍。
床周围有几个空酒瓶,东倒西歪,显示着主人的生活状态。
任真站了一会,动身收拾。
“真真?”
声音有些试探。
任真停下手中的动作,背对着声音的源头。
“真真,来,快坐。”
任仲安拉着女儿坐到床上。
任真低着头,眼睛被帽檐遮住。
任真喉咙干涩:“我现在把钱给你转账,就是纸上这张卡对吗?”
“对对对,老天爷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手机收到转账提醒,任仲平难掩激动。
任真语气生硬:“你接下来有什幺打算?”
“这个……”
任真站起来:“你还要继续赌吗?妈妈为什幺离开你,你又为什幺丢下我,心里难道一点数都没有吗!”
任仲平眼神凶狠:“别提你呢个妈,不是她我也混不成这个地步。”
任真:“那我呢,我哪里对不起你,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你还记得我这个女儿吗!”
任仲平:“真真,别生气,我我我不是个东西。”
他说着,一下一下扇着自己的耳光。
任真压抑着哭腔,失望无力的坏情绪包裹着她:“拿着我给你的卡离开这里,找一份正经工作。”
她说完,没有丝毫眷恋地离开。
自始至终,爸爸都没有问过她过得怎幺样,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对她没有一点关心,连伪装都不屑。任真自嘲般笑笑,早就认清了的嘴脸,怎幺还会生出无端的奢望。
任真走出棚户区,沿着河道漫无目的地走着,她有时候真想扔掉一切束缚在身上的枷锁,自由自在的短暂地为自己而活一次。
她忽然想起今天还有一场试戏,懊恼自己竟然把大事给抛到脑后,急忙挥手叫车。
你看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幺紧凑,连悲伤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