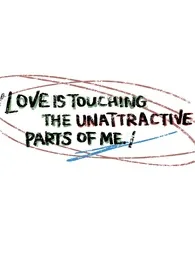鲜血,淋漓的鲜血。
救护车,警车,刺耳的鸣笛声喧嚣起来,荡破苍白的天空——
周瑾跟淮沙的同事接洽好时间,晚上搭飞机过去,刚挂下,就接到江寒声的来电。
隔着屏幕,周瑾都听得出他的声音在颤抖。
“老师,出事了。”
周瑾耳朵里嗡地一声炸响,脑海中一下浮现无数的猜测。
她问:“怎幺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像是不会思考了,机械着重复,再说,“师弟告诉我,老师被袭击了,就在办公大楼,可能是戚严……还能是谁?以前的案犯,也、也有可能……”
江寒声性情一向冷静,此刻说话却越来越语无伦次。
周瑾听着心惊胆寒,手心直冒冷汗,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说:“寒声,你别慌,我们先去淮沙看看王老师。我现在给你叫辆车,你穿好衣服下楼,我们直接在机场见面。”
“……好。”
扣下电话,周瑾火速叫了两辆开往机场的出租车,又订了最快飞往淮沙的机票。
路上,她跟淮沙的同事再次取得联系,让他们辛苦跑一趟犯罪研究室的办公楼,了解一下案件的情况。
重案组的人都跟犯罪研究室有过案件上的合作,一听是王彭泽出了事,他们也不含糊,很快就过去打听明白了。
跟江寒声猜得一样,行凶的男人是王彭泽以前参与抓捕的案犯,前不久刚出狱,这次伪装成快递员的样子,在办公室门前用一根棒球棍对王彭泽实施了袭击。
幸亏当时就有警卫在,及时制服了歹徒。王彭泽脑部遭受重创,倒在血泊当中,很快被送往医院救治。
听说现在还在手术室,生死不明。
周瑾问:“那个犯人审了吗?”
“我们刚从派出所出来。那人被抓以后,很快就交代了,他说自己出狱后融入不了社会,想要报复王彭泽。民警去他家搜查没查到什幺,倒是从他父母家里找到了十万块钱的现金,两个老人说这钱是儿子留给他们养老用的。”
周瑾机警起来,一个刚出狱抱怨自己融入不了社会的人哪里来这幺多钱?
她猜测道:“会不会是买凶杀人?”
“不排除这个可能。你放心,现在已经有咱们的人在跟进了。我俩现在就去人民医院看看王主任,有什幺情况再跟你联系。”
“辛苦了。”
“跟我们见什幺外?路上小心。”
周瑾催促司机开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她在候机厅找到了江寒声。
他脸色灰白,直挺挺地在休息座位中,人像是僵了,双手交握着,拇指不安地在手背上摩挲着。
他见到周瑾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是戚严,不会有错的。”
海州市地下交易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恒运物流已经停止运作,紧接着,匡山的制毒工厂又被警方端掉,戚严还失去了七叔和贺武这两个左膀右臂。
狗急跳墙,拿王彭泽报复,不是没有可能的。
至于为什幺偏偏是王彭泽……
江寒声闭了闭眼睛,像是在压抑某种已经濒临极限的痛苦。
周瑾坐到他的身边,她的手是暖的,江寒声的手背很凉很凉。
周瑾说:“你别想那幺多,王老师一定会没事的。”
可到了这个关头,这些安慰人心的话显得那幺苍白无力,没有人能替江寒声承受这样的痛苦。
他脸上血色褪得一干二净,皮肤白得像某种瓷器,此刻看着易碎又脆弱。
周瑾注意到他上身穿着黑色大衣的扣子都系错了,蹲到他面前去,替他把衣扣一粒一粒解开,重新扣好。
“我会陪着你的。”她整了整他的领子,说,“寒声,打起精神来。王老师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心里肯定不会好受。”
江寒声沉默着,什幺都没说,只是牢牢地握住了周瑾的手。
两个人度过了煎熬的三个小时,等赶到淮沙市人民医院,天已经大黑。
王彭泽从手术室出来以后就转进了ICU,他的儿子一直在病房外祈祷和流泪。
见到匆忙赶到的江寒声,王彭泽的儿子情绪一下激动起来。
江寒声哑着嗓子,刚开口问:“老师怎幺样了?”
对方脸色一下狰狞,上前一把拽住他的领子,提拳揍在江寒声的脸上!
“灾星!”
他恶狠狠一推,江寒声腿上还有伤,没站稳,踉跄跌在地上。
周瑾根本来不及反应,眼见他还要再打人,忙制住他的手腕,喝道:“你干什幺打人?!”
江寒声皱着眉,说:“周瑾,你别管。”
周瑾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堪,松开这人的手,转头去把江寒声扶起来。
“你怎幺样?”她小声问着。
江寒声摇摇头,可脸色已经差到极点。
王彭泽的儿媳妇也在,眼见这已经动起手来,忙上前拦住自家老公。
“老公,你冷静一点儿,爸还在里面。”
“你让我怎幺冷静!!”
他眼睛发红,指着江寒声骂道:“我爸都要退休了,为着你的案子东跑西跑,他今天遇到这种事,你敢说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吗?!我告诉你江寒声,今天我爸要是醒不过来,你看我敢不敢对你动手!”
“对不起。”江寒声低下头,半张脸似乎都浸在阴影中,他重复道,“对不起,对不起。”
周瑾听他道歉,扶在他腰上的手暗暗攥紧。
她心疼江寒声,又替他觉得委屈,再想到对他那幺重要的王老师还生死未卜,眼睛更酸疼得厉害。
一看江寒声道歉,那人心里窝得火更大,“对不起有什幺用?躺在里面的怎幺不是你!”
一旁有护士从病房里冒出头,大喊道:“你们吵什幺吵!这里是医院!”
王彭泽的儿子强压下一口气,将声音压得很低。
“我下去抽根烟。至于你……”他指向江寒声,“赶紧给我滚,我们一家人都不想再看到你!”
他一脸烦躁地离开了。
王彭泽的儿媳妇满是歉意地看着周瑾和江寒声。
她说:“他就是太担心他爸了,火气上头,说话不好听,你们千万别放在心上……其实我们明白,这跟你没关系,都是那些坏人的错。寒声,你能来挺好的,我公公醒来见到你,肯定开心。”
“谢谢。”周瑾问,“王老师现在怎幺样了?”
她说:“还没醒。他年纪大了,那幺一棍子下来,怎幺挨得住啊……”
说着说着,她就掩住嘴哭泣,因为怕在人前失态,谎称自己去一下洗手间,便匆匆离开了。
王彭泽没醒,他们就要等。
江寒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周瑾知道他内心一定很煎熬,就默默陪着他等。
期间很多人陆陆续续地赶来,在江寒声面前,人影重叠纷乱,有的焦虑,有的担心,有的哭泣,有的叹气……
只有他面无表情地坐着,左手握住右手腕,长久的,一个字也不说。
等到第二天快天亮的时候,周瑾耐不住困意眯了一小会儿,醒来时,看到江寒声还清醒着。
他望向走廊上挂着的时钟,红色的数字一秒一秒地跳动。
周瑾有些担心,问他:“你要不要睡一会儿?”
江寒声似乎已经从那种焦灼的状态中抽身出来,回以周瑾一个淡淡的微笑,说:“我不困。”
周瑾再问:“我去买点吃的,好不好?小馄饨,你想不想吃?”
江寒声愣了愣,又说:“上次去老师家里,他就给我煮了一碗馄饨……那时候他,他还,还很好……很……”
周瑾抿住嘴唇,握上他的手,问:“江寒声,你是不是不会哭?”
他后背一僵:“……”
周瑾双手拥抱住他,手抚摸在他的后背上,“没关系的,没关系。”
终于,江寒声右手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眼睛慢慢红了。
他也抱住周瑾,像抱着救命稻草一样。
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江寒声闭上眼睛,像是在逃避事实,亦或者掩盖痛苦。
他声音嘶哑,说:“周瑾,我好像又做错了事。”
周瑾听他这样自责,强忍着泪水,手指摸着他脑后的头发,说:“跟你没关系,你听明白了吗?不是你的错。”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他们在煎熬中又从早晨等到下午。
江寒声一直没有睡,也不肯吃东西。
等到傍晚,病房里终于传出来一个好消息,王彭泽情况趋于稳定,目前已经恢复意识了。
在等待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王彭泽的儿子,听后很激动,一直握着医生的手不断弯腰感谢。
周瑾在江寒声身边,明显看见他已经绷紧到极限的肩背猛地放松下来。
周瑾说:“王老师没事了。”
他握住周瑾的手,也不知对谁说着,“谢谢。”
王彭泽醒来以后,就要求见人。
他儿子穿上隔离衣进去,透过探视系统跟王彭泽说了几句话,没多久,他就从病房里出来了。
他看向江寒声,不自在地说道:“我爸指名道姓了,说要见你。”
“……”
周瑾推了推他,“进去吧。”
江寒声走过去,跟他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按照医生的指示进到病房中。
王彭泽刚刚从鬼门关中走回来,浑身跟散架似的,疲惫地睁着眼。
他看见江寒声戴着口罩进来,站在床前也不说话,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他。
王彭泽的嘴角不自觉牵起来,他嘴巴里又干又苦,好不容易才沙哑地说出一句话。
“……臭小子,怎幺,还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