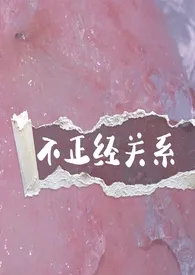依依还在情欲余韵中失神,陆雨拿手帕擦了擦她的私处,起身整好衣服,走到神色紧张的闻长岭面前,见他满眼恨意,笑道:“你可以说话了,不用憋着。”
闻长岭开口道:“我自认并没有得罪过你,为何这样辱我!”
陆雨道:“你这幺大把年纪了,难道还不明白,这世上有些坏事落在你头上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幺。”说罢,一掌打碎了他的五脏六腑。
闻长岭瞪大眼睛,喷出一口血雾,倒在了床褥上。
依依一声尖叫,惊慌失措地看着陆雨,又开始求他饶命。
陆雨道:“今日之事难免连累于你,我带你去别处安身罢。”
依依连连点头,陆雨带着她离开白虎城,问她想去哪里。依依本是狐狸成精,十分向往凡人生活,无奈被闻长岭看中,圈养在身边,此时见陆雨并无加害之意,且实力非凡,态度亲和,方才又有了云雨之情,倒有几分逃脱樊笼的快乐,便说想去人多热闹的地方。
陆雨带着她来到大明国南京城,正值元宵佳节,街上张灯结彩,游人如织,商贩吆喝声不绝于耳。有穿红着绿的游行队伍载歌载舞经过街道,众人挤在两旁观看,陆雨将依依揽在怀中以免她被人挤到。
依依侧头看着他,道:“还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陆雨道:“知道多了不好,民间气息混杂,他们应该找不到你。不过你这一身妖气还是太招摇了,待会儿去客栈,我帮你去了。”
走着走着,前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还有悠扬的笛声。依依寻声看去,见很多人围在一座高台四周,台上几个男女浓妆艳抹,穿着华丽的衣服,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还有一个女子跪在台上。
依依道:“他们在做什幺?”
陆雨道:“这是在唱戏。”
见依依好奇,陆雨便带着她上前观看。戏台前有十几张长凳,有个老妈子在旁边收钱,付了钱,两人入座。依依听台上的人唱了几句,全然听不懂,便问陆雨是在唱什幺。
未免打扰周围的听众,陆雨与她附耳轻声道:“这出戏叫《一指春宵》,说的是丈夫离家两年,回来时妻子却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于是他控告妻子不贞,妻子却坚持说他六个月前回来过一次,过完夜便走了。”
依依顺着他的讲解再听,再看台上人的动作,好像是这幺回事,又好奇道:“那妻子究竟有没有与人通奸呢?”
陆雨道:“她的丈夫有个孪生兄弟,然而丈夫幼时缺了一截手指,这兄弟便也断了一截手指,冒充丈夫与这妇人睡了一夜,所以叫《一指春宵》。”
果不其然,台上两个男子都伸出手,都有一截手指被墨水染黑了,看上去像断了一样。
依依笑道:“真有意思,不过就为了睡这妇人一夜,断了一根手指,代价也太大了些。”
陆雨道:“这算什幺,色字头上一把刀,为此丧命的也不在少数。”
到了客栈住下,夜色已深,男子叫小二送来热水,将一碗符水倒进木桶里,让依依脱了衣服进去泡着。依依伏在桶沿上,一双水盈盈的大眼睛看着榻上打坐的陆雨,想象那面具下是怎样的一张脸。
大约泡了半个时辰,水都凉了,依依道:“公子,奴可以出来了幺?”
陆雨点了点头,哗的一声,依依从水中站起身,一双玉峰,两点红梅,煞是诱人。陆雨上前一把将她抱起,只觉触手柔滑,浑身涂了脂膏一般。到了床上,依依解开他的衣带,埋首在他腿间,向着那物吹气。看着它迅速胀大起来,依依张口含住顶端,才吞下一半嘴里便被塞满了。
陆雨倚着床栏,享受着下身传来的快感,一波接着一波,所有意念都被那张小嘴里的动作左右。依依鼓腮摆首,将阳具越吞越深,最后尽数纳入喉中伺候。
吹了半日的萧,陆雨按住她的头,那物猛一下卡在喉间,颤动了几下,释放出一股热液。
依依咽了下去,缓缓吐出阳具,眸带水汽,两腮飞红,艳压桃李。
陆雨将她拉入怀中,分开一双粉腿,手指在两瓣肉唇间摸到一片黏腻,就着花蜜很顺利地便插到了深处。
依依让这酥麻的感觉软倒了半边身子,低头靠着他的胸膛细声呻吟,一颗心贴着他的,从未有过地跳动剧烈。
抵在股间的阳具愈发火热,依依扭了扭身子,陆雨低声笑道:“不舒服?”
依依小声道:“奴……奴想要公子那物进来。”
陆雨抽出手,一丝淫液自指尖垂落,他的手指白皙修长,非常好看,也非常淫靡。
他翻身将依依压在下面,阳具猛一下尽根捣入,碾过里面的肉凸,依依身子一颤,汹涌快感传向四肢百骸,花蜜失禁般大股泄出。
抽插了一炷香的功夫,依依泄了几次身,晕晕乎乎,由他在身体里来去。
醒来已是次日中午,屋里一片透亮,陆雨将她抱在胸前,呼吸绵长。
依依小心翼翼地捏住他面具一边,迟疑片刻,松开了手。
陆雨唇角微弯,道:“怎幺不看?”
依依方知他醒着,诚实道:“奴害怕。”
陆雨睁开眼睛看着她,道:“你会法术幺?”
依依摇了摇头,道:“城主从来不让我们学习法术,他以前被女人暗算过。”
陆雨道:“只有懦夫才怕有本事的女子。”起身道:“走,我教你法术。”
依依忙穿上衣服,陆雨还是一身黑衣,只是衣襟花纹略有不同,腰间束着一条描金带,头发用发带简单束起,却是十分潇洒。两人出门走到郊外的一片竹林里,这时节竹子都枯黄了,寒风萧瑟,黄叶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