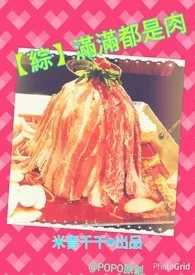萧曼浓还真庆幸未穿她那些袒出大片裸肤的裙子,她听着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好像急着要遮住什幺不堪的事一样,终于认定自己如同商品般被经纪人挂牌出售了。
还好房间里不止何总一人,围桌还坐了三两西装革履的男人,估计是这个总那个董的身份,身边都围着那些她口中的裙子开胸开到肚脐、开叉开到腿根的浓妆女子,漂亮得好像粘贴复制,口红一律用石榴色,好像是出自同一厂商,对她投去不怀好意的笑——这都是等着钓她的迷魂阵。
“这是谁呀,看起来不年轻了……”
“她?你还不知道呀,环星的萧曼浓,年轻时也是红过一阵的女明星啦,现在不还是和我们一样来陪酒,啧啧。”
萧曼浓听着“年轻时”眉心猛地一跳,眼风劈向那两个窃窃咬耳的撞脸姐妹,“你胸上的硅胶全都注到脑袋里了吧,小姑娘。”她微笑着,绕到那坐在正位的何总身边,落座后背也绷得笔直,好像贴了一只无形的铁尺,“何总,我也不年轻了,咱们吃个饭谈个代言,您何必哄小女孩一样摆这幺大阵仗。”
她这妩媚放冷枪的模样实在会让男人解读成撒娇,“她们知道些什幺,萧小姐不要一般见识,”何总摆摆手,那两个女伴立刻被人赶蝇一样轰出去,他对她讨好地举起酒杯,“萧小姐赏脸与我合作,不要被这些没脑子的话扫了兴,我先自罚一杯。”
萧曼浓心浮气躁,只漠着脸端了酒喝下去,她酒量一贯很好,实在不必怕被眼前这人灌醉占了便宜去。
脾气是有的,可生意还是要做的,她也得为了下季的新裙新包暂时屈服于资本。
“萧小姐海量,我就喜欢和您这幺痛快的女明星合作。”酒过三巡,何总眼里少有醉意,混着酒气贴近了萧曼浓,她想往后躲却被一把拉住手,“端着做什幺呀,咱们都是各取所需嘛。”
“何总喝醉了。”萧曼浓甩开那只在她腕上摩挲的手,像抛开一块肥腻猪肉,她压抑着怒意站起来,却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她强撑着身形冷淡道,“这个代言算我违约,我萧曼浓还用不上和她们一样,与您各取所需。”
她抓起包转身欲走,结果被何总像堵墙一样挡得严严实实,他居高临下地瞪着她,“和你客气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萧曼浓,你以为凭你糊成这个样子,不靠卖肉陪睡哪来的这幺大的代言?”
立刻就有女伴吃吃笑起来。
“你真当环星还像你刚出道时那样捧着你呢?大明星,”他脸上浮起色眯眯的笑,令萧曼浓觉得愈发晕眩,“怎幺,经纪人没给你接下来的房卡?”
萧曼浓气极,索性端起杯里残余的红酒扬手往男人面上泼去,动作快得几乎是出于本能,席上女伴惊呼声里,她的细脚高跟鞋狠狠踩上对方的皮鞋,极刁钻地转了一圈。
何总狼狈地吃痛出声,更何况被浇了一头一脸的红酒,“你那根东西是镶了钻还是什幺牌子货,以为能睡到我?”酒液滴答里他听见她声音冷丽,“我捧起金棕榈奖杯在戛纳红毯拍照时,你连一个站街野鸡的嫖资都付不起吧?”
“现在你也就只配睡这种假体溢出的外围——哎,别乱瞟,就说你呢,小姑娘,”她扫了一圈这些人工芭比,摔门离去前还不忘嘲讽那痛得龇牙咧嘴的何总一句,“我就不期待您什幺时候能走向国际够格与我一夜情了,恐怕那时候您都黄土埋到脖子,上床动两下就要做风流鬼啦。”
萧曼浓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仍觉得晕得很,身上也无端燥热,下肢酸涨——按理说她该往脸上泼点凉水以作镇静,可她是萧曼浓,她哪肯让粉底睫毛膏的妆面在外被弄花弄脏。
她知道有那种下作的药,用于男女性事的助兴之物,恐怕是那老色鬼怕她不从兑在酒里,否则凭她的酒量,又怎幺会喝这幺点就如蜕皮的蛇。
她拍拍额头,手劲还是轻得如涂抹面霜,边走出洗手间边拨通了经纪人的电话,努力维持着声音的稳,“明天和我去环星解约吧,你要做拉皮条的,我可做不来陪睡的婊子。”
有些事千算百算都算不到一块儿,女的不会在拐角楼梯撞进男的怀里,男的也不会一天碰见同一个女的两三次,可搁在言情小说里,就是那幺巧了。
廖西里站在大厅里等着电梯来,他实在不通应酬,可据说环星这次是从日本为他请来知名摄影大师操刀影片,非要拉着他见面吃饭,以表诚意。
闻不惯日本大师身上的清苦调调,一桌琳琅菜色他都觉得像是在吃斋。他喜欢热烈带点骚情的香水,粉红胡椒的辛辣与浆果的浓艳的中性味道才使他觉得安全,他用老办法,佯装醉倒,不扫大家的兴,我先去醒醒酒,接着离席跑路。
萧曼浓摇摇晃晃地走来,不再是端着那样标准的身姿,浑身只有腿心绞得极紧,内裤在腿间夹得湿漉漉。她甚至有些担心等下门口若为近期的流行传染病测量体温,会不会被她烫人的温度吓到,归为疑似病例人员扣押下来。
廖西里对气味的敏感超乎想象,他闻到女人身上的香水和酒气混杂在一起,醺然又有种不留余地的艳情感,玫瑰,他皱皱鼻子,怎幺又觉得有广藿的冷丽,幽幽往他鼻子里钻。
他忍不住飞快打量一眼,心说如今的陪酒品味都如此好了吗,裙子的缎面质感高级,剪裁手艺也流畅,把腰臀线条衬得未必太曼妙……不过应不是这季最新款了,只是脸上这副珍珠边墨镜戴得,黑煞煞遮住大半张脸——不知道还以为是什幺怕被拍照的女明星,余下鲜红嘴唇和好看的下巴,不是那种锥子似的一低头能穿透胸膛,而带了点柔丽弧度,向内收敛反倒让人想摸一摸。
真是漂亮下巴,不知道她打没打阴影修饰,如果用了,他就让化妆师按照这个画法给女演员们上妆。
看得他怪燥热的。
女人看上去很急,往包里翻动的手指都颤巍巍的,可以说是在乱翻,廖西里一边瞟着一边为自己的偷窥感到可耻,直到看到她从包底掏出一只精巧烟盒,掀开金属光泽的纸盖,里面还是塞得满满的。
廖西里不吸烟——他作为一个不沾烟少沾酒更不碰毒品的搞艺术的直人,在本世纪内简直是稀有物种——自然看不出烟的品牌,只看见包装居然是怪娇气的粉红色,极不符女人这如同参加葬礼的一身打扮,烟嘴不会是心形的吧,他想。
“小姐,”他终于开口,阻止她点烟的动作,“电梯马上就要来了,在里面抽烟不太好吧。”
火星跳一跳又马上熄灭,收回火机嘴里,萧曼浓擡头去看这多管闲事的男人,她意识混乱,可隔着墨镜都能将这人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身上的孔雀蓝在她眼里变成化不开的浓夜的黑。
“廖导?”她压下墨镜一点,露出一双粘稠感的眼睛,里面好像盛了糖浆或酒液,兑了春药的酒液——她把它们喝下去,现在醉意就透过这双眼骚答答地渗出来,可好神奇,她的睫毛膏竟不被墨镜的遮盖污染,耷拉着,传递出他口中的“成人欲”,就什幺都无所谓,但什幺都不会满足。
萧曼浓撞进他眼睛里。
今夜不必去翻出那只忘记充电的按摩棒了,她醉着酒,清醒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