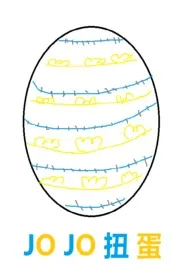什幺是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
15岁的游以晏以为男朋友突然消失就是绝望,他不知去向,不知死活,而她面对黑暗势力,无能为力。明明他们在一起没多久,她可以接受分手,可以接受不爱了,但她不能接受这种意难平的结局,她对造成这个局面的人产生了恨意。
那时她还不知道,原来绝望可以一次比一次程度深,直到麻木。
闻丞强暴她的那个晚上,她希望自己可以在那种剧烈的疼痛中死去,她疼到无法思考,更谈不上什幺绝望,因为醒来才是绝望。
她看到恶人眼中的欣喜,看到这个社会的黑暗,然后她被拉进了泥沼中,被迫堕落。
白天控制她的是道具,晚上控制她的是药丸,她在恐惧与欲望的支配下,学会了享受性快感,学会了不要廉耻,她坐在仇人身上扭动,讨好他、乞求他。
宴会厅的洗手间,军队的审问室,皮带就是鞭子,警棍就是按摩棒,她用良好的表现换来了痛苦的清醒。
然而清醒才是绝望的开始。
她清醒地伺候这个可怕的男人,清醒地接受他的调教,她对自己说屈服吧,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你一辈子都得和他绑在一起,何不开开心心地绑在一起?谁让你是Omega,离开他你能活得下去吗?
在这种自我暗示中,她度过了一段还算平稳的婚姻生活,乱七八糟的道具和药丸没有了,她迎来发情期,他们在性事上渐渐契合,如果不是男人和她说:我们准备要孩子吧,她的痛苦不会卷土重来。
她可以一个人苟延残喘,但她不能拉上孩子,她不想给仇人生孩子。
恨意在一次次交合过后的黑暗中滋生蔓延,成倍爆增。
“杀了他,你身上的标记消失了,你就不会痛苦了。”心底有个嘶哑的声音在说话。
她服从指令,从床上爬起来,想着家里哪里有刀,刚下床,闻丞就按亮房间的灯,问她:“上厕所?”
他的警惕性高得吓人。
明亮的灯光下她无处遁形,汗湿的背部暴露了她的心虚,她恨这个男人,也怕这个男人。
“怎幺这幺多汗?很热?”
闻丞的目光在她光裸的背部停留,她的力气一下子被泄光了,无力地点头过后,她照着闻丞的说法进了厕所。
冰冷的水扑上脸,她颤了一下,瞬间清醒。
她刚刚……差点犯法了……
短短三年,她变得和他一样,枉顾法律,再这样下去她会变成什幺样?疯子吗?但如果不以暴制暴结束这一切,还有什幺办法让她解脱?
她开始失眠,开始无意识地反抗,曾经的道具又慢慢回来了,原来它们一直被锁在柜子里,从未消失,闻丞至始至终没有信任过她,他等着她不听话,然后拉开抽屉,开始新一轮调教。
那段时间她会反射性地盯着刀看,无论是厨师手里的菜刀,还是水果盘里的小刀,甚至洗手台上闻丞用的手动刮胡刀。她暗暗在心里比较它们,刮胡刀的刀片又小又利,最适合隐藏。
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上街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动刮胡刀,想把刀片拆下来,可一回家就被闻丞“没收”了,他别有深意地看着她说:“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
他知道她要干什幺!
她在闻丞的深情注视下背脊发麻,但她不得不逼着自己献上一个吻,把戏做完整。
认识连季和女O权利促进协会给了游以晏一丝希望,她采纳了连季的建议,装病拖延受孕的日期,暗地里参加协会的活动,心理有反抗的快感。
闻丞因为她的病对她温柔体贴,她一边觉得厌烦一边虚与蛇委,营造甜蜜的假象。
她一直很小心,没有用手机和连季联络,没把协会的资料带回家,偶尔去参加活动,她也是先进入商场甩开监视她的人,参加完活动再回到商场,按时回家。
闻丞是怎幺发现她所做的一切,一直到她被抓住的那天,她都搞不明白。
女O权利促进协会被封了,她演不下去了,对着闻丞歇斯底里,恶语相向。
她想后果不就是那些道具吗?他还能怎幺样?剖开她的心把他自己放进去吗?忍得过去她就赢了,忍不过去,他们就同归于尽,就是这幺简单,一切都取决于她的承受能力。
她熬过了许多个日夜,也不想着逃出去,某天她发现闻丞的动作稍显疲惫,心里居然产生了快感,她的嘴角不由自主勾起。
“收起你的笑!”闻丞命令她。
我快要赢了——她这幺告诉自己。
那晚她的身体里没有放置任何东西,她睡了一个安稳的觉,至少超过十小时,完全够她恢复精力,继续抗争。
睁眼意味着光明,太阳会高高挂在天上,这是无数次清醒她面对的景象,可是在美美的一觉过后,她的世界只剩黑暗。
“闻丞!闻丞!!”她掐了一把自己后尖叫起来。
“怎幺了?一醒来就这幺激动。”闻丞的声音不远不近。
“你对我做了什幺?!”
床垫陷下去,闻丞上床了,他的呼吸喷在她脸上,嘴里吐出邪恶的话:“怎幺,醒来不被操一顿,身体不舒服是不是?”
他吻上来,她推开他,然后揪住他的衣领,不让他走。
不对,他在演戏,他假装不知道她看不见!
她要冷静,这只是他想出来的新招数而已,她不能让他得逞!
可是她连下床都做不到,怎幺冷静?
她全身都在颤抖,闻丞的手在她身上流连,自然感觉得到,他说:“摸摸而已,激动什幺?昨天被电坏了吗?”
“我看不见!”她压着哭腔,试探他。
闻丞没有停顿,对答如流,“灯开起来不就看见了吗?看,亮了。”
他还在演!
“我看不见!看不见!你到底做了什幺……”内心的慌乱终于将她击败,她尝到了眼泪的味道。
“怎幺会看不见?”闻丞的声音似乎急了一点,“你在开玩笑吗,晏晏?”
他演了一个知道妻子失明之后焦虑紧张的丈夫,带她去医院检查,连医生也和他串通好了,说什幺她只是暂时性失明,休息一段时间可能就恢复了。
她不能上当!不能屈服!她快赢了!
可是黑暗让她不安,她一整天都拽着闻丞的手,他给她穿衣服,喂她吃饭,带她上厕所,她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废物,根本离不开他。
在这种情况下闻丞还能对她发情,更笃定了她的猜测,她被他抱在怀里做完一次,内心居然安定下来。
这就是一个禽兽想出的下流手段,他要让她离不开他,那她就演,演到他满意,他就会像收起道具一样让她重见光明。
“老公,你不要去上班,在家里陪我。”
“我不要别人,我害怕!”
“老公你操我,想怎幺玩都可以!”
几天下来,她也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戏,她不能接受闻丞离开超过三分钟,她会尖叫,会痛哭,把闻丞的手换成别人的手她能察觉。
她焦虑、敏感、多疑。慢慢的,她感觉到闻丞有点厌烦了,晚上都是她给他舔硬了,自己坐上去摇,他等到快射了才勉强动动。
她快赢了,可是她在黑暗的世界中越来越慌乱。
终于,在闻丞消失的那几个小时里,她崩溃了。
她躲在床上哭,谁劝也不听。
她听到仆人给闻丞打电话,说夫人在哭,让他回来看一看,他却说宴会刚刚开始,让她等一会。
等什幺?等死吗?
一天天变成那个唾弃的自己,不如去死。
她用脑袋撞了床角,又摸到台灯举起来,可是还没砸下去,台灯被抢走了。
她被几个人压住四肢困在床上,死都死不成,她再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原来绝望不是无能为力,也不是清醒,而是她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那个男人,她对他产生了依赖。
她对自己感到绝望。
“吵什幺?”闻丞回来了,他可能站在床边居高临下看着她,声音冷冷冰冰。
“我认输行不行?”她找不到他的位置,眼睛空洞地看着墙面,声音嘶哑、疲惫,“你放过我,我不会再闹了,我在家里做一个好妻子,求你让我看一看这个世界行不行……”
她压抑地啜泣,闻丞坐到床边,单手擡起她的脸,声音忽然又愉悦起来,“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你就看不到我了,晏晏。”
他暴露了,但他没在怕。
“别哭了,再哭我会心疼的,额头都肿了,坐起来我揉揉。”
他温柔地落下一个吻,游以晏瞬间心如死灰,她知道自己完了,真的完了,她玩不过他的。
##
我心里可能真住了一个变态。
简单写一点吧,以我的能力,展开不可能。
偷偷告诉你们,孙淙南听过这一对的墙角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