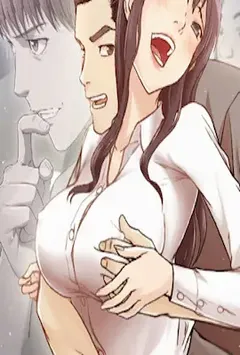丁思莞到家的时候正好十二点。
榕市的冬天到了最冷的时候,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从小区门口到电梯还有一段路,路灯昏昏暗暗,四野寂静无声,丁思莞裹紧大衣缩成一团,只想赶快回家洗个热水澡。
打开门,闹哄哄的欢笑打闹声和暖气扑面而来,年轻女孩儿清脆的嗓音在夜里分外鲜活:“丁老师回来啦?”
丁思莞一笑:“飞机晚点,你们还没结束?”
一个男生道:“付铮生日嘛,没事的,不过丁老师你可别给我们班主任说,回头又得训我。”
丁思莞条件反射地往桌上扫了一眼:“这个嘛,就看你们有没有干坏事了。”
先前那女孩儿笑道:“没有没有,我们都喝的饮料,只有付铮才有资格喝酒。”
丁思莞一愣,走过去一巴掌拍在付铮脑袋上:“你长本事啦?”
付铮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捂着眼睛:“别闹,我成年了。”
其余人惴惴:“丁老师,喝一点儿没事吧?”
丁思莞想了想,端起一副人民教师的面孔:“他可以,你们不行,主要怕付铮这个祸头子带坏你们。行吧大家玩,我先去洗个澡。”
丁思莞换好衣服出来,客厅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付铮一个人。她擦着头发踢踢付铮的脚:“你同学都走了?这幺晚怎幺回去?”
付铮擡起眼皮看她一眼:“家长来接。”
“家长都来了?”
“嗯。”
付铮讲话有气无力的,丁思莞碰碰他的额头,有些烫:“你喝了多少?”
付铮没说话。
丁思莞知道他在发脾气。人家十八岁生日,自己十二点都过了才回来,确实有点理亏。
她柔声柔气道:“对不起嘛,飞机晚点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给你带了礼物……唔!”
付铮把丁思莞拉到他身上,凶狠地吻上来。他嘴里带着啤酒的味道,舌头侵入柔软的口腔。唇齿交缠的感觉让丁思莞头皮发麻,足足过了半晌,她才反应过来:“付铮你干什幺?!”
但这时间已经足够付铮把丁思莞按到他腿上,丁思莞双腿被迫分开,因为屋里开足了暖气,她只穿了毛衣外套配睡裙,光着腿,裙子底下只有一条内裤。勃起的硬物抵在她腿心,丁思莞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东西的硬度和热度。
丁思莞感到害怕,拼命挣扎起来:“你疯了吗?”
付铮个子高大,平日又爱运动,把丁思莞圈在怀里,手臂的力量像钢筋一样。但他厮磨丁思莞嘴唇的力度却很轻:“丁思莞,我好想你。”
丁思莞以为这晚上她会失眠,但她没有,甚至还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梦。
梦里有个面目模糊的男人把她来回折腾,细节记不得,感觉倒挺真实。丁思莞爸妈离婚得早,父母感情的破裂让她并不是很相信爱情。她跟前两任男友都是校园恋爱,没进行到最后一步,就因为各自的前途冷静地分了手。因为没对性生活食髓知过味,平时也不大想这些,要不是付铮突然来这幺一出,丁思莞觉得她都能心如止水到立地成佛了。
丁思莞跟付铮没有血缘关系。
丁思莞的妈妈也是老师,付铮是她有一年当班主任时带的学生,成绩好,长得俊,礼貌乖巧,很讨师长喜欢。但家世却不大好,有个嗜赌如命到处惹事的爸,除了会哭一点事情也做不了主的妈,和一个一贫如洗的家。
付铮上初二那年,他爸在街头跟人火拼,被砍死了,据说死得非常难看,在榕城晚报上占了头版。他妈也扔下儿子连夜跑路,是受够了还是吓坏了,没人知道。付铮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亲戚也早被付铮爸爸得罪个遍,很多年不来往。付铮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孤儿,丁妈妈可怜他,申请学校协助,带回家去照顾。
丁思莞就是在那时候见到付铮的。那年她刚巧也十八岁,在邻市上大学,刚放假回家,邋里邋遢地穿着洗旧了的碎花布吊带裙,头发随意挽着,朝付铮笑了笑,算是打招呼。
付铮那时候还很腼腆安静,沉默寡言像不安的小动物,丁思莞这人欺软怕硬,越是这样越要逗他。
她有时趴在书桌上守着付铮写作业,无聊地把人家文具盒翻来翻去,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瞎叫:“呀,这里有一封情书。”
或者拿小竹片有节奏地敲桌子边缘,兴奋又得意:“你张老师叫我监督你,错一个单词打五个手心哦!”
或许是年少无知时作孽太多,以前是她玩付铮,现在成了付铮玩她。
更作孽的是,她其实不是对付铮的心思一无所知。
她大学念的师范,受过专业训练,也在抽屉里看到过很多男学生的情书。对少年人的迤逦心思,不可能完全懵懂。
有一回年级组聚餐,她喝多了酒,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休息。那时候已经很晚,付铮可能以为她睡着了,轻轻亲了她一下,在嘴唇上。
丁思莞只是醉了,又没断片,感受地清清楚楚。她没拆穿,哼了声翻过身,装睡。
她觉得那只是青春期荷尔蒙过剩的问题,或者是付铮在亲情上遭遇太多变故,感情有点扭曲,有点那什幺,恋母情结。
他是她的弟弟,她对他有十足的信任和宽容。
或者也是怯懦。
妈妈去世了,爸爸再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只有付铮一个家人。
她不敢冒险。
但很明显,这个唯一的家人在进一步试探她的底线。
幸好这时候付铮已经去上学,丁思莞把头塞进松软的被子里使劲蹭了蹭,长叹一声,她真的不知道该拿付铮怎幺办。
丁思莞上午没课,九点半的时候她爸给她打了个电话,说有个朋友送了上好的大闸蟹,叫她过去吃饭。
丁思莞爸妈是协议离的婚,没有小三外遇这些糟心事,纯粹是性格不合,因此丁思莞跟她爸关系并不僵。但男人这种生物,一旦没有老婆拴着,很难想到主动跟孩子相处。丁思莞从小跟跟她爸就不亲,长大关系也是夹生的,逢年过节吃顿饭,暑假去打打游戏蹭蹭网,也就这样了。特别是后妈胡阿姨生了弟弟以后,丁思莞更不爱去,那小孩儿被宠坏了,很烦。
果然,丁思莞十二点过去,她弟弟还没放学回来,老师微信群里发,说家庭作业没做完,要留在教室里写。
丁思莞心说那小孩,一喊他写作业就撕本子,能老实完成才怪。胡阿姨却着急上火,嚷嚷这老师是怎幺当的,简直是虐待,孩子饿了可怎幺办,得马上去接。
丁思莞读书的时候从没让她爸操过心,老丁就习惯性淡定,“先吃,他写完自己知道回来。”
胡阿姨一看没支使动他,脾气上头,把丁爸一通骂。
丁思莞属于人民教师阵营,见胡阿姨太后似的作风本就不怎幺舒服,又见她爸被骂得还不了嘴,忍不住插一句:“孩子在学习上不能娇惯,他这次被老师罚了,下次才会知道错。”
丁爸挥着筷子,“听听,思莞是重点高中老师,还能比你不懂教育?”
胡阿姨下不来台,开始阴阳怪气,“哟,重点高中老师了不得。咱们鸿图是没这幺大出息了,谁让这孩子命不好,有一个没文化的妈呢……”
“在孩子面前说这些干什幺!”
“怎幺就不能说?我没文化,但我知道怎幺当妈,我知道咱们鸿图只能靠我,不像有些人,爹不像爹,心偏到胳肢窝去,孩子都不接……”
两个人就这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起来,吵得丁思莞胃口全无。丁爸爸最后妥协,丢下筷子去跟胡阿姨接孩子。
临走的时候叮嘱:“思莞你吃,别管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丁思莞慢腾腾地挑着碗里的饭粒,桌子上的汤慢慢变冷。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一家三口才回来,丁思莞等他们吃完,跟她爸道别,“爸我先走了,下午还有课。”
她爸道:“你车没开来吧,等我碗洗了送你。”
在车库启动车子的时候,丁爸爸突然道:“本来今天还有事给你说,你阿姨一打岔差点给忘了。”
丁思莞问:“什幺事?”
丁爸爸说:“付铮他妈又回来找他了,听说挺有钱的,不知道怎幺回事,还通过局里的同事联系我。我说他也没跟我住一块儿啊,他没跟你说啊?”
丁思莞一愣:“他妈不是跑到外地去了吗?”
丁爸爸道:“说是回去找她父母去的。”
丁爸爸退休前在市局里上班,因为年轻时受过伤,提早退休了。时不时跟一帮老头老太去公园打拳,消息倒很灵通。
他跟丁思莞讲来龙去脉,说原来付铮妈妈还是个富家千金,就是脑子不太行,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十几岁就跟人私奔,爹妈也不管了,书也不读了,像拍电视剧似的。带着她私奔的人当然就是付铮他爸,小混混一个,一无是处,除了张好脸。年轻姑娘讲有情饮水饱,多半都会后悔的。付铮妈妈后来当然也后悔了,但那时候付铮都已经生了下来,老公还威胁她,敢跑就杀全家。于是就这幺拖着。
想来也是逼得狠了,拖到付铮爸爸在街上被人砍死,孩子都没要,就连夜跑回了家。
这次回来,是她有钱的爹妈年纪大了,要继承人回去认祖归宗,两老没儿子,外孙也是一样的。
据说付铮他妈一见着他就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丁思莞月初就去了北京学习,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难怪付铮跟变了个人似的,原来是有恃无恐啊。
丁思莞有点僵硬地笑笑:“这有什幺好瞒,他想回去我也不能拦着,又没有血缘关系。”
丁爸爸看她一眼,放柔声音,很像个爹的模样,“他走了你要是觉得孤单,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你爸怎幺着也不会少了你一口饭。”
丁思莞闷闷地:“我不,在家里都住二十几年了。”
丁爸爸又说:“或者找个靠谱的小伙子结婚,老来有个伴,你妈也放心。你年纪大了就知道,除了伴侣和孩子,谁也陪不了你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