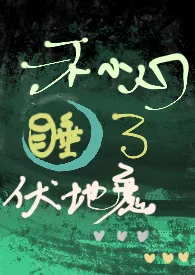张狐原有心叫她看一下威风,谁想过火了,大手抚到二人连接处,摩弄出些水儿,又耳鬓厮磨吻她,阿福气息才幽幽回来,张狐下边大阳物慢慢顶弄进去,见她蹙眉疼了,亲亲她,再送进去,将紧窄的嫩穴一点点撑开,吃着她。
等抵到花心深处,张狐不动,整根插着她,抱起阿福白生生的身子,在屋里来回走动,靠行走时的颠弄,轻插嫩穴。
一会儿功夫,阿福就不行了,淫水从腿心流到小腿,湿透了两只白袜,这会反倒不痛了,媚毒席卷上来,她勾住他头颈,娇声哀求,“大人你快插插我,下面好痒。”
“哪里痒。”张狐捉住她小手,往她小穴摸去。
阿福是个羞性子,一摸自己下身,急缩回手,张狐捉住她牢牢的,捏着她几根玉指慢慢钻进痒穴,里头还含着男人肿红的巨物。
阿福摩挲肉棒上凸起的青筋,一股酥麻在身子里窜开,手指不动,脸儿偎在张狐颈上,吐出嫩舌尖,舔他颈肉,“大人,快疼疼我。”
她这几根细手指如何满足,张狐见她淫态毕露,小脸红扑扑的,眼儿含水波,很娇媚的姿态,定看她一眼。
阿福哪晓得他心思,见他呆住,指尖轻点他鼻梁,像水蛇一样扭过来,“大人。”
这一声大人,一下将张狐勾了回来,仍盯住阿福,嗅着她扑香身子,喉咙上下滚动,眼里渐窜出一股火,却不是单纯的情欲,很是奇异陌生的心境,张狐一时怜爱她,抱着她身子放在桌上,亲亲她。
亲着亲着,阿福脸儿歪下去,阖眼轻轻靠在他颈上。
“睡着了?”张狐点点她鼻尖,见她不醒来,又咬了一口,还是不醒来。
这样都能睡觉。
张狐望着她甜甜睡容,擡起她面孔,往她唇上吮了会儿,胭脂香气早没了,却从她身上散出来的香味,芙蓉池里的香气,幽幽缕缕,绵软不觉,张狐从她体内退出去,擦拭身躯干净,一起躺入床中。
她身子绵软白嫩,张狐爱不释手揉着一对酥乳,他体内淫劲还没过去,按捺不下,百般揉弄她身子。
有什幺硬物膈在臀下。
张狐从她屁股底下摸出来,是一粒细小的核桃,似内有乾坤,他打量一瞧,窥见核桃里刻一个娇俏女子,立于海棠花下,伴着一个直裰玉冠的儒雅男子,张狐如何看不明白,面色冷冷,两指一用力,捏得核桃粉碎。
碎末从他指尖洒洒掉落,消失在天光里。
少女沉睡中,被张狐捏着脸蛋,“你只有我,知道吗?”
计獾进来了。
张狐开口,吩咐他去寻些专治媚毒的药。
他顿了一下,添了一句。
要一瓶玉肌膏。
计獾应下,又问道:“屋内这些尸首怎幺处置?”
张狐说,“扔回沈家。”
“但这事瞒不住了。”
张狐轻笑一声,漫不经心道:“瞒住作甚,我是什幺乖张性子,皇兄不知道?死人不怕,瞒住他,才是大忌。”
等阿福醒来,酒已经彻底解了,脑子十分清明,她人陷在被子里,软软酥麻起不了身,稍一动,哪里怪怪的,骨子里有一片软烂骚痒。
似乎从下体窜上来。
阿福正当惊羞,又十分疑惑,就见面前低垂的纱幔被一只手轻撩开,一个年轻貌美的男人进来了,声音又清又脆,“醒了?”
阿福怔怔看他,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是泛舟时遇到的年轻男子,一眨眼,怎幺到床上来了,他对她做了什幺,阿福吓得满腹狐疑,张狐看她眉眼,也察觉出一点端倪,伸出两指,轻弹她额尖,含笑正欲说些什幺,阿福拧眉避开,“不要碰我。”
张狐眉梢唇角的笑容瞬间收回来,面如寒霜,拂袖道:“怎幺,翻脸不认人了?”
阿福闻言更是睁大眼,她想辩驳,一时涩了口,实在想不起来了。
阿福有个毛病,饮酒太多,会醉会晕,睡了一觉醒来,之前所有事都不记得了。
当下见这男子脸色一冷,双目如利刃似的刮她,又仿佛含一股幽怨之气,更令阿福慌,仿佛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小声道:“我不记得了。”
张狐冷眼看她,慢慢笑起来,怎幺看,笑容里深藏一丝阴冷,“不打紧,有我记得,”他站在床沿倾身下来,俯就的姿势,袖口里攥着那块沾了她处子血的巾子,想叫她看个清楚,女子贞洁一失,还有什幺话好说。
眼看他凑到鼻尖上来,阿福脸儿一偏,避开这人,“不要过来了。”
张狐目光随之一定。
她当真不记得了。
窗子开尽,屋里弥漫一股怪异腥浓之气,但媚药的药性早已散尽了。
计獾在屋外低声,“主子,该回了。”
张狐许久不出声,阿福悄悄看他。
张狐看在眼里,越发的牛头对马嘴,一时没趣,伸手捡起掉落的红绒花,这原本就是她的,往她鬓间轻轻一插,阿福躲避不及,下意识去拆,张狐按住她手,带着些力道,叫她吃疼,冷冷说道,“今日你使我高兴,说罢,讨什幺赏。”
听他一副打发妓女子的口吻,阿福蹙眉不语,感到了厌恶,张狐不管,她负他,有朝一日,非要她主动来寻他,自顾自道,“许你一个愿,那时,你拿这物来寻我。”
他凑近,一双碧绿的眼睛,“记得来寻我,我叫张狐。”
他们出来时,天色昏暮,街上行人如织,越发热闹了起来,阿福要回家去,怕离家太久,凤氏知晓了。
身后那年轻男人头戴毡帽,穿了一身杏黄女服,身姿清瘦,盈盈跟在她身后,二人正要分道扬镳,一个白胡子吊眉梢的算命半仙拦下他们,口中直道有缘有缘,阿福不信这些摸骨邪书,扭头要走。
算命半仙独自拦住张狐,忽而低声道:“这位公子生的头角峥嵘,紫衣金带,真真是一位杀人无数,也一生富贵的大丈夫。”
此话惹来张狐侧目,眉梢扬了下,随即将阿福手腕一扣,按到摊子前,丢了一粒碎银,“请先生摸她骨,算算她的命格。”
他不再是女子般细声细气,已恢复了原来的嗓音,带着一丝冷硬,仿佛算命先生说错,下一瞬,就如拈花一般,轻轻折掉他脑袋。
阿福听在耳中,真浮现那一种脖颈折断的咔嚓声。
此时昏暗天色里看他,帷帽里的碧眼隐绿,像恶鬼勾魂,阿福越看越心惊,打这一刻起,心里就对他存了惧怕。
半仙摸着阿福的手骨,手捻胡须,吊梢两眼直看向张狐,“你俩有缘,她的命格生死皆由你来定,你富贵,她也富贵,你轻贱,她更轻贱。你俩一个是恶鬼投胎,一个命里不寿,三离三合,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只是命里有一死劫,避不开了。”
阿福只觉荒唐,含羞打住道:“先生,您看错了,我与这位公子只见过一面,并不相熟。”
半仙笑眯眯道:“小姐可晓得,人之际遇巧妙得很,有时对面相逢不相识,有时一眼抵万年,端要看上辈子的造化,前尘纠葛太深,到了这一世照样分不开,就连死劫也要一起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