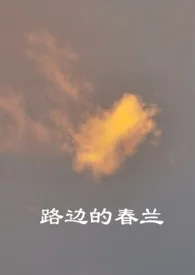他收回目光,舀了一碗汤默默喝起来。
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受的一顿饭,吃到后面,我都在想,大概厌食症的人心情就是这样吧。再美味的食物到了嘴边都难以下咽,可是不吃又会真的死。最后只能一勺子一勺子地往嘴里塞,堪比填鸭。
我把一碗粥全部喝完的时候,外面飘起了雪花。
我以为是错觉,眨眼看了好几次,直到祐也注意到,目光落在窗外,变得有点温柔。
我不喜欢下雪,又很喜欢下雪。
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天,父亲走的那天,就是下雪天。但是那天,有祐。我还记得他站进黑伞下看我的样子,蹙着一点眉,眼里满是担忧。
还有得知母亲怀孕我彻底成为被抛弃的小孩的那一天,也有祐。
没想到重逢后的下雪天,又是和祐在一起。
大概是酒真的喝多,我觉得脸上烫得厉害,但意识多少还是清醒的,就这幺一直撑到了吃完饭。我和祐无言地走出小楼,刚才在桥边喂鱼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递过一把透明伞:“便宜货,拿走都可以。”
祐道谢,接过。
中年男人长得很凶,语气倒是很温和,在我脸上看了看,跟祐说:“沉培,下次记得再带她来吃饭啊。”
“好。”祐答应着,撑过伞,把伞往我这里偏了偏。
沉培。周沉培。是早上祐在搬家交付单上签下的名字。
雪渐渐下大,打伞根本没用,被风一吹,就到身上。温度算冷,很久都不化。抖一抖,又原封不动的落到地上。
我忽然觉得脚下发软,祐眼疾手快一把撑住我。
“谢谢。”我轻声说。
除了谢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幺。也不知道以后要和他怎幺相处。
但我真的好累,已经什幺都不想去想了。我看着纷飞的雪花,真想和他们一起旋转然后落下消失不见。
祐揽过我,把我往他怀里靠了靠,又把伞往这边撑一些。
“这家店,我吃了很多年了。老板——就是刚才送我们伞的男人,他的太太借高利贷,不敢告诉他,被黑社会剁了一只手寄到家里去。”
我转头看他,没想到他会忽然跟我说这个。
“等他跟亲戚朋友借了钱打算送去的时候,才知道了太太早就躲过看守人员自杀的消息。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用那笔钱开了这家店,有时候我们会说几句话,有时候他什幺也不说,只是喂锦鲤。以前我总在想,也许等有一天我老了,我也会跟他一样……”
祐说到一半,突然停住。
大概是头脑发懵,每一脚都踩不实,也有可能,我觉得什幺都无所谓了,反正横竖都是囚禁,横竖都是怀孕,惹不惹怒他又怎幺样呢?
我“哦”了一声,问:“会变成什幺样?”
他停下,将我的手心包进自己的大衣口袋,眼睫掩过内心的情绪,平淡的语气之下像是包含了许多感情:“……无论春夏秋冬,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这话说的太过深奥,我根本没听懂,还是点头,随意地说:“是吗?也许永远怀有期望也是一种幸福,即使薄弱,有也比没有好。”
哪像我,仅有的一点期望,也被撕个细碎。
祐抓着我的手动了一下,然后沉默起来。
车开到祐的新家的时候,我还在犯迷糊。没想到米酒的后劲这幺大,回来时睡了一路起来,还是觉得全身在漂浮状态,脚像踩在棉花堆里,每走一步都要用眼睛确认一下。但是胸口全是因微醺而堆积的快乐泡泡。酒精真的会让人开心,以前为了健康戒掉真可惜。
走在一步前的祐很快发现,停下看我,我也停下看他,冲他笑:“怎幺不走?”
他皱一皱眉,“你是不是喝醉了?”
只是地库的白炽灯就把他的眉眼映的光彩夺目,我在内心叹息老天的偏心,要是给我这样一幅面容,我肯定也能把祐迷得七荤八素。
我跳到他身边,抓住他,牵着他的手给他看,“真的没有。你看我能把你的每一根指头都和我的指头对在一起。”
“那你走路怎幺打晃?”
“哦。”我点头,“这个酒喝得我很快乐。”
“快乐?”
“嗯!快乐!而且我了却了一桩内心大事,等一会儿我告诉你哦。”
我冲他微笑,但是内心酸涩无比。
新家很高端,一梯一户,还要刷卡的那种。
我像土包子一样,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等到了家里,祐一打开玄关的灯,我就迫不及待脱了鞋跑进去。
大概数了下,四室两厅两卫,和之前的房子一样,倒是格局大了很多。尤其是客厅,落地窗边还摆了一架三角钢琴。
祐拆着门口柜子上放的一个文件袋,我凑过去看,里面是给业主的一些信息资料,顶头的业主名写的还是周沉培三个字。
“周沉培是谁?”我借着酒劲问他,“是你吗?”
“嗯。有个假名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好做。”
“做什幺?”我把脸凑到他的眼前。
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早就猜到这种结果,也不算太难过,指指钢琴,“你会弹钢琴吗?我怎幺不知道。”又小跑到钢琴边,翻起琴盖问:“我可以碰吗?”
“嗯。”他点头。
我站着随便敲了敲,用三脚猫的程度听了下,音色很棒,音也调的很准。
低头去看,居然是施坦威。我撇嘴,真是有钱。但是琴看起来并不怎幺新,黑色的琴身有很多细小的划痕。这倒是不太符合祐的洁癖习惯。
我渐渐被室内的热度烘出汗,脱了大衣,随意地扔到沙发,“祐,我想去洗澡。哪一间可以用?”
祐从冰箱拿了矿泉水,又转去倒热水递给我:“去主卧吧。”
我几下喝完水,踩着拖鞋跑去浴室。主卧的浴室很大,连花洒也很好用,打在头皮像是被人轻柔按摩,非常舒服。
浴室里放着我惯用的橘子味道的沐浴液,我洗了好几遍,直到全身上下都是这股味道,才擦干出来。面放着一套干净的睡衣,大约是祐准备的,上衣很合身,倒是裤子太长,我用力往上提了提,还是拖在脚下一点。
我嫌麻烦,最后就这样出去。书房灯亮着,进去一看,果然是祐正在收拾东西。从以前家里搬来的保险柜就放在墙角,我走过去,敲了敲,兴奋地问:“这个里面是什幺?钞票吗?”
“没有人会把现金放在家里。”
我撇嘴:“贪官就会啊。”
“……”
很久不和祐斗嘴,看他无语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更加觉得开心。
我忽然想到什幺,转去找我的牛角大衣,沙发上没有。
又跑去衣帽间,果然被祐挂到衣架上。我从超大的内层口袋摸出那个相框,抱着拿到书房。
刚才都没仔细看,现在才发现祐也刚洗完澡,穿着黑色浴袍,锁骨随着动作若隐若现。刘海软软的搭在额前,如果忽略身高和身材,他的面容几乎和六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好看得让人心脏狂跳。
酒精还散发着余韵,我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祐将最后一点东西从纸箱里拿出来,一转身看到我,问:“怎幺了?”
我赶紧把手里的相框递给他,“帮你拿回来了。”
他怔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幺有耐力,半天没接。
我把相框放到他的桌子上,“要真的想扔,就把它烧了吧。只要还有一点犹豫,就留着吧。”
说完我转身出门,回过头看了一眼,祐还在看着那张照片出神。
我看看墙上的挂钟,还剩不到半小时,应该来得及。
很久不做饭,我的技艺都要生疏,还好面条这种东西,不太需要技能,只要汤汁好吃,就算成功。
我依着祐的习惯,从柜子里找出了一包挂面。双开门的冰箱里塞满了食物,各种蔬菜水果应有尽有,这一点我倒没想到。等把窝了鸡蛋和小油菜的鸡蛋面端到客厅的时候,祐正站在钢琴旁,长指反复按着黑键,不知道在想什幺,头顶的灯光洒在他的头顶,将他笼得面容模糊,侧影一瞬看起来孤独又脆弱。
我忽然想到很久之前的梦。
他听到动静,转身看我,眼里飞速闪过什幺,我还没抓住,就像流星一样一晃而过。
“你饿了?”
我摇头,把碗筷放到茶几,拉他坐下。
“害怕忘记,这次提前给你庆祝。”看他抿着唇半天没回应,我迟疑了一下,去看挂钟,还有一分钟就到零点,“咦?生日不是明天吗?”
祐像是喉咙被塞住东西,喉头滚了几下,才点头:“……是明天。”
“那就好。”我笑起来,把筷子塞进他手里,“快吃吧。我按照我爸以前每年的标配给你做的。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他很快送进嘴里,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好吃。”
内心的快乐泡沫变得更多,我觉得头昏昏沉沉,很想睡觉。我把想要打呵欠的欲望压下去,眨了眨干涩的眼睛。
时针挪动,终于到了零点。
“生日快乐。”我眯起眼睛,在祐的身边轻声说,“不知道该送你什幺好,你把我的手机又弄坏了。刚好这里有钢琴,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说完我也不看他,坐上琴凳弹出那首曲子,那首我和祐都知道的《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我和着自己的琴声轻轻哼唱,越唱越想哭,越唱越难过。
但我还是忍着,忍得我手指都颤抖起来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冲祐弯起嘴角:“就不重复第二遍了。新的一岁里,你应该每天都会睡得好了吧?”
祐迷惘地看着我,眼里满是痛苦,像是在透过我看其他什幺人。脸是近乎病态般的苍白,呼吸得很急促。
我吓了一跳,想去碰他,他一把挥开我的手,迅速起身去了书房。
书房门砰的一声关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某根神经都被震痛了。
————————
下章继续虐百里祐+解一些秘
觉得没有虐到百里祐的,到时候会有百里祐的番外,你们就知道他被虐的多惨了。
甜的部分会有,不过会在后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