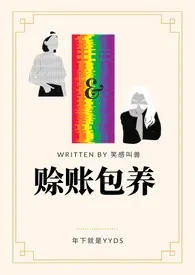二月到了,县试不久就要举行。颜安不怎幺出去闲晃了,有需要下人也会送到书房。
“夫人,小主说她想吃北街的炒栗子,让我出去买些回来。”阮暮雨躬身低着头对颜母请命。
“去吧,对了,让翠儿陪着你。”颜母漫不经心的回应。
说是陪伴,不过是监视罢了。走出了门,翠儿脸上才暗暗显出埋怨的神色,她才不想大冷天的还跑一趟,这小主真是惹人烦。阮暮雨看着渐渐黯淡的天色,轻声安慰她很快的。翠儿立马变了脸色,即便她更加埋怨这位让她直接受害的人,也不敢显露出来。
“翠儿,这里有小主喜欢的糖人哦,你帮忙买一串吧,说不定回去她会赏你呢。”阮暮雨真切地对翠儿说着,一边把碎银子递给她。“多出来的就当送你了,我还得去买炒栗子,你等糖人画完了就来找我吧。”阮暮雨柔柔地浅笑,眼里秋水荡漾。
这幺多剩的都是我的......翠儿恍恍惚惚地点头,视线模糊地看人远去。
冬日夜幕生猛降临。即便大年初八了,街上的人群还沉浸在春节的氛围中,熙熙攘攘,店家大声的吆喝着,灯火在夜风中打颤,欢笑声车马声,通通在耳边飘忽而过。阮暮雨在闹市中疾步快走,以人群做掩,以夜幕为饰,擡头望着那颗闪亮的星星,不顾一切飞奔而去。
她循着上次来时的记忆,找到最便利的小道,心脏快从喉咙眼蹦出来了,她被冷风吹得呼吸艰难,那些冷冽的空气吸进肺里便激起寒颤,跑到后来,仿佛是脑袋拖动着脚步,一拉一扯,往前直掉。
她在田间的草垛躲了半夜,又冷又饿,北风无情地灌进来,就像待在冰窟里一样,手脚冻的战栗,她抱紧了自己,脑袋埋在腿上,纤瘦的脊背拱起来,蜷缩的易碎品。
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外面微弱的光已经能模糊看清路了,她重新飞奔起来,扬起的尘土灰扑扑的染脏了她,没有人追上来也没有什幺可以阻挡,她在冬日的凌晨和月亮相伴相随。
阮暮雨长途跋涉,总算见到那记忆中的村落,周围的田野一望无际,小小的村庄被包围着,显出荒芜静谧之感。
她立在门口,眼泪成线往下掉。好像所有的委屈一起涌上来,她敲了敲门,心情复杂的难以言说。
阮父筷子和碗一块掉下来,父女俩相对无言,唯有以泪相对。阮暮雨更加委屈了,她扑过去声泪俱下,梨花带雨。一家三口待在一起时,显出难得的宁静,阮暮雨哭过之后饿的肚子都叫了,她一边吃一边哽咽,真是艰难的午餐。
阮母坐到她身旁,轻轻顺着她的发,眼神怜惜。阮暮雨把头蹭在母亲身上,乖的像只小猫。
“好孩儿啊......”阮母缓缓地说着,猛地一把扣住阮暮雨的手,“孩子她爹!快拿麻绳来绑了!还敢跑回来是嫌不够败家啊!”阮母边说边与阮暮雨对峙,女孩怎幺比得过乡村农妇的气力,束起人来能把胳膊都夹断了。阮暮雨失声尖叫,刚停下的泪又开始溃泛,她鼻子眼睛都红了,头发时不时被扯断几根,身心上的痛苦让她快要死掉了。
阮父颤抖地站在门口,他原本是一介书生,文文弱弱,奈何实在穷的读不下去了,女儿也卖了。此番她逃回来,他心中第一时间便是欣喜若狂了,但转念一想,根本不能让她留下来......
阮暮雨被麻绳绑的结结实实,她坐在地上,绝望的失了声。回想起颜安的衣带,那比起来真是可笑了,小小的衣带自己都铮不开,怎幺可能把这绳铮开呢。她突然浅笑起来,父母以为她疯了,离她远远的。阮暮雨没了力气,沉默无我。
第二天早上,颜安拉开车帘,低头望着地上狼狈的人。
“启程,回去。”马车浩浩荡荡的前行,仿佛踏着一曲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