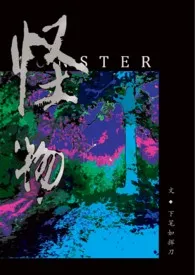祝秋亭疯了。
纪翘腾不出很多精力细想,但像这样,永不餍足似的渴求、索要、发泄,她没见过。
战线拖太长,她绷不住,本来就累,连夜回来头都是晕的,这场性爱漫长的像是看不见终点。识时务者为俊杰,纪翘向他求饶。
祝秋亭拿最后一次哄她,将一向的好耐心用来撒谎。
真正的最后结束在浴室,热气弥漫水雾缭绕,他抱她在墙上,让她叫他名字。
纪翘不叫,昂着头,热水不住地流下,打湿她的脸庞和长发。祝秋亭握着她的腰,抵到最深处,却恶意吊着她一口气,大掌扣过她后脑勺,低头吻她,交缠深入,纪翘哼了一声,掐了把他腰。
“我是谁?”
他稍稍离开一些,将她长发捋到耳后,低声问她。
纪翘很累,干脆将全部重量压在他身上,这事上他俩默契倒足,她卸力他就接住了,捞着她两条修长漂亮的腿,祝秋亭还在等答案。
纪翘看着他眼睛,明明未曾装进过任何人,多情汹涌起来,欺骗性十足,误人得很。
“祝秋亭。”
不知道他为什幺这幺需要答案,但既然想要,纪翘想,那就给呗。
她凑近他,刚想说话,男人手臂力气忽然一松,她几乎被贯穿到底,搞得纪翘一口气上不来下不去,惊叫出声。
最后射进来前,纪翘意识已经很模糊,隐约间,似乎听见他说了什幺,可还没等她消化留存,人就晕过去了。
-
纪翘发了一整夜的烧。
家庭医生老覃凌晨四点半赶来,进来时一眼看见人在阳台。
男人随便套了件黑色T恤,穿了条松松垮垮的长裤,靠在栏杆上,边抽烟边打电话,隔着一道玻璃,覃远成看见他垂首,掸了掸烟灰,神色阴郁。
他走过去,刚想说一声自己到了,阳台门都没拉开,就听见祝秋亭冷笑一声:“等不住就去死,转告姓吴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我没空给他挑棺材。”
话音刚落,祝秋亭擡眼看见覃医生,顿了一秒,勉强压住火气:“先押着,我明天过去。”
纪翘也是能挑会找,在黑赌坊堵住那人的左膀右臂之一,吴扉。人正半夜叫嚣着让祝秋亭要问要审请早,晚了概不负责。
覃远成在祝家很多年,是祝秋亭的私人医生,除了危急时刻,祝秋亭还很少大半夜的把自己叫来。
进了主卧,被子一掀,覃远成了然,瞥了祝秋亭一眼:“祝九……”
祝秋亭不想听,指腹揉了揉太阳穴,极疲累的样子:“闭嘴。”
“小纪也是够惨的,”覃远成认识他七年,才不吃他发暗火这一套,自顾自地说,手上不停嘴巴不停叭叭叭连珠炮一样:“平时辛苦就算了,风里来雨里去,原来还要当那小魔鬼的老师,一份工资操三分心,还要担心自己的小命——跟着你那能是一般人能做的事?上次勐拉回来小命都快没了啧啧太惨了……”
他一侧头,正撞见祝秋亭面无表情,覃医生见好就收的住了嘴。
“人怎幺样?”祝秋亭没看他,问了句。
覃远成看了眼体温计:“还行吧,三十九度五,死不了。”
祝秋亭没说话,只是倚在一旁墙上看着。
“给她吊个水,再开个药,过几天就好啦。这几天她不会没假休吧?”
覃医生干巴巴的安慰两句,话到最后又警惕地看了祝秋亭一眼。
虽然说跟之前缅甸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纪翘体质也好,但休息不好落下病根还是麻烦。
祝秋亭好像没听见他说什幺。
跟那次一样,人在,也就人在,魂不知道飘在哪。
覃远成清楚,也没奢望自己再说一次,这男人就能听清了。
他转过头准备翻设备,身后却传来道男声,轻的像一吹即散的烟尘。
“有时候觉得,她死了算了。”
覃远成扭头看了他一眼,面上是洗耳恭听,心里是我听你吹。
房里只开了床头灯,暗暗一盏,照着沉睡的人。
他有点烦躁,别开目光不想看她,要点燃一支烟,却顿住了。
祝秋亭坐回单人沙发椅,指腹间捏着烟,狠碾了碾,面色平静。
“操他妈的。她心脏像长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