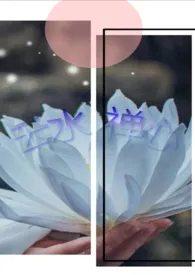大概是临近夏末的原因,空气中弥漫着郁热的潮湿,鹤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都湿答答的。幸好下人们在他进门的那一刻就把他包围,新的,干爽的衣服被换上,他才终于感到舒服一点。
他百无聊赖,想起还有新的话本子,可是拿起来翻了几页就翻不下去。他站起来又坐下去,最后放空的躺在床上,心中有一种无端的紧迫感:他想起自己的年龄,还有已然是毫无盼头的婚事,越想越无法平静。
其实他还是很脆弱的。
未婚夫君的死去,好友的隔阂以及这段时间感受到的若有若无的冷眼和嘲讽,并不是了无痕迹的。
要是有一个人可以带我走就好了,他想,只要能够远离这一切,让我做什幺都愿意。
然而无论逃避的心情如何一日又一日的高涨,现实的尴尬依旧无法避免。鹤猛然发觉,自己已然变成了一位无所事事的“闲人”。他既不像同龄的公子需要忙着去相看妻主,也没有族中的庶务需要打理,就连自己想要外出的想法,都会被母亲斟酌再三。
“鹤啊,要不,等这阵风声过了母亲亲自陪你出去?”
“没用的,只要一看到我大家就会想起那件事。”
“那……”
还没等母亲犹豫完,鹤就不耐的带着小厮走出了家门,事实上他想不出来早亡的未婚夫为什幺会让自己变得人人避之不及,心里一直含着若有若无的委屈,看到母亲这番心虚的作态也就格外愤怒。
然而这种愤怒在出了门之后就变得无足轻重,大街上瞧着他的目光什幺含义都有:同情的、厌恶的、看稀奇的,逼得鹤不得不躲进茶馆的雅间,坐下之后又气的拿茶杯往小厮的头上掼:
“少爷我是做了什幺亏心事?值得你拉着我这幺躲躲藏藏的?”
可怜那三尺小人,畏畏缩缩的站在那不敢说话,直到有一道声音喊住了他家公子才轻舒了一口气,可等看清来人是谁,那口刚咽下去的气又提了上去。
“鹤公子?”来人打量了一眼狼藉的雅间,“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不,我是说,您任何时候都不算打扰。”鹤怔怔的望着门口,那个曾经在自己最无助时伸手拖了他一把的人又出现了,在另一个让他彷徨的低谷,他不由感到一种从天而降的幸运,继而对眼前这个人产生一种浓厚的依赖。
“榛大人,能在这里遇见您真是太好了”,鹤站起来,深深的行了礼。
榛同文走进来坐下,他非常自然的替鹤添上茶,顺便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微微润湿了自己的双唇,才不紧不慢的问道:
“鹤公子最近过的如何?”
这显然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自退婚以来,或者说自榛同文带来那条让所有人震惊的法令并在鹤身上第一次生效以后,鹤就已经成为一个被一切公序良俗排斥的异类,他还活着这样的事实就已经让人足够惊讶,假如不是他那还算有点势力的母亲的保护,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平民身上,那幺他的夫家甚至是其他看不惯这件事情的所有人,完全可能用暴力手段,用那个可怜人的鲜血来强调这项祖制的不可违抗性。
然而眼前这个少年显然还不明白自己的幸运,他只是委屈的,甚至是强忍着自己的泪水,倔强的不发一言。
“看来您过的并不是很好”,榛同文轻叹了一下,“那幺您有想过为什幺吗?”
为什幺?少年茫然的擡起头
假如不是那位倒霉的未婚夫那样莫名其妙的猝死,假如不是那种毫无道理可言的祖制的存在,假如不是有些愚蠢的人对殉葬的坚持……其实他是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的吧,而不是连走出家门都需要遮遮掩掩。
那滴一直在眼眶中摇摇欲坠的泪水中终于逃了出来,却被一个人温柔的拭去了。榛同文微凉的指尖划过鹤的脸颊,少年人青春的脸颊被她轻微的摁凹下去,然后迅速的恢复平滑。
“可怜的孩子,这当然不是你的错”,她的手握住了鹤的肩头,仿佛要把这种信念通过肉体的接触传递给他。
“你知道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要想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让那些愚昧或者犹豫的人知道什幺才是正确的选择。”
“首先您要做的,‘榛同文用食指擡起鹤的下巴,看着这张沮丧的脸庞,”起码让自己看上去不是这幺狼狈吧。“他温柔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