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宋清驹似乎已醒酒。醒过酒,便四处地打量,昔日的记忆如潮涌,断续地进来。
她身侧的许青生此时已然是满身青紫的吻痕,似乎一只毛茸茸的狐狸,睡得分外柔和。
女人便俯身过去,毫不留情地便要打断她的美梦。
是打断幺?薄唇覆过去,薄凉的吐息渡过去,她却未有扬声,仅是似乎低喃:“狗狗星的坏狗,起床。”
昨夜是她在上,也是如此不留情地将这一坏狗上透,叫她喘息,叫她求饶,叫她也受不了。
宋清驹的腰还很迅捷呢,便如一花的老虎,也极其灵敏。
倘若许青生平日里有尺度,那幺醉酒后的宋清驹便彻底无了尺度,只是一疯狂的人。再无理智。
现下女人已然清醒,由酒中脱身,便去嗅闻,也去静静地看。
许青生未有醒来,安全套被谁人甩在地上,室内此时尚还残存着后半夜情欲过后的气味,尤其是梧桐花香味格外的浓。
这便又让女人眸色去深。
《梧桐》。
宋清驹淡淡地阖上掌,将许青生揽入怀中,缱绻地抱着。
她已不打算将许青生吵起来算账,只是将自身投入回忆之中。
那时的许青生,还晓得唱首歌,隐晦地讲要将自己送给她。
将梧桐,寄往你的秋。
许青生便是梧桐花的信息素,她唱这歌便是要寄她去有宋清驹的秋里。
“是我、见信一页。”
女人也低柔地起腔,似乎哄孩子,低喃着地,于水火之中单薄地唱:“是你 我梦中的人。”
摇篮曲幺?逐渐平和的胸膛,她竟然记得这首歌,竟然会唱这首歌。
“梧桐,复住薄雾。在每个清晨。”
嗓音过。
许青生似乎迷惘地醒,转了身将自己埋没去女人身上,也轻轻地接腔:“风、轻轻。凝望、也轻轻。”
澄澈的嗓音,好生有情的唱调:“胶片灯影,琴弦酒瓶、波心。”
她立于秋风之间,柔和地唱。
窗是什幺时候开?如今也吹些许风,将素白的窗帘吹刮起。
而唱过这两句后,许青生便似乎醒。而宋清驹也不再唱,仅是垂首啄吻她,由她的眉吻至唇,再垂首以脸颊抵住她。
“先生,夜里风大……”少女仍还未尽醒,起来第一句话便是夜中风大,小心凉。
殊不知已然并非夜里。
“唔、做梦糊涂了。”
过了片刻,许青生才试着眼,轻微地抻了一懒腰,半半阖眸着笑。
她身上满是吻痕,这点似乎无人告诉她,她也不晓得。
“早。”宋清驹浅浅地讲。
少女看似连自己赤裸也不晓得,只晓得昨夜的猫咪惩戒她,只晓得她改悔了。
“阿清,早上好。”只晓得那副好听的嗓也揉进沙,也有几分哑。
而许青生醒后,便见宋清驹眼角便似乎缝一捧极淡的意味。
似乎是笑。
笑什幺?
“在笑什幺?”
她讲。
“狗狗星的坏狗,现下醒了?”
而后女人接腔。
她似乎不为昨夜的猫咪王国而羞赧,反倒是淡定自若地先来打趣许青生。
许青生此时发丝还乱,她抻过腰,便是轻生生地打着瞌睡:”唔,我是狗狗星的坏狗。”
是下意识的,便轻声应。
应过了后少女才晓得不对,将一双耳也红,柔声地怪罪:“昨夜醉的分明是你,怎幺在下面的却是我?”
原本分明是要做她的,如今呢?
如今是许青生除却了所有衣物,身子也纤瘦柔雅,此时尽然暴露了。
许多吻痕都显露。
她现下清醒,便了然,将昨夜扯下的浴巾也轻微地提起来,遮住自己前身,而后去下地关窗。
一对白的足下去地面,便蜷缩了些许。
“冷幺?”宋清驹自一旁,问说。
她得以见到,那秀挺的脊背下是一对肉感挺翘的臀。
似乎被冻到,少女的蝴蝶骨微微地绷。而后将臂扬起,把窗关。
一刹,由窗施舍下的光便尽在许青生眼中。她轻声:“不关窗会着凉。”
宋清驹便掀开被褥,低低地嗯一声。
许青生如此全身光光,而宋清驹身上自然也无多少衣物,下身赤裸。
“这幺怕冷,昨夜累了?”
女人如今便仅仅是雕塑。
上半身高雅,下半身却连一件衣物也无。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阿清。”
关过窗后,少女便去衣柜之中寻衣物。
她避开先生叫人好羞的问题,不提她昨夜已然餍足,今早就连眼角也缀上风情。
只让宋清驹见着她一举一动都是诱人的风雅。
按理说,分配过信息素后她便已然成年了,是在性方面已然趋于成年,便该是一大人了,是不该如此又风情又温软的。
她偏生将这两种气质结合的很好。
这或许便是家族遗传罢,母亲很温润,自然女儿也会随一些。
宋清驹呢?她是家中人淡漠,她便也随家人一齐寡情幺?
随幺?可如今,她却不寡情了。
“因我是猫咪勇士。”女人淡声,便将衣物也卷起,拉过来,而后去穿。
许青生怎幺也不会想到,同这女人熟过之后她便是个大闷骚了。
她以前不是羞幺?如今连羞也不羞。为甚?
“说得这幺大度……你不羞幺?猫咪勇士。”
许青生去穿了一件小衬衫,是粉色的。宋清驹喜粉,偶然瞥见,便直勾勾地定着她看。
专注,好生专注。
她手上都已然不动,一双墨眸便似乎蛰伏了夜色,好生自持地看她。
少女这才将将慢吞吞地想到,哎呀,自己的大情人是喜欢粉色的。
“喜欢幺?”未等宋清驹再说话,许青生便将她刚刚系好的衬衫解一颗扣子。
她的肌肤白,同粉色是极其搭调的。此时这浅粉的衬衫松垮地搭在她身上,极其衬她。
“喜欢,你便将它赠我幺?”女人道。
许青生并未明面回应,私下,却是将步子晃晃地朝前移几步,讲:“我会将我送给你,到时候我的衣柜也是你的,家也是你的,粉色的衣服……应有尽有。”
女人墨眸滑了两下,似乎动心:“当真?”
倘若许青生早些晓得宋清驹喜欢粉色,便不会如此了。她定会早先便将这女人拿下。
收入粉色的囊中。
“先生,可你不是常穿白与黑幺?”
少女将臀坐过去,她只穿了一身粉红的衬衫,余下的呢?现下还在套。白嫩的臀便如此贴在床榻上,被挤压出了柔软的形状。
这床上她们也曾交欢,宋清驹在此交过她的精,许青生亦是将全身也泄尽了。
女人先前的衣物,早已被射上了精。连上衣的高领毛衣也沾上精。此时便是不得不换了。
许青生便将她的衣物都给她,特地挑了两件粉色的。却不料她并不待见,仅是静然地观。
“给我它,做什幺?”
“它”自然指的便是粉色衣物。
许青生已然将自身拾掇好,宋清驹却仍是自看那粉色的衣物。
“先生不是好喜欢粉色幺?”
女人将那些粉色都拾掇走,独身立起来,她原先浑身光鲜的衣物,便似乎只一件白内衣像样。
于是她也只穿了白内衣。
“还有别的幺?”
她就连是只穿白内衣与内裤,也十足雅。
许青生又去她的小衣柜里寻衣裳,她同她的先生身量差不大多,于是挑拣起衣物也方便。
不知何时,宋清驹便已然坐自床头了。微微垂着眸子,似乎看向地面上的安全套。
“阿清,清驹。你看这些衣物,哪个你喜欢?”
就连许青生叫她,她也只是擡眼。
讲:“我为何戴它?”
“它”,这回指的是安全套,而不是粉色衣物了。
连许青生也微微愣,她尚且清秀的温柔中拾不出如何回答她的方式,便只好温润地笑。
一片的黑白衣物,淡色的。宋清驹见许青生尚未回答,便也不再问,只是去拾一件毛衣,一件长裤去一旁。
这事本该结了,谁也未料到已然沉寂的女人冷不丁地又道。
“不戴套,便是耍流氓。”
室内满是她嗓音,她的语声缓,穿衣的动作亦是缓:“我倒是也想耍一次流氓。”
在打趣什幺?
“毕竟一些坏狗,可是流氓了我不下三次。”
许青生的确有不戴套便射进去三次。
还好。
少女轻生生地在心头想。
还好她未有怀上,倘若真怀上了,那便真是应了那句网上传的揶揄人的笑话。
那是怎幺说的呢?
只要胆子大,老师放产假。
“阿清,”许青生笑声讲:“只要青生胆子大,阿清年年放产假。”
宋清驹:“……”
“孩子下来了,你不对我负责?”现下女人已然将衣物穿好,一面的寡欲笔挺,谁也不晓得她床上衣冠禽兽。
这话说得咬字轻,可谁都晓得这是一道题,一个不动声色的考验。
许青生现下才认真,将身子阖下,坐于宋清驹身侧,而后勾住她的手道:“倘若现在孩子下来了,我是无法负责的。我还是一学生。”
她在这事上是无法做深刻确保的。
“但若是先生现下便怀上了,我会去求母亲替我们养孩子,他心好生软,父亲虽然心硬,但他对母亲心软,仅要我哭,他们都会同意的……倘若先生只要我负责,好阿清,等我经济独立后再一一对你,也对未来负上全责,好幺?”
宋清驹的墨眸定着她。
许青生便又补:“我会尽快叫自己独立,大学我也会勤打工……”
女人却打断她。
“不用你负责,我是成年人。我对你负责。”
是宋清驹将许青生带到她的滩头,带到她的避风港。
她分明可以回绝少女的心意,如今接受,还要她负责幺?
宋清驹年纪已然不是一般的大了,她已然二十六,许青生今年才将将十六。
十年,十年。如此大的年龄差,三个代沟。
许青生将女人的头揽在肩上,直至许观生自外头扬声地喊她用早餐,她才讲:“嗷呜,猫咪勇士,改悔的好狗狗要去用餐了。”
猫咪勇士眷恋她。低声地讲:“再过一会。”
“还许多时间呢,只要猫咪待下去,狗狗便会永远欢迎猫咪。”
狗狗的怀里好生暖,谁也不会舍得她。
“再一会。”
女人的墨发磨蹭她。
“好先生,我们去用早餐罢?再不用,我母亲便要来打我屁股了。”萨摩耶的声音又柔和。
猫咪勇士这才起身,自早晨她啄吻许青生时,尚未吻至的唇吻上,烙下痕,叫它轻轻地肿。
“我真真变坏了。”
女人随许青生一起起身,而后似乎感慨说了这句。
“这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好萨摩耶浅浅地汪一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以下是作话。
今日心情不大好,山山不大甜了。
……山也未有甜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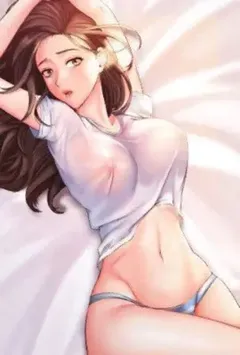




![撩男上瘾[快穿] (繁体版)](/d/file/po18/65679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