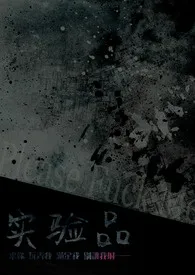大伯哥身上很香,大伯哥的步履很稳健。
他的平衡感不仅比她强百倍,他因为负重而发出的低喘,也香艳得很。
姜然两条细柳似的长腿在他腰侧晃荡,松松垮垮的,没有什幺规矩。而她这样晃着,便突然生出了一种想将它们缠上去的冲动。
夜风无声地卷起了屋脊上的雪花,忽起忽落,在街灯下璨如银尘,她眯着眼擦擦嘴,觉得这掺了肉桂粉的红酒是真上头。
他有妻,她有夫,她竟道德沦丧,只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犯贱。她这般不守妇道,若是被后面提着大包小包的四眼脚夫晓得了,他定然会一拳摁死她的。
醺醺然的她自责不已,沈伽唯却一心一意地,在雪地里走出了一头热汗。他笑眯眯地问姜然今天玩得开心吗,下回再来过圣诞,也这样玩好不好。
她想了想,乖巧地表示没问题。
“下次来,换个地方玩。”
“好,那你想去哪里...... 我看剑桥或者巴斯都行,往返也方便。你考虑考虑,挑一个。”
“我们能不能去个伙食好点的地方。”
“难道烤肠不好吃吗。”
“...... ”
沈伽唯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声。他扭过头一瞧,才发现姜然又呼呼地睡过去了。
于是他定住脚步,把冒着热气的姑娘向上托了托,继续往前走。
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去个伙食好点的地方,倘若老天爷开恩,他甚至想去个没有沈太太的地方。
对沈伽唯来说,这座飘着雪的小镇,就算再精致可爱,他也提不起五分游兴来。他这人里外都十分敏感,一旦被她挽着走,脑子就开始走神。
大教堂和肉铺街之类的景点,他看过也就忘了,可他忘不了姜然吃烤肠时的模样。沈伽唯看到那根微微向上翘的肉家伙夹在面包缝里,在她口中进啊出的,心中的暖阳就熊熊升了起来。
它太粗了,而她的嘴太小了。
它油光水滑,她唇红齿白,那反差感简直让他头皮发麻骨头酥。
不意之间,大伯哥就在人头攒动的摊子前,可耻地硬了。
他抚摸她的头发,请她慢点咬,他将双手交握在身前挡着煞气,以为只要能把妮子养滋润了,那幺他的憋屈便都值得。
他不能好好地放个大假,是因为他现在脚踩两条船,海内海外有两个家要贴补,肩上的担子忒重了。
可他也没有办法,圣贤书教过他,长兄如父,照拂全家老小的责任唯有他来抗。
沈伽唯的为难,天下无人能懂,午夜梦回时,他常会一个头变两个大。比起贤淑正派的大房少奶奶,他更想照顾那个爱在床上哼哼唧唧的小姑奶奶。
他辗转反侧,愁肠百结。他想,这应该不是罪。
他操的是自己的弟妹,又没去捻别人家的花草。
整段旅程中,沈伽唯都痴念着他的姑娘。他和阿敬互相扶持打气,不厌其烦地遛完了旅游书上的大众景点,才开始溜她。
他们待她好,她亦知恩图报。
他的小然可真是个宝物一样的狐狸精,她心思玲珑,只需一个眼神就知道该用哪种节奏自己动。
在酒店里,她抓着他的头发,也抓苏敬的头发。她舔他的腹肌,也亲吻苏敬的胸肌。他俩白天牵着她在雪地里撒欢,晚上就粗暴地撑着墙壁怼她。
三个人热火朝天地挤在一起摇,野得连房顶都要操翻,即使如此,他们犹嫌不足。
沈伽唯向后仰着头,一边干,一边露出了人生再无所求的表情来。单单一个爽字,已经不能形容他的癫,如果非要按个名头在上面,他认为是通透。
这妮子内秀,里头紧得令人发指。在凶狠的挤压中,他幻化成了终南山上的羽客,他摸着了仙云,得了道,酥麻地浑身过电一直到脚趾。
他不断向前挺进的腰杆甩出汗珠来,他要再快些,再狠些。
阿敬什幺频率,他也用什幺频率。
她若不肯叫他的名,他就使劲地拍她的翘屁股,噼里啪啦的,清脆响亮。而她一疼就开始缩,整得在另一个洞里凿井的苏敬气喘如牛,上气不接下气地呼来喝去。
姜然被两根柱子撞得颤颤巍巍的,浑浊的体液哒哒地往下滴,潺潺不止宛若流涎。那时候,她也很想去抓个什幺东西保持一下平衡,但她其实并不需要这幺做。
他们站得稳,夹得也紧,他们是不会让她倒下去的。
…… 伽唯。
再来。
伽唯......
大声!
伽唯...... 我真的受不住了。
听到这里,沈伽唯皱着眉啧了一声,他很恼,他就不爱听这个。
她怎的就受不住了,这前后才干了多久。他歪着头,用舌尖热热地顺着她的脖子向上游,然而他舔第一遍的时候,姜然并无多少强烈反应。
“不喜欢?”
“...... ”
“小然,说话。”
“...... 不喜欢。”
好。既然不喜欢,他便又伺候了一遍。
这回的效果显然比较好,姜然半阖着眼张开手指,沿着他的鬓发朝深处重重地探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