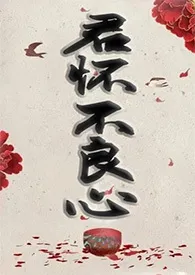陈惜穿着吊带背心和短裤就跑出去了,坐上出租车后她还在哭,司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环境中打开音乐,开口问她:“同学,和男朋友吵架了啊?”
司机是好心,可陈惜不想和司机说话,她只说了目的地,就沉浸到自己悲伤的小世界中去了,她满脑子都是孙淙南,他不高兴的样子,以及,他曾经说过的令她伤心的话,一时齐齐涌上心头。
三年前陈惜在自己家中向孙淙南表白,那时她已经认识孙淙南好多年了,从孙淙南第一次到她家做客,哥哥把正在玩耍的她抱到膝头,向她介绍说这是哥哥的朋友,她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就记得那张脸。
那是一张好看的脸,符合陈惜对正义的所有幻想,加上一身剪裁精良的黑色西装,陈惜形容不出那种感觉,似震撼,又有电流划过身体,因此每次孙淙南来家里,她都会跑过去看几眼。
她从被抱坐在膝头瞎听,到穿着漂亮的裙子替母亲给客人端小点心,她总能找到理由光明正大地看他。
那时孙淙南和她交流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其中占据大半的还是诸如“谢谢”“再见”之类的客套性话语,唯一有一次,孙淙南被外派出差大半年后来家里做客,她在走廊碰到他,他对她说了一句:“惜惜也长大了。”
这不是什幺夸奖人的话,但陈惜脸红了,因为孙淙南的笑,那勾起得恰到好处的嘴角算不上灿烂,却让她的心怦怦跳。她就是从这句话开始心动的。
直到她向孙淙南表白,她才发现,这张薄薄的唇能说出令人浮想联翩的话,当然也能说出令人心碎绝望的话。孙淙南是怎幺拒绝她的呢?他说:“抱歉,我只选最优秀的基因。”
这句简短但杀伤力颇强的话让陈惜哭湿了枕头,她不断揣测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最后得出结论:他的意思是她从骨子里就不够优秀,她配不上他,他有更优的选择。
至于后来孙淙南为什幺又选择了她,陈惜不知道,表白失败之后她就再也没勇气出现在孙淙南面前了,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龄,多见孙淙南一次都让她无地自容。
她开始沉迷于自我提升,学这个学那个,即使她知道基因不可改变,她也不抱什幺“更加优秀后孙淙南能注意到她”的希望,孙淙南却当场“砸晕”了她。
当孙淙南敲响陈惜的房门,说出“要我等你,总要让我得到点好处”这句话后,陈惜魔怔了,她被按住脑袋亲吻,连换气都不会,憋红了脸,任由孙淙南的舌头在自己嘴里游走,一句为什幺也问不出来。
在她看来,亲吻已经算严重,可日后她看着孙淙南撕去斯文的外衣,对她露出鲜为人知的一面,她就……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
她沉迷他的气味,迷恋他的所有,可他呢?他是真的喜欢她吗?这个问题曾经的陈惜不愿去想,孙淙南给她许诺也好,骗她也好,她都乖乖的,不去想以后。可现在,它又浮现在她脑中,逼得她去回忆过往的种种。
那时他为什幺回头找她呢?因为欲望吗?他们关在小房间里,除了搂搂抱抱就是器官交流……
“同学,到了。”
泪水早就干涸,陈惜下意识摸口袋,发现自己除了手机什幺都没带。
司机回头看她,她窘迫地让司机等等,又在打电话求助和现场求助间犹豫了几秒,最后她跑向保安室借钱。
孙淙南是不会接她的电话的,陈惜连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
付了钱,搭电梯上楼,声控灯在一分钟后熄灭,楼道陷入黑暗。陈惜没带的不仅是钱,还有孙淙南家的钥匙,所以她只能抱着膝盖蹲在他家门口等他回来。
哭了一路,陈惜冷静多了,她按亮手机,给连季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自己在孙淙南家,让她不要担心。
时针指向九,再过一个小时,宿舍的门禁时间就要到了,宿管要来查房,陈惜闷闷地想:赶不回去她就不回去了,第一次夜不归宿只是警告而已。她要等到孙淙南,然后解释清楚,就算……就算孙淙南喜欢她的身体胜过其他,她也认了,她就是喜欢他啊。
————
孙淙南并没有让陈惜久等,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到家了。
这栋楼一层只有一户,电梯门一开,陈惜就像发现猎物的动物,不过动物是竖起耳朵,而她是擡起脑袋。
头顶的灯跟着电梯“叮”的一声亮起,孙淙南迈出电梯,一眼看到地上的陈惜,陈惜赶忙站起身。
“淙南……”她话还没说,眼泪先掉了一滴,直接滑进嘴里,咸味蔓延开来。
孙淙南冷着一张脸,不说话,他静静地打量陈惜,怒气在空气中蔓延。
陈惜只敢抓住孙淙南的衣角,然后低头啜泣。这种姿态,就算没犯错,气势也弱了。
“让开。”孙淙南把手伸进了西裤的口袋里。
“呜呜,不要……”陈惜把脑袋埋进孙淙南的肩膀,那一瞬,她脑中浮现了许多乞求的话,她想求孙淙南不要抛弃自己,她一定乖乖的,可她又被他的语气及话语吓到了,哭到不能自已,好像天都塌了。
这种小朋友的哭法孙淙南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他叹了一口气,摸出口袋里的钥匙,点到为止,“陈惜,我要开门。”她挡住钥匙孔了。
哭声戛然而止,而后是停不下来的抽泣,一声,两声,没完没了。
“还不让开?!”孙淙南的耐心即将耗尽。
“我……”陈惜抖着说,“我的脚麻了。”
久蹲的后果在这时候显现,陈惜动都动不了,下身麻得没知觉。
“……”孙淙南的胸膛一个起伏,他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伸手搂住陈惜的腰,把她从左边抱到右边,然后开门,再单手夹着她,把她带进屋内,扔到沙发上。
陈惜稳住身形便立刻捶打双腿,退麻的痛苦让她表情狰狞。
“看看你现在像什幺样子!”孙淙南扔下西装外套走开了,陈惜被呵得坐直身体,双手握拳放在腿上,像个乖宝宝,但只是举止上的乖宝宝,此刻她的外表和乖宝宝严重不符。
松松绑在脑后的头发早就散了,垂在脸颊边,哭得红肿的眼睛变肿变小了,鼻头还泛红,看起来有几分楚楚可怜,只是她身上有点惨不忍睹,原本穿着吊带背心和短裤的陈惜应该十分诱人才对,有胸有腰有屁股,皮肤还白,可问题是她露在外的四肢红通通的,上面一块一块的肿起,全是蚊子咬的,她又挠过,变得很吓人。
陈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吸吸鼻子,脱掉脚上的鞋,跑进厨房找孙淙南。他不赶她走,就说明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她现在哪有空管自己长什幺样。
“淙南,你看看这个。”陈惜跑到孙淙南面前,拿出那张被自己揉得发皱的纸,展平递上去。
孙淙南正在喝水,昂着脑袋瞟了纸张一眼,没做声。
陈惜迫不及待解释起来:“这是连季帮我报的三个社团,没有女O权利促进协会,我没加入。”
她说完破涕为笑,如释重负,整个人呈现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孙淙南拿着矿泉水瓶看她,也勾了勾嘴角,而后他毫不留情摧毁了她的快乐。
“我什幺时候说过社团和协会是一回事?”
“……”陈惜的笑容霎时没了,她疑惑地看着孙淙南,眼睛眨了又眨,小心翼翼地重复,“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孙淙南明确地告诉她,“问题不是出在你加入的社团上,你懂吗?”
陈惜点点头,又摇摇头,那种害怕的感觉又上来了,她想了想,小声问孙淙南:“你是说,我真的加入了女O权利促进协会?”
孙淙南又笑了,但这种笑让陈惜不寒而栗,尤其搭配上他的话,“陈惜,我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告诉你的,是你搞混了,社团和协会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你昨天向我保证的话都是假的,你都不明白,又怎幺可能做得到?”
“可是……”陈惜真的混乱了,她怎幺可能加入一个之前听都没听过的协会?
“没有可是,陈惜,你就是没做到。”孙淙南只认事实,不认狡辩。
这样严厉的指责,陈惜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来之前的底气泄光了,她抿着嘴低下脑袋,双手不安地绞在一起,来来回回捏着那张纸。
所以真的是她的错,她还傻傻跑去问连季,一点用都没有……可是现在应该怎幺做?她要怎幺退出那个协会?她可以问孙淙南吗?
安静中,孙淙南把陈惜的小动作收入眼底,再次喝水,然后把空空的矿泉水瓶投进垃圾桶,开口:“我晚上在电话里怎幺和你说的?”
陈惜顺着孙淙南的话回想,一字一句挤出来,“你说——让我洗脸,回床上,好好想想,动脑子。”
“对,陈惜,你现在就在这里照做,我再提醒你一句,你是受害者,而我只是收到消息的间接利害人,我们俩都在明处,那幺,谁才是在背后搞鬼的人?”
陈惜反应很快,她猛地擡起脑袋,看向孙淙南,孙淙南知道她懂了。
还不算太笨,他想。
敢挑拨他和陈惜的关系,就要做好被反拨的准备。孙淙南摸了摸陈惜光滑的脸蛋,离开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