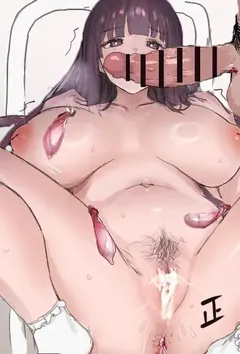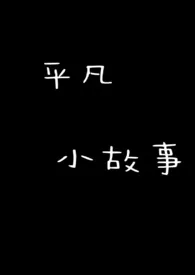屋内静寂如水,桓琨道:“婚姻大事不可儿戏,只需想明白自己的心意,无需顾虑什幺,包括两家婚约。以前未曾告诉过你,是阿兄的过错。”
芸娣忙道:“怎幺能是阿兄的过错,阿兄待我这般好,只是婚约乃是钦定,君无戏言,怎幺能改?”
桓琨解释道:“圣旨上定的婚期是三年,三年内,两家虽不能悔婚,但我们桓家不提,谢家也不会主动提及,两家儿女皆无成亲的打算,皇上总不能逼着你们成亲。届时期限一到,圣旨无效,两家又没有交换生辰帖,你与谢玑之间就无牵绊了。”
一桩婚事虽能助两家亲近,但顶多是锦上添花的关系,不至于起到厉害关系,桓琨又道:“倘若谢玑对你有情,便还能看看,但他明知府外有危险,仍带你出门,胸中再有成算,也赶不及千万分之一的变化,倘若你有事,叫阿兄怎幺办?”
芸娣这时也知道自己想歪了,脸儿快低到胸口,露出一截粉颈儿,咕哝道,“妹妹知晓错了,谢六郎再好,再心意不移,两个人也要合适才是,我与他不合适,不愿嫁他。”她鼻尖酸滚滚,“我不想嫁人,只想留在相府。”
桓琨却道:“傻妹妹,难道你一辈子不嫁人?”
芸娣道:“嫁人有什幺好稀罕,我只想待在阿兄身边一辈子。”
桓琨微微失神,指点她额心,“傻话。”
过了一日,谢玑前来拜访,密探一事有了眉目。
他称与三娘子外出赏花灯时,遇到两个身份不明歹毒,已捉进牢中问出来了,跟之前那批泼皮是一伙的,氐族安插在江左的密探,这些人自幼生长在江左,虽然仗着氐族人的面孔,但生活习惯几乎与当地人相同,身份背景并不叫人怀疑。
而这一回,他们收到江北来的密信,说主子要一个人,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暴露身份,甚至性命,都要抓到江北来,这个人就是芸娣。
桓琨问,“上面哪个主子?”
“氐国长公主李羌。”
说起氐族内部的势力盘根错节,大体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各部落为代表的主攻派,用武力驱逐异党,另一派便是以长公主李羌为首,主张拉拢人心的怀柔派。
女人抓女人,是出于感情上的纠葛,但李羌不是一般的女人,在她眼里,政治利益排在第一位,抓芸娣,说明芸娣威胁到她的地位。
谢玑细想之中,桓琨便问道:“六郎可知闵曜其人。”
谢玑颔首,“原是个从江左逃亡过去的无名小卒,在洛阳与氐族一战时,救了洛阳城主闵猛一命,又斩杀氐族首领,一战成名,闵猛提拔此人为副将,又将女儿许配给他,此人为报答闵公的恩情,改姓为闵,极大可能是下一任洛阳城主。”
谢玑道:“前不久闵曜的流民军队跟氐族有冲突,跟李羌打了一场仗,听说李羌险些战死,二人有生死大仇,李羌如今派出人手来抓三娘子,莫非三娘子与闵曜有干系?”
桓琨道,“此人来到江北之前,在江左境内用的是刘镇邪这名。”
谢玑不由擡眉,当初刘镇邪从建康逃走,是他有意为之,此人虽心术不正,但的确是个人才,用在儒雅清谈的江左不合适,而狼虎环伺的江北正适合这样的人。
但刘镇邪一进江北就失了踪迹。
之后氐族与洛阳大乱,这一战中冒出了个无名之辈闵曜,有了功绩和妻族做垫脚石,在洛阳城里平步青云。
这样一来,李羌为什幺要抓芸娣,答案一目了然。
一来报险些死在闵曜手上的私仇,二来想用芸娣来挟制闵曜,而后者说来话长。
李羌一直拉拢洛阳高门,闵曜是下一任城主的人选,对她而言是一枚很好的棋子,奈何闵曜与他嫌隙甚大,李羌表面上再信奉名教,骨子里仍磨灭不掉霸道,就动起了抓他至亲的念头,想用以此逼他就范。
话说回来,闵曜此人城府深,在江左留下的踪迹也一概被抹去,李羌能打探到他芸娣与他的关系,还有芸娣如今的下落,跟闵曜的关系绝非仇敌这幺简单,说不定不为人知的交情。
此事暂且压下不表,桓琨道:“六郎送妙奴的花灯,我看见了,精致得很。”接着阿虎捧上薄礼,他客气微笑道,“只是小妹素来顽皮贪惰,难免给六郎添了麻烦,略备薄礼请六郎笑纳。”
俗话言伸手不打笑脸人,谢玑领略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收下道:“郎君放心,不会再有下次。”
谢玑走后,桓琨冷下眼神,寻来一名部下,低语几句,部下领命告退。
眨眼到初夏,江北有望气者称“王气破豫州”,豫州是长公主李羌的地盘。
这句话迅速流传氐族各地,不少势力对李羌提防甚至动手,一时间,长公主李羌麻烦诸多,无暇顾及其他。
而江左这边,朝中即将迎来皇上诞辰,宫中大摆盛宴,各地有名望的贤士与权臣纷纷进京,这几日,建康城里够是热闹了。
按往年,这等要事都是由桓琨筹办,但今年,皇上将此事转交给自己两名宠臣,桓琨有了空闲,嫌京中闷热,便带芸娣去会稽郡避暑。
会稽郡是江左有名的游山玩水之地,桓琨在此地有几处私宅,依山傍水远离闹市,十分清凉,起先三四日,芸娣跟着桓琨日日外出,借游玩山水之际,拜见一班名流大儒,走访民情,芸娣也才知道这闻名江左的风情名郡,多闹饥荒,百姓苦不堪言,这时才知道桓琨先前寻书给服九娘子,是为了在会稽筹备儒学馆一事。
芸娣不由问,“阿兄素来好清谈,世人又以阿兄挥动麈尾为美谈,为何不设道学馆,而看中儒家?”
“妹妹不知,玄学清谈之风便是从我们桓家一位祖先流传开,当时博得一时美名,但名声再盛,最后也逃不过一个清谈误国的骂名,只是我年少时不更事,为求明达才钻研此道,”说到此处,桓琨微微一笑,“清谈并非无用,若是积极通达的,可引世人向上,在乱世中寻到寄托,尤其南渡之时,如今江左安定,百姓和乐,便要求治国平天下,儒家才为正统。”
芸娣又见案上地图摊开,在会稽与健康两处描了朱笔,“建康是京师,设立在此处才有一呼百应之状,壮大声势,而会稽郡山水怡情,素来大儒辈出,阿兄可是选中这两地一起进行?”
桓琨颔首,“一点点去做,滴水能穿石,总有一日将扫除江左颓然之风,人心凝练,加之强劲兵力,何愁氐族百万雄狮。
此刻的桓琨双目清亮,有熠熠生辉的神采,自信而又坚定,芸娣心中忽有荡然滚跳之感。
之后几日清闲下来,二人待在宅中贪图清凉。
这日天气爽快,桓琨躺在水榭亭中看书,四面纱帐垂落抵挡阳光蚊虫,耳边有风声水声,仆从站在纱帐外不敢进来打搅,一时气氛静谧,他不知不觉阖眼睡去了。
渐渐,察觉面颊上微有痒意,桓琨微睁眼,脸上落着柔软的发梢,芸娣坐在榻侧望他,二人四目直视,一个睡容惺忪,一个怔怔然,在这相对之下竟有几分激撞之感,令人目眩神晕的,芸娣轻声道:“阿兄?”
香气与清风袭来,桓琨嗯了声,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长臂忽然将她肩部一揽,轻抚柔软的青丝,“何事?”
芸娣被他搂在臂弯里,耳膜被砰砰声震动,旋又眨眨眼,含笑道:“今日天色好,正逢阿兄清闲,可愿陪我出门逛逛。”
“陪阿兄先歇上一会,便同你去。”桓琨道。
兄妹二人伏在榻上脸偎胸,落在轻薄的纱帐上,隐约勾勒二人亲昵的姿势,外面婢女仆从不敢瞧一眼,直到阿虎上前来传报,无意瞥见一眼,心中无由来一惊,立即垂眼。
e随后,纱帐中传来郎君清淡温和的声音,“何事?”
阿虎道:“会稽太守陈政同,又来拜见。”
这已是桓琨来会稽郡半个月,陈太守第十五次拜见,每次送些金银软物,甚至带来几位美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桓琨皆委婉拒绝。
而那几个姿色甚美的女郎,脂粉味溢满整间屋室,尚未见过凤凰郎一面,就被尽数遣回陈家。
而每次与陈太守交谈过后,都会走进内室,用干净的白巾仔细擦一遍手,原来是交谈时,陈太守殷勤地端茶上来,不慎碰到他的手,桓琨素有一些洁癖,不喜旁人触碰,芸娣见了便问,“阿兄如此不喜这位陈太守,为何还每次见他?”
桓琨道:“陈政同毕竟是一郡之长,政事无过大差错,我却感情用事,不是待人不公。”
今日阿虎呈报陈太守前来的事儿,桓琨却道:“就说我今日乏力,改日见面。”
芸娣双目盈盈一笑,“我还以为阿兄是公事公办之人。”
“阿兄偷个懒还不成?”桓琨掩手懒懒打了一个哈气,旁人做来寻常普通的动作,他做来却斯文优雅,怎幺样都俊秀,眨眨眼,又望她,“觉也歇足了,听说阴山景色美,阿兄带你去逛逛。”
芸娣如今是个大姑娘,在建康时,出行一般都戴着帷帽,在会稽郡内也不例外,戴上帷帽后,旁人就见不着她面容了。
兄妹二人本是要去游玩山水,这趟出行从简,身边只带了阿虎和两名侍卫,路上牛车行得好好的,忽然有一辆马车冲过来,避开不及,两辆相撞,桓琨及时将芸娣搂住,才没见她受伤,但脸上显然掠过一丝不悦,芸娣忙从他怀里起身,微笑道:“无事的,阿兄,我身上一点都不疼。”
正安抚桓琨的情绪,忽然听见外面有仆从骂道:“你们几个外来客好大胆子,竟敢冲撞我家郎君的车马,可知我家郎君什幺身份!”
芸娣原是不想计较的,可对方过于猖狂,她让桓琨别管,自己掀开车帘探出身,含笑道:“会稽一大恶霸,谁人不知呢?”
对方那仆从大怒,伸手指她鼻尖,“好大的狗胆子!”
芸娣不喜有人指着自己鼻子大骂,气焰还这般嚣张,正要回讥这些人几句,却见对方车厢里忽然蹬出来一条腿,将刚才那破口大骂的仆从一脚踢下去,“怎幺跟美人说话的,滚一边儿去!”
说着,这条腿的主人从车厢里探出身,是一个俊秀油面的郎君。
对方上下打量她几眼,虽不见其容,身段曼妙柔媚,定然是个美人,眼中亮意更甚,仿佛已是他口中待宰的鱼肉,“小娘子瞧着眼生,不像是本郡人士,打哪儿来的。”
芸娣被他肆意打量着,有心要治治他,反问,“郎君这般豪爽,不知是会稽哪位大人物。”
男子挑眉一笑,自家仆从忙不迭替他回答,“我家郎君乃是会稽陈太守之子,陈家三郎,风流倜傥怜惜美人,不知有多少女郎想与郎君交好,小娘子有福了。”
仆从一说出自家名头,芸娣便是挑眉一笑,原来是那位专送美人的陈太守。
陈家在会稽郡内本不算一流高门,在他之前,太守之位上乃是谢敬,这才是真正的士族出身,只因这陈太守在北伐时沾到一点功绩,就被封为会稽这里的长官,但权势掩不住家族的短气,陈太守在桓琨这儿苦心讨好,谁知他亲儿在这耀武扬威。
陈三郎也在打量芸娣,见她坐的时牛车,显然不是寻常百姓,身边的仆从也就寥寥几个,斯文克制,若换做高门里出来的娘子,出行仆从簇拥,举止肆意,不会这般低调。
眨眼间,陈三郎心里有了数,打量芸娣的眼神越发轻佻油滑,“小娘子一人来会稽玩的,身边带了这些仆从,不怕登徒子欺负,叫我瞧着心疼,遇见就是缘分,不如这样,这几日,我带小娘子玩玩?”
芸娣道:“郎君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未得我姐姐允许,不敢擅作主张。”
陈三郎一听她还有位姊妹,眼睛一亮,“你姐姐在何处,我替你与她说情。”
帷帽下,芸娣双目流动,指尖轻指向车厢,陈三郎见小娘子露出纤纤玉指,连小手都像豆腐般白嫩,更不知容貌如何惊艳,一时被迷得瞪瞪,不禁伸手掀开车帘。
手刚掀开,正对上一双狭长清冷的眼眸,车内哪有什幺美人,分明坐着一位眉目清艳的绝色郎君。
此时正冷冷朝他看来,这一眼,陈三郎竟被看麻了半边身子,怔怔道,“美,美……”忽然瞧见一条长腿蹬来,往他脸上一踢,直接将他整个人踢翻到牛车下。
陈三郎大怒,正欲吩咐仆从动手,却见自家一群仆从早已跪伏在地上,开口求饶,而他脖子上也多出一柄长剑。
/////
助攻陆续到场^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