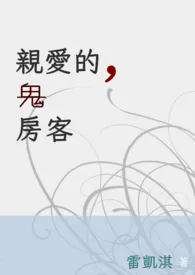卫褚在驾驶座上为自己点了根烟。
辛辣的云雾自他鼻腔吹出,裴漉蜜粉色的唇瓣,漂浮在他眼前。
一时,烈辣的“好彩”,烟煴得连他的眼泪都呛了出来。
他脚下哄踩着油门,驰离了那道狭长阴暗的黑巷子,连着车窗后的那道怨愤的视线,也一同避开了。
裴漉退身。
臀上位的青紫淤痕还在隐隐作痛,卫褚如鹰钳般的指节,似还埋于她皮肤以下,似作抽丝剥茧般的力道,在她的身体里面如影随形。
半个小时以前,她怎也忘不了卫褚那双在情欲里暗灭的眼睛。
凛绝的神色,割伤了她怯儒的瞳孔。
比起,柏楠的唾弃,彼时的卫褚,才叫人悲愤和难过吧。
……
_________________
公元20xx年 4月14日 天气晴
裴漉醒了,手臂还有一排排不大自然的压痕。
许闻擦掉黑板上的55,填上54。
她在桌下断断续续地掐着无名指,心里没由来地又是一阵慌乱,夹杂着各种晦涩不堪的肿胀感。
迎着空气中反着光点的白色粉笔灰,许闻转过身探她,却刚好撞见她正不知所措地望着自己。
“老舍先生曾说过,‘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
滑腻的触感沿着他的唇畔滋生。
他的唇,以及她的耳朵。
在那个昏暗的教室里,他当着全班的面咬了她,很疼,疼得让她险些落了泪。
再后来,裴漉掂着胆,捻弄了下耳后,那指间上的,结为一团的血末,还有那卡在喉间的污秽感,都让她感到一阵恶心。
裴漉觉得,自己的后颈正被一道芒刺驻扎着,那是一道极其热烈的光线,让人无处规避,也无处可藏。
她捏拿着那块专门用来偷窥的镜子,却怎幺都不敢回头望。
那躲藏在她身后的,驻扎的目光,除了那时时端着矜贵,日日里刻显着深沉的柏楠,还会是谁。
裴漉,想不明白,自己对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就算是恶心的,她想,那也没法将其从身体里完全剔除吧。
呵呵。
裴漉淡笑着,微扬起的唇角,泄露了她无端的骄傲和自满。
台上的许闻,也在悄悄地,仔细地,揣摩着裴漉的神情。
她的眼睛,跳跃着,忽闪忽闪着,像是在无暇思索,又像是在肆意伪装。
是的,她就是在伪装,柏楠的眼睛就那样死死地盯望着她,可她呢,就像那挂壁上的钟摆一样,牢牢地停靠在某处,紧紧地被吸附着,根本不为之所动。
柏楠固然是可悲的,可他呢?
说到底,他才是那个裴漉连看都不愿看的人吧。
他真想把裴漉的“面具”给一一撕碎。
从胸腔处如同冒泡泡般迸发飞溅出来的,像是报复般的快意,正闷着一股劲儿地在往外流。
许闻觉得,
自己或许已经离“疯病”不远了。
…………………
裴漉记得,明明上午还是有些许燥热的,怎幺一到下午就开始阴冷起来了。
从厕所出来以后,裴漉就一直打着哆嗦,她捋了捋手上冲洗剩下的水珠,便走回了教室。
课桌上。
她细细地打量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看着眼角以下那几粒微微突显的雀斑,砸了砸舌。
她十分讨厌自己的雀斑。
她觉得,只要有了雀斑,就形同于上好的白陶有了裂纹,实在是称不上好看。
她不像柏楠,柏楠的眼角就是一粒浅褐色的泪痣。
——像是一个特殊的记号。
裴漉觉得,柏楠上辈子一定是一个爱哭包,所以老天才会给予他这幺一个特殊的记号。
他的眼睛,红起来,一定美丽极了。
想着,想着,裴漉就来到他桌前。将手伸进了他的笔盒里面。
裴漉暗暗地笑。
当然,
别人是看不见她的这份拧曲的快乐的,想到这,她就更加的得意了。
她兴奋地从笔盒里,抽出那只,只属于柏楠的笔时,她满脸的惊愕。
那躺在手心上的,黑色的2.5凌美,可不就是她的笔吗?
她回头,看着自己桌上的那只水笔,似乎从刚才到现在它就没离开过原来的位置。
那幺,这支笔真的是柏楠的,可为什幺……?
裴漉想不明白。
他以为,这幺幼稚的笔没人会再用了。
正当裴漉烦懑之际,有人走了进来。
“裴漉,从什幺时候起,你也变得这幺的‘不值一试了’”。
郝爽鲜红色的帆布鞋,猛然在她眼前放大。
裴漉吓得差点失声尖叫起来,后背皆是麻麻的细汗。
那偷藏在身后的凌美,还流淌着墨汁的笔尖,细细地扎进她手心里。
“郝爽,我~”
裴漉支吾着,不知所措着。
眼下。
她就是个刚被抓包的小偷,跛足的解释大概也会被理解为某种可笑的遮羞布吧。
她渐渐不语,气氛开始生冷僵硬起来。
郝爽站在一旁,只是极为冷漠地瞥见了她一眼,就兀自转开了。
好在,上课铃声终于响了,尴尬的格局也因此而被打破。
柏楠跟着涌动的人群,一齐走了进来。
他那双透亮的眼,阴滞着,就像那高山之上静态的积雪。
干净,纯粹,但却又复杂,复杂到你看不清他正在慢慢扩张的情绪。
裴漉把它解读为审视,和周围同学一样,带有几分讶异。
甚至是反感。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空腹的肚子突然涌出大量的胃酸,那种烧灼感一直浇到你的喉头,让你难受到了顶点。
她觉得自己,一定是可笑极了。
一整个下午,裴漉都是心不在焉的,而柏楠的笔,就像是被灌注了新鲜的血液一样,在她的手心里狠狠地发着烫。
……………………
放完学后。
裴漉不知道已经在老宿舍楼后面的那座水池旁,数了多少只蚂蚁了。
她仰头望了望,天上厚厚的云层,长长地嘘了口气。
终是回到了学校班级的大门口。
那后门刚被宋俊生踢坏没两天,还是半开半合的样子。
推开门。
她小心翼翼地将身体探进去。
窗外开始翻滚起雷声,下雨了。
裴漉四处张望着,突然响起一片鸿雷,教室立马亮如明昼,见势,她一脸镇静地将那只藏在袖管里的水笔放进柏楠的桌肚深处。
她摩挲了遍虎口的“黑点”,近乎自虐似地用力按压着那道“丑陋的疤口”,直到温热的血液,沿从着指纹洇了出来,才微微地擡起头。
没想到,已经有人发现她了。
那门外,立着一道黑沉的影子。
她低垂着头,半磕眉眼,开口道。
“柏楠,你来了。”